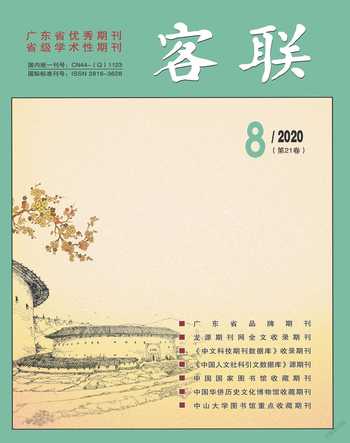論黨組織在國有企業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黃丹
【摘 要】我國國有企業股權結構集中的現實背景下,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及監事會三權相互制衡、內部監控的制度設計有其合理性,但國有企業中黨組織的地位、職責和參與管理的方式在公司法中沒有規定。本文試圖通過明確企業黨組織在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和職責及其行使權力的程序和規則,現有的法人治理結構就會充分發揮相互制衡的作用。
【關鍵詞】國有企業;黨的領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各國應采取何種法人治理結構,應從其自身實際出發,結合各自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法律制度的特點確定。我國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如何提高其運營效率、增強其競爭力和活力,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和難點。過去,我國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對國有企業進行了以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并根據我國國有企業國有股獨資、獨大的特點,仿效德日等國家,設置了現行的法人治理結構,又仿效英美模式補充了獨立董事制度,但實踐證明,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的長期存在,現有法人治理結構模式不能很好地解決兩權分離下產生的委托—代理問題,因此,有效解決前述問題,成為我國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能否充分發揮作用的關鍵。
一、我國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仍存在的問題
我國國有企業目前的法人治理結構并不能很好地解決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下的委托—代理問題,也不能解決公司內部的權力分配,主要原因就在于與西方企業不同,我國的國有企業需承擔經濟責任、社會責任以及社會責任,不能簡單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單一目標;在多責任要求下,我國國有企業存在股東缺位、代表股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主體行政化以及外部董事職能弱化、經理層官員化、缺乏激勵和約束等一系列治理問題。
(一)國有企業股東缺位導致內部人控制嚴重
國有企業的股東缺位,全體人民通過政治授權的形式委托國家代表人民來管理國有企業,而國家本身也是抽象的主體,只有通過層層轉委托的形式來行使國有資產的所有權,由此形成了復雜的委托—代理—轉代理鏈條。
代表全體人民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由于并不能享有企業利潤的分配,導致其對公司經營者監督的內在動力不足,怠于行使股東權利,因此,無法形成德日模式下大股東對公司的有效控制,而多數國有企業的外部董事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內部董事又在經營層兼職,出資人代表與公司經營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突出,公司經營者實際上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權,委托—代理關系失衡,形成了內部人控制的局面。
(二)國資委履行國有企業出資人職責不足
股東缺位下,面對內部人控制問題,履行國有企業出資人職責的主體—國資委不敢完全放開授權經營,導致“管人、管事、管資產”存在不足。由于作為股東的管理經驗有限,國資委又經常混淆了出資人職責(股東權利)和國有資產監管職責(行政監管權力),在行使股東職責時,慣用行政思維、行政手段來行使股東權利,政企不分問題嚴重,導致股東對法人治理參與行政化,不但干預企業管理者的長遠發展戰略,甚至直接參與企業人、財、物的管理,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
(三)法人治理中的“三會”未形成有效制衡
董事會、監事會的弱化,導致企業黨組織權力的強化,部分企業黨組織甚至直接越過三會,不履行基本的程序,直接參與經營管理,用黨組決定代替三會、經營層決議的現象比比皆是。而在國有控股公司中,作為大股東的國有獨資公司往往控股超過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導致其擁有對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其他中小股東無法實際參與公司的經營決策和選擇經營者,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以及經營層完全被大股東控制,中小股東的利益極易受到侵害。
二、國有企業堅持黨的領導是法人治理的內在需要
我國國有企業委托—代理問題不能在現有西方法人治理結構框架內解決,我們必須找到新的主體對中國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進行補充完善。以新加坡為例,我國在國有資產規模、市場化程度、政府管理的理念與體制、國有企業的責任等方面與新加坡有較大差異。新加坡建立了國際化、市場化的高管薪酬體系,在我國還無法實施模仿。
過往,我們習慣于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治理模式通過組合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國外法人治理中沒有政黨的地位,由于同時存在著結構驅動型路徑依賴和規則驅動型路徑依賴,“過去”一直影響著“現在”的法人治理,所以作為模仿的我們對企業黨組織的地位和作用也總是諱言。
觀察我國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現狀,我們發現企業黨組織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雖然一直在政治上強調、在工作中踐行,但其在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卻一直沒有明確,學界也沒有對此進行過系統研究,因此,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有必要在法人治理結構框架下對國有企業中黨組織的地位、作用進行研究,以構建基于中國國情的新的法人治理模式。
《公司法》要求企業設立黨組織。實質決定形式而不是形式決定內容,必須考慮企業黨組織的地位、作用,這是國有企業的現實情況,不從現實的情況出發去研究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照搬照抄西方的治理模式往往導致法人治理最終無法有效運轉。
此外,堅持黨的領導是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從操作層面而言,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必須在法律的規定下進行,依法治企也要求法人治理結構中對黨組織的地位、職責范圍、履職程序予以明確,否則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將脫離法治的軌道。
在中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導致民營股份的加入,肯定會要求原有的國有獨資企業沒有股東會的治理結構必須調整,股東會必須成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關,從而形成既要充分保障民營股東的權利也要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制衡機制。
【參考文獻】
[1]馬克·格爾根:《公司治理》,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
[2]徐大立、趙國杰、李廣海:《國有企業法人治理模式研究》,《上海經濟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