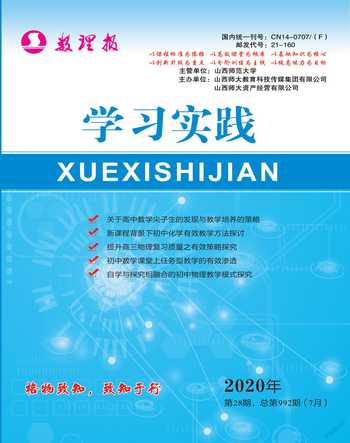淺談文人與醫學
張士娟
1924年1月17日,魯迅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上說:“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重要些,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士兵不可一樣。”
魯迅主要用這句話來闡釋天才和環境的關系,可他卻勾起了我對有關文人問題的思考。我常想,文人是否也有自己的一方土壤呢?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人們常說憤怒出詩人,正如官場只會磨出政客,商場只會產生商人一樣,文人也應該有孕育它的一方土地。
我想淺談的是文學與醫學的關系,當然這一點也還是從魯迅先生那兒得到啟發的。
魯迅為了醫治受難的國民,曾經“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生。”專程去日本學習醫術。后來他覺悟到國民最需救治的是心靈,從而棄醫從文。他明知“惟黑暗和虛無乃是時有,卻偏要向這些做絕望的抗戰。"在中國魯迅的文學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學醫的初衷是為了治病,從文的目的也是為了救人。學醫的人看到人生老病死的機會較多,更容易體會到人性的復雜與多樣,從而激發他們的思考,進而把這一思考付諸筆端,專業不對口在這里毫無影響,正如朱元璋開始是做和尚,后來卻黃袍加身一樣。同樣,郭沫若在長期的留學生涯中,也是選擇了學醫的,盡管我并不喜歡他。與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相比,中國當代的寫手們不必再向前輩們那樣,為了國家民族的危亡而吶喊彷徨,可這時的醫學仍然與文學有著不解之緣。如果不是對醫學知識爛熟于心,諶容不會寫出《人到中年》;畢淑敏不會寫出《預約死亡》;同樣池莉的《太陽出世》也是在她親自為產婦接生后,在看見旭日東升的那種震撼下醞釀出來的。醫學對文學有著良好的啟發作用,盡管有很多二者兼備的人,并沒有像魯迅那樣主動探尋二者的關系,他們幾乎都是在寫作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受其影響的。讓我們來看一看契訶夫,他畢業于莫斯科大學醫學系,醫生工作對契訶夫的文學活動有著良好的影響,他說“學醫對于我的文學事業有著重大的影響,它大大擴大了我的觀察范圍,充實了我的知識。"
上中學時,我看到過一則小故事,福樓拜對自己的徒弟莫泊桑說:“你要注意觀察周圍的事物,總有一天你會成功。"認真觀察是福樓拜成功的一大秘訣,在外國文學史專題講到他時,我發現福樓拜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外科醫生兼院長,它對事物縝密細致的觀察,是接受了父親實驗主義的傾向,而他后來在創作中表現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以及對宗教格格不入的思想,與他青少年時代所生活的憂郁而嚴肅的醫院環境不無關系。可以說,盡管他并不見得精通醫術,醫學還是促成了福樓拜的寫作風格的形成。再讓我們看一下濟慈,這個英國浪漫主義撒旦派詩歌的代表人物,他曾在23歲時一天早飯后,用了不到三個小時的時間,就把一首聞名于世的八段八十行的《夜鶯頌》一揮而就,他說:“我覺得學醫一點也不會影響我寫詩,我深信這一點,因而為了沒有把我的醫書丟掉而高興。"雖然他沒有用醫學知識來好好保護自己的身體,25歲時就死于嘔血;雖然他作為醫者,明知其危害卻還要吸食毒品來激發自己的創作激情,我始終都堅定的認為并不是醫學沒有能夠拯救詩人濟慈,而是在他,死亡的確是一種解脫。“人間真不值得留戀,去吧去吧。"正如蘇格拉底臨行前所說:“我死去,而你們活著,我不知道哪個更幸福。"
對于他們來說,寫作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宿命。他們是如此的對這個世界有所感悟,而世界卻以文學擁抱了他們,我想他們唯有感恩。他們的成功無疑是幸運的,可是與他們的奮斗肯定也有很大的關系。
想要喬木和好花,準備好了再好的土壤也還是不夠的,同時還要有好苗子,不知道您是否也心有戚戚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