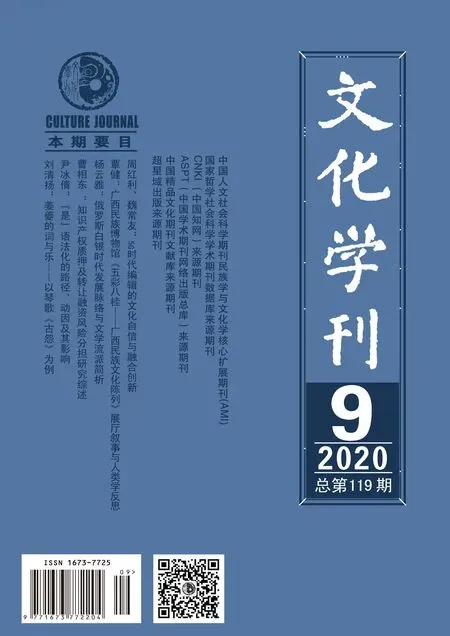歙縣長慶寺塔建筑藝術初探
劉立冬 蔣晴晴
塔在東漢時期隨著印度佛教文化的傳播而傳入中國,早期具有鮮明的宗教象征意義。隨著佛教中國化的發展,塔的象征意義產生了變化,有了宗教之外的文化意味,例如與傳統堪輿文化融合后產生的裝飾河山、點化堪輿的作用以及與傳統園林藝術融合后產生的美化園林、登高眺遠的作用等。可以說,與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相伴的是中國古代塔建筑離開幽深廟宇、走入塵世的過程,中國古塔既表現出古人對佛教文化的推崇和信仰,也洋溢著世俗人情的詩意光輝,是佛性和人性的交融。

漢 云紋 華陰縣 華倉遺址采集
中國古塔研究可以從多個維度展開。從建筑形態來看,不僅單個塔體的樣式各不相同,古塔的組合形態也大相徑庭,有單塔、雙塔和三塔之分,甚至有更多單塔構成的塔林;從建筑的選材來看,可以分為木式塔、磚石塔、磚木混合塔、琉璃塔和鐵塔等不同材質的塔;根據塔的結構形態與外觀造型,可以將塔的建筑結構類型分為樓閣式塔、密槽式塔、亭格式塔以及喇叭塔等[1]。本文將以安徽歙縣長慶寺塔為研究對象,研究其選址布局中的堪輿文化因素與建筑藝術。
一、長慶寺塔概述
古代徽州人為了祈福免災,在徽州地區建造了很多佛龕寺廟。有寺必有塔,一般塔的位置都位于寺的前面,也有的位于寺的側面或者后面。塔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徽州地區以佛塔和堪輿塔居多。在徽州眾多的寺塔建筑中,以歙縣寺塔最為著名。據記載,歙縣建寺廟最早在晉代,到唐宋時期逐漸繁盛[2]。
長慶寺塔位于歙縣徽城鎮練江南岸的西干披云峰麓,下臨練江,自古以來就是古城秀麗的風景名勝區。1981年9月,安徽省政府公布長慶寺塔為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3月,長慶寺塔被國務院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舊有寺院二十四座,僧房經閣,飛跨巖谷,至宋淳熙中,尚存寺院十五六座;到了明代,僅存十座,因此西干又名“十寺”[3]。歲月悠悠,西干十寺已蕩然無存,只剩長慶寺塔巍巍矗立青山綠水之間,作為西干山曾經佛事興盛的見證。
清乾隆年間,長慶寺塔頂被風雷暴雨折壞,墜入練水中。程瑤田根據折落塔頂上有“大宋重和二年正月”鑄字推斷,重和二年(1118)為始建開工年,宣和三年(1121)是塔完工的年份[4]。長慶寺建成時,有村人在山門與淑芳臺前建造七級方塔,人稱長慶寺塔。由于戰亂和損壞的原因,長慶寺塔歷代有修葺。清康熙《徽州府志》記載:“明朝泰昌元年的三月朔,黃備張氏集資修塔。”民國《歙縣志》述:“元天歷元年、明成化間張族兩次重修,萬歷末張大晉復倡族人修之。”自宋宣和至明萬歷年末五百年間,黃備村張姓族人不斷集資修繕長慶寺塔,使得這一千年古塔保存至今。1979年,塔基土層被切削,佛塔岌岌可危,經安徽省人民政府撥款,歙縣人民政府施工砌筑了護基大坎,并且一同砌筑了游覽蹬道與修復塔身。
長慶寺塔塔身共七層,是一座樓閣式磚木混合結構實心方形塔,沿襲唐代建筑風格。第一層有券門回廊,顯得比較高,石檐柱間寬4.33米,四面都辟有券門,門洞中空,內有石雕蓮瓣佛座,旁邊嵌民國二十五年(1936)重修碑記。塔身總高23.1米,底層是用青石制作的須彌座,共五層,上承一層塔檐石柱,邊長約5.28米,高2.34米,其束腰部分高66厘米,有間柱、角柱,都是民國時期所修。長慶寺塔砌磚用有黏性的黃土膠泥連接,塔磚尺寸規格為31厘米×17厘米×5厘米,這種尺寸的塔磚在堆砌時可以增加表面的接觸面積,從而使塔身甚至整個塔體趨于穩固。
長慶寺塔的層高沿襲了傳統中國塔的建筑形式,第一層比上面各層都要高一些,自下而上呈一個逐層遞減的建筑結構方式。第二層以上,每層墻面均凹進一券窗式佛龕,四隅方形交椅柱半隱半露,柱頭作方形櫨斗,凹入的門券內部繪有一尊彩色佛像圖案。塔身上嵌有數方明代重修碑石,頂部有鑄鐵葫蘆形狀的塔剎頂,四角分別用鐵鏈系牢穩固,各飛檐、翼角下懸鐵制風鐸。無論是遠望還是近觀,長慶寺塔給人的感覺都是古樸端莊、簡潔大方。塔檐向四周伸出的翼角下,懸掛和裝飾著若干鐵質的風鐸。微風拂過,風鐸便會叮咚作響,悅耳動聽,使人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此塔矗立山腳倒映于練江,為素練添秀,為行人指迷,宏偉秀麗,已近千年。
徽州地區的古塔遺存不多,且大多數為六角形或者八角形寶塔,長慶寺塔是當地存世極少的方形佛塔。該塔既保留了唐代塔式風格的風韻,又體現了鮮明的南方宋塔風格,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因此,塔的風格建筑與城市的人文氣息密切相關。長慶寺塔以優雅的姿態,點綴著歙縣優美的山水風景,塔的建筑與自然風景渾然一體,成為文化名城標志性建筑之一。
二、長慶寺選址布局中的堪輿文化因素
在古代佛教的建筑中,佛寺和古塔的選址相互聯系,密不可分。佛教是一種起源于古印度的外來宗教文化,從佛塔建筑的選址布局中不難發現中國傳統堪輿文化對佛教文化的影響。在堪輿學說和古代玄學中,風、水、氣是堪輿先生主要考量的客觀對象[5]。有生氣或靈氣的地方應該具有山清水秀、避風向陽、四面環山、潺潺流水、鳥語花香等特點,這種地方象征著人杰地靈。因此,根據傳統堪輿文化中的記載,塔和寺廟的選址應該尋找一些既靠近水又環繞著山脈的地方,形成一種“金城環抱”的氣勢,這樣才能體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統一。
在中國傳統堪輿文化中,建筑選址要有水環抱,后有靠山的屏障,左右兼具砂山環抱,四周山清水秀,又有青龍、白虎等四神獸作為方位神靈鎮址,各司其職保衛著古代城市、村落、民宅。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受到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佛寺在選址方面受堪輿文化影響,發展出“四靈獸”的選址原則,要求在建筑的四周形成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和后玄武的模式特點,而后山要四面環抱,并呈現層層展開的結構,且周圍的山脈都要朝向中心建筑。
只要符合以上特點,就可以稱之為“四靈地”。“四靈獸”成為佛寺選址原則,是佛教與道教的融合在建筑文化中的體現。這種追求和信仰與佛教所追求倡導的靜修教義及佛教徒的生存息息相關。因此,一般單個建筑都以方正的長方體建筑為主,其他結構的建筑為輔,整個建筑的堪輿群都要依靠著山脈的走向依勢來建。其實,借助堪輿確定寺址和塔址的例子有很多,雖然沒有明確歷史文獻記載長慶寺的選址是否受堪輿文化影響,但是觀察它們的形勢,分析它們隱藏的藝術“密碼”,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佛塔的選址與佛寺的選址緊密相連,一般佛塔建在寺廟的前面。盡管佛教標榜著“凈法以界身,大悲愿力,去來不落于常情”,佛教圣徒卻仍然為自己的寂滅之所大費心思,這同時說明堪輿文化對佛教塔寺建筑文化的沖擊和滲透。
三、長慶寺塔建筑藝術中的磚雕石刻與壁畫藝術
長慶寺塔下是一高大的石制須彌座,基座隨塔身呈四邊形,沿襲了唐代塔類建筑的須彌座風格。有關須彌座的記載,最初來源于印度的古代傳說。在傳說中,須彌座就是世界的中心,塔用須彌座做基底,不僅能降低塔的重心,而且能彰顯佛偉大且神圣的形象[6]。
塔身的第一層四面分別開有券洞,洞內藏有雕刻的佛像。目前,佛像已丟失,但依然可見塔內有石砌寶座,寶座四周雕有蓮花圖案,精致美觀,體現了古代匠人精湛的雕刻藝術[7]。塔身第二層外壁四周繪有精美的壁畫佛教藝術,均系宋代以后修葺時補繪。第二層以上的塔身,墻面中間設有隱出的窗券,各邊砌出半藏半露的方形角倚柱,用柱頭砌磚,狀如櫨斗。飛檐用磚疊澀法挑出,上覆以瓦筒,并間以五層斜角牙子,形成美妙的磚砌圖案。除翼角下懸有鐵制的風鐸,每層飛檐下仍懸有二至三個風鐸[8]。
長慶寺塔剎整體造型呈倒葫蘆形狀,塔剎基用方形石制成,塔剎身似圓形,上大下小,塔剎頂呈錐子形,四周掛有風鐸,并用鐵索鏈固定塔剎。微風拂過時叮咚作響,悅耳動聽,四野可聞。長慶寺塔內的壁畫藝術分布在一層到七層的壁面與天頂部分,每一層塔的四面墻上都繪制不同的人物圖案。經過長時間的風雨洗禮之后,墻面上的壁畫風化較為嚴重,塔中的每層壁畫墻面下方均有脫落現象。此塔壁畫藝術中所采用的繪畫媒介都是以天然礦物質顏料為主,主要是以藍銅礦、朱砂、石綠等天然礦石制作出來的顏料。塔內的圖案紋樣可以分成兩大類型:第一類是中國傳統裝飾紋樣,通常繪有祥禽瑞獸、卷云紋、植物花紋等各式紋樣,這些壁畫藝術風格紋樣主要圍繞佛像等圖案進行描繪,主要使古塔中的建筑藝術風格變得燦爛絢麗;另一類壁畫藝術主要是描繪佛像的寫實風格,內容均為佛教題材,主要圍繞佛像、仕女、菩薩、天王、高僧、官員等人物圖案進行描繪[9]。
佛塔的第一層壁畫藝術檐下繪有祥云瑞鶴圖案,墻面上繪有三世佛造像,袒胸露臂,面相慈祥圓潤,儀態莊重,烏發肉髻,雙耳下垂,雙手呈環抱形狀自然下垂至腹部,左掌疊放在右掌上,雙足交叉盤坐于蓮花寶座的中央。佛塔的第二層其中一面墻壁繪制了三尊菩薩像,中間一位菩薩像身披袈裟,由于時間比較久遠,面部以及衣服的色彩保存得不夠完整,下半身損壞較為嚴重,已經很難分辨出儀容姿態。另外一面墻壁上繪有三種不同人物畫像,中間畫像繪制的是一尊菩薩像,面部圓潤,眉毛纖細,沿襲了唐代人物壁畫的造像風格。右側繪制的是一位站立的僧人,手持禪杖,身披袈裟。根據推算,左側繪制的應該是一位帶帽子的佛教弟子畫像。越往高層,墻面的壁畫損壞現象就越嚴重,有人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頂層有維修題記一方,應有年款,但已被后期修復痕跡所覆蓋[10]。
塔內的壁畫藝術損壞極其嚴重,其中墻面有大量劃痕和現代人各式各樣的涂鴉。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墻面被撬走或者脫落不知所終,多處見到黑色墨水涂畫或刻畫的人名,嚴重破壞了塔內壁畫藝術的完整性。
四、結語
長慶寺塔不僅代表北宋時期的建筑特色,給后人留下豐富的歷史資源,同時彰顯了古人對塔式建筑審美觀念和造型藝術的認知。長慶寺塔是歙縣現存古建筑中最古老的建筑,研究長慶寺塔建筑形態,必須要從歷史文化背景以及自然生態環境入手,再回歸到長慶寺塔的歷史時空維度中去。由于歷史文獻和當地縣志資料缺乏,對長慶寺塔的內在藝術形態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