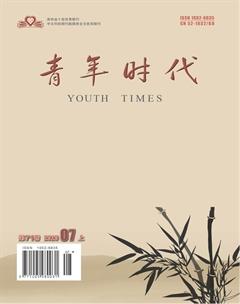論我國無差別犯罪的成因及防治
張喻佳

摘 要:無差別犯罪的頻發,預示著我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更為復雜的緊張階段。區別于其他犯罪,其具有選擇對象上的隨機性和犯罪動機上的社會不滿性,實質是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的宏觀環境下,社會控制弱化及個體心理畸形的綜合產物。應當建立一個從宏觀上完善二元化社會結構、中觀上實現綜合網狀式的社會控制、微觀上強化個體心理矯正的多維度防控系統,以有效打擊該類犯罪。
關鍵詞:無差別殺人;綜合動因論;社會控制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社會轉型進入新時期,各種社會矛盾集中涌現。犯罪作為社會的“晴雨表”,也隨之進入一個更為復雜的歷史階段,無差別犯罪頻發就是其重要表現之一。2018年11月,一男子于建昌小學門口駕車沖撞人群,致6名兒童死亡;2018年10月,劉某在重慶幼兒園門口持刀隨機行兇,致14名學生受傷;陳水總縱火案、冀中星爆炸案……一系列帶有強烈社會不滿性以及選擇對象隨機性的無差別殺人案件,徹底顛覆了傳統犯罪模式,打破了犯罪主體與犯罪對象常有因果關系的這一常理,造成了全國范圍內的恐慌。隨著該類案件頻發,有必要就其展開討論:無差別犯罪是什么?其成因為何?應當如何進行有效防治?筆者將就此逐一提出見解。
《法制日報》駐日記者張超首次提出“無差別犯罪”概念。隨后,張小虎教授指出其為“并無犯罪組織依托的行為人,出于社會不滿情緒,針對不特定的被害對象,采取具有較大殺傷力的手段,肆意殺害無辜他人,造成一定社會恐慌的刑事違法行為”[1]。該類犯罪特殊的成因體系使之衍生出與其他犯罪不同的“個性”。筆者認同上述觀點,并在此邏輯前提下展開論述。
二、多重維度下解析無差別犯罪之成因
“個體犯罪原因是由若干主體因素之間、主體外因素之間以及主體內外因素之間互相作用而成的網絡結構,是特定時空條件下,受復雜的生理與心理、個體與社會互動影響的綜合產物。”[2]不同于傳統犯罪,無差別犯罪具有其特殊性質,因此通過綜合動因論視角,對其進行多維度地剖析具有重大意義。
(一)宏觀社會結構維度
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社會成員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迫切,共同認可的文化目標變高,但達到該目標的機會并不相等,社會失范隨之產生。其一,二元經濟結構下,激烈的就業競爭和經濟波動導致失業人員數量增加,資源和自身條件的限制導致階級固化,阻塞底層人民向上流動的通道,增加其被剝奪感,使其陷入思維沼澤;其二,不完善的就業、醫療等社會保障成為其誘因;其三,群眾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通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從冀中星爆炸案等可以看出,執法人員存在大量相互推諉、搪塞群眾等問題,合理訴求得不到滿足促使事態惡化。
(二)中觀社會控制維度
其一,社會排查、預警功能滯后,忽略“危險信號”。馬永平曾在案發前預告“寧夏銀川公交車的幾點火光……”,若加強網絡排查力度,及時捕捉到潛在危險,予以約束,便能有效防止犯罪行為;同時,缺乏對重點人群的信息掌控。如陽贊云在9·12駕車殺人前已犯下六次罪行,公安機關知其存在危險,但松懈了后期跟進,間接放任犯罪發生[3]。其二,社會支持不足。犯罪人缺乏同社會的良性互動,產生強烈的社會拋棄感,對于顯性矛盾,外界未引起足夠重視,導致其化解緊張的功能弱化,如鄭民生在辭職后多次求職未果,周圍人透露明顯感受其內心厭世情緒擠壓,但未及時對其進行疏導。其三,輿論控制不當。該類犯罪呈現出較強的示范效應,如成都公交車縱火案發生后,受到媒體肆意報道,此后全國多地發生數起同類型案件,在作案手段上有極高的相似性。此外,由于輿論較強的煽動性,媒體的不正向引導往往導致群眾“同情泛濫”,而忽略了犯罪是不可饒恕的,成為犯罪助推器。
(三)微觀個人維度
筆者認為,犯罪人在受到挫折后之所以將矛頭指向與自己無因果關系的群眾,原因有兩點:其一,犯罪人往往深受社會多重壓迫,持續多方的壓力使其淡化對某個具體矛盾的關注,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憤懣;其二,個體因素的差異,如認知缺陷導致犯罪人逃避自身能力問題而一味地將失敗歸咎于社會的不公。
沒有一個人只是單一地受到外部影響而走上歧途的,犯罪行為的發生必須經過個體因素的中介、加工和轉換。首先,心理因素是犯意誘發的重要條件。從認知方面來看,淺薄的認知水平不足以支撐犯罪人做出正確的是非判斷。從情感方面來看,無差別犯罪人性格往往沖動暴躁、嫉妒心強、嚴重缺乏社會責任感。從動機方面來看,無差別犯罪人易被邊緣化,缺乏來自社會的認可和重視,以致內心扭曲,甚至企圖通過掀起極端暴力犯罪來吸引社會關注;同時,行為因素對犯意的發酵有一定影響。秋葉原殺人案犯罪人加藤自童年起就沉迷于各種網絡暴力游戲,長期不良活動對其犯罪心理有著潛移默化的補強影響;衡陽駕車傷人案罪犯陽贊云于之前已犯下六次罪行,犯罪行為的養成導致其對法律權威的無視。
綜上,無差別犯罪成因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和層次性(如圖1所示),即“個體之所以走向犯罪道路,是由主體內外因素形成有機整體后共同決定的,而并非各自孤立地發揮作用”[4]。無差別犯罪人作為弱勢群體,在二元結構環境下,因文化目標與現實情況的巨大落差,產生失衡心理,并在發泄渠道匱乏和社會控制滯后的情況下逐漸發酵,直至實施失范行為。整個過程中,各因素之間互相聯結作用,不同程度地推動著犯罪產生,構成多維度原因系統。
三、無差別犯罪之防治
(一)宏觀層面——完善社會結構
首先,采取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分配制度,促進社會合理流動;其次,加強公共服務建設,高覆蓋基本最低生活保障、工傷、醫療保障服務,其中充分發揮非官方機構的支持作用,鼓勵創建各種民間慈善機構和弱勢群體志愿幫扶;同時,疏通信訪、聽證等群眾利益表達渠道,減少“堵訪”等現象發生,提高執法效率和透明度,切實做到“執法為民”。
(二)中觀層面——強化社會控制
1.事前強化風險預警、提供社會支持
首先,強化風險排查與預警。無差別犯罪凸顯出一定的工具性,應建立犯罪排查及預測機制,調動社會控制從被動防御、事后補救到主動出擊、全面預防。公安部門、學校、社區等應形成立體式防控系統,及時捕捉潛在犯罪信息如矛盾糾紛、危險言語等,加快信息傳遞。其中,公安機關應盡快構建以情報部門積極發現、治安部門日常檢索為主導的綜合作戰模式,全面搜集犯罪信息,并以危險程度分級預警。洛杉磯警局和Palantir扎根于警局實際辦案情況和警務經驗,結合Gotham技術,搭建了一套語義搜索比對平臺[5],以排查出網絡上的反人類、反社會等“危險信號”并作出迅速反應,阻止了多起犯罪案件發生,為我們展現了一套值得借鑒的反極端暴力犯罪的智慧方案。其次,充分提供提供社會支持,致力于構建起以政府支持為基礎,以社區、家庭支持為重點,其他慈善組織、社會機構為補充的綜合支持網絡。目前,北京等地正在探索“社區青年匯”式的復合性組織體系,以加強對青少年、尤其是流動青少年的社會支持。這種以共青團為樞紐的地域性活動平臺,實現了青年同社會之間積極包容的良性互動,為流動青年提供了“社會支援”和“社會約束”,疏通了青年的訴求表達渠道,防控效果顯著[6]。
2.事中快速反應、多方響應
其一,公安機關應積極發揮主導作用,加強人才隊伍和警用裝備建設,加快由“人控”向“技控”的轉變。提高現場反應能力和安保工作質量,同時,加強對重點場所、單位的外部巡邏和重點防范、對交通工具的進出口把控、對可疑人員和隨身攜帶物的檢查。其二,重點場所、單位、區域應加快形成專業防控隊伍,加強人員素質建設,引入先進防控技術,充分發揮其自防作用。其三,形成大社會范圍的信息共通、高效到位、一處造襲多方響應的聯動格局。衡陽市構建“校園警務室、治安室和流動警務崗亭”三級治安防控網點,實行校園周邊全面巡邏機制,有效提高了應急處置能力。美國巴爾摩市于2005年啟動了“學校——家庭——社區的防控項目”[7],由家長、教師、高年級學生、社區代表組成行動小組,并組建老人志愿巡邏隊,取得了較為理想的防控效果。
3.開展日常防控建設,加強法制與輿論建設
其一,2006年,我國頒布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而無差別犯罪此類重大突發安全事件,尚未納入預案。鑒于該犯罪的高發態勢,應盡快將其納入預案;其二,加強對傳播行為的規范,加快制定重大突發事件報道準則,并建立起嚴格的問責制度。此外,還可以通過先進技術進行實時監管,美國推出了一款名為RumorBot(謠言機器人)的軟件,該軟件可通過搜索引擎和數據庫跟蹤謠言[8],防控效果顯著。最后,應擴大官方媒體的影響力,占領輿論高地,正確引導在全社會形成犯罪不可饒恕的共同認知。
(三)微觀層面——深化個人心理矯正
斯皮羅提出,個人與社會是雙向反饋的關系,只有當外界文化深化為個體動機時,才能發揮好社會控制的作用,主要包括:外部控制、內化控制[9]。首先,建立起集危機排查與評估、心理矯正、危機跟蹤和能力培養于一體的外部心理干預網絡。危機排查即通過專業檢索,鎖定危機人群;危機評估即對個體是否處于危機狀態及嚴重程度的評價;心理矯正即在前基礎上分級管理,有側重地提供心理治療服務,進行糾正;危機跟蹤即多次進行評估,直至不良心理不具備再生條件;個體能力培養即幫助個體切實提高調節情緒的心理能力,實現真正的心理成長。基于上述步驟建立起來外部心理干預系統,可引導個體其重現健康心理。其次,強化社會認同,推動內化。伴隨著集體主義的彌散,對個人主義的過分崇尚,導致個體陷入極端利己主義沼澤。筆者認為,個體通過社會控制有效進行自我約束的前提在于,其對所在社會及建立起來的社會規范和價值體系所持有的高度認同。因此,應強化社會認可,加快形成新的集體意識。
四、結語
伴隨著社會轉型的迅猛發展,無差別犯罪案件大量涌現。總之,該類犯罪的自身特性決定了其形成原因的錯綜復雜性,即其產生是由于社會結構、社會控制、個體心理因素三重維度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某個因素獨立決定的,呈現很強的整體性和層次性。因此,應基于此構建起全面、立體的防控體系。我們期待,通過對其成因及對策的解讀,能遏制此類犯罪的發生,維護社會安全與穩定。
參考文獻:
[1]張小虎.我國無差別犯罪的現實狀況與理論分析[J].江海學刊,2011(1):125-130,239.
[2]王志華.犯罪綜合動因論[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3):101-104.
[3]張雨,陳羽.衡東“9·12”惡性案件嫌疑人被批捕[EB/OL].(2018-09-16)[2020-07-01].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8/0916/c42510-30295948.html.
[4]王志華.犯罪綜合動因論[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3):101-104.
[5]宋祥斌.基于大數據的極端暴力犯罪管控系統設計[J].電子技術與軟件工程,2019(20):166-167.
[6]常宇.基于社會關系重構的城市青年服務管理模式創新——北京市社區青年匯的實踐與探索[J].中國青年研究,2013(11):35-39.
[7]余中根.構建有效的校園安全防范的學校、家庭與社區合作機制——美國巴爾的摩市的經驗及其啟示[J].外國中小學教育,2010(7):50-54.
[8]成全,趙代博,張惠濱,劉碧強.微博傳播規律視野下的反腐倡廉策略探析[J].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7(3):52-57.
[9]向德平,田北海.轉型期中國社會失范與社會控制研究綜述[J].學術論壇,2003(2):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