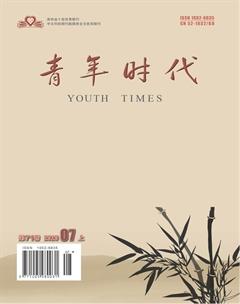兒童是誰:現代兒童觀的反思與重構
呂純卉
摘 要:“兒童是誰”的追問引起了人們對兒童個體和兒童精神世界的探究,對“兒童是誰”的回答將為思考“如何教養兒童”和“對兒童的需要如何回應”奠定基礎。“兒童”的概念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改變,在當今時代背景下,應充分認識到兒童具有特定的年齡范圍,兒童屬于兒童自身,兒童是具有獨特生理和心理結構的、獨立存在于社會文化中的個體。
關鍵詞:兒童;現代兒童觀;童年
一、關于“兒童是誰”的追問
(一)從“兒童是什么”到“兒童是誰”
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對兒童的探討側重于“兒童是什么”,即探討“兒童”共性的概念,力圖找出“兒童”群體的一致屬性,兒童哲學則從“兒童是誰”這一角度追問,探究兒童個體和兒童的精神世界。“兒童是什么”到“兒童是誰”這一提問方式的轉變,賦予了兒童個體鮮活的生命及其獨特的意義。
(二)“兒童是誰”是兒童哲學的根本性問題
“兒童是誰”是兒童哲學的根本性問題。馬修斯認為,“我們很難理解兒童是誰、兒童應是什么樣子等問題,原因可能在于童年對我們成年人來說有太多的意義。”童年之于不同時代、不同群體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從歷史的根基和社會文化背景出發,深入剖析不同時期、不同學科的兒童觀,探析“兒童”的概念,追溯兒童的本源和本原,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兒童,思考“兒童需要什么”和“我們應給予兒童什么”。
二、對“兒童是誰”的回答是兒童觀的折射
(一)成人對兒童的理解受到成人視角的局限
兒童觀是人們對兒童的看法和態度,而成人不是兒童本身,對于兒童的認識會受到自身視角的影響,不能代表兒童對于他們自身的認知,且兒童因其年齡較小,身心發展不成熟,需要成人特別的保護和教育而在其與成人的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所以,“兒童”這一概念被成人界定時,將無法避免地受到成人的認知模式、所處地位、身處的社會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影響,“兒童”未必是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成人對“兒童是誰”的回答折射了其所持的兒童觀。
(二)“童年”的概念在歷史中的演變
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講述了西方“童年”概念的變遷歷程。在原始氏族社會中,兒童被視為氏族部落未來的成員,學習狩獵、采摘等生存技能,“兒童”的概念在這一時期尚未被分化出來。古希臘時代,保留下的塑像沒有一尊是兒童的,國家對殺害嬰兒的行為也沒有任何道德或者法律上的約束等體現了“兒童”地位的低微,由此可以看出“兒童”的價值并未被人們所認可,但是,希臘人建立了“學校”,讓我們看到了專屬于兒童的“兒童期”的曙光。古羅馬時期,人們開始把成長中的孩子同羞恥的觀念相聯系,關于“兒童”的觀念有了顯著的進步。中世紀時期,隨著人們的閱讀和書寫能力下降,兒童開始在這個口語的世界中了解到屬于成人世界的秘密,與成人生活在同樣的社會范圍里,在此時期,傳播環境不能將兒童與成人分離,從而導致了童年的缺失。但是,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童年被“發明”了出來,印刷術創造了成年與兒童的定義——成年是有閱讀能力的人,兒童則是沒有閱讀能力的人。因此,印刷術通過限制沒有閱讀能力的兒童了解社會秘密的可能性,將兒童與成人相分離。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和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中,“個性解放,平等自由”與“理性”的呼聲影響人們對兒童的觀念,繼而涌現出一批關注兒童的教育家,新的兒童觀孕育而生,如洛克的“白板說”,盧梭的自然主義教育思想,承認兒童期具有其獨特價值的兒童本位觀敲開了現代教育的大門,福祿貝爾與蒙特梭利繼承發展了盧梭的觀點,提倡“以兒童中心”,杜威提出“兒童即目的”……尼爾波茲曼認為,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中期是童年的黃金時代,而到了二十世紀中后期,電子技術的發明與普及又讓兒童自如地進入到成人的世界,成人與兒童的界限再次被打破,“童年”開始消逝。
在中國,兒童曾被古代人認為是“小大人”,被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隨著時代的發展,近現代涌現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他們力圖打破陳舊的兒童觀,推動中國教育的發展。周作人在其作品《兒童的文學》中呼吁“應把兒童看作兒童”。陶行知繼承和豐富了盧梭的“兒童本位”思想,認為兒童是“活”的人。陳鶴琴也指出,兒童是獨特的、發展的應受到尊重的人。
縱觀東西方歷史,“童年”概念的發展漫長而曲折。隨著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社會分工日益細化,人們的關注逐漸從自然界、宗教信仰轉向人本身的價值,成人對兒童的認識日益加深,“兒童”的地位也在曲折中不斷發展。侯莉敏教授在《兒童的生活與教育》中指出,作為文化概念的“童年”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也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消失,這與每一時代的兒童觀緊密相聯。當一個時代的兒童有著很高地位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提童年的概念,而當一個時代的兒童沒有地位的時候,我們需要提出童年的概念,捍衛童年的概念。
如今,在生物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眾多學科的綜合發展下,人們擁有了全新的視角審視兒童,舊的觀念受到沖擊,新的兒童哲學正以恢宏的氣勢與強調成人本位的民間兒童哲學展開殊死搏斗。民間兒童哲學觀存在這樣的誤區:我們不把童年期看作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命期,兒童僅僅被看作是國家的未來,或被當作工具用以傳宗接代、光耀門庭,由此帶來教育上的誤區——揠苗助長和及早教育,而這種誤區背后的根源是物質文化與適應文化失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沖突的結果。現代化兒童觀需要被反思與重構。
三、反思與重構——兒童是誰
(一)兒童擁有特定的年齡范圍
即使成人可以保持一顆純真的童心,但他也不再是一名兒童,而是一位保有童心的成人。兒童有其專屬的兒童期,有特定的年齡范圍。國際《兒童權利公約》將兒童界定為18歲以下的人;中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規定0~18歲為未成年人;醫學界將0~14歲的兒童為兒科的研究對象;在兒童心理學中,初生至十七、十八歲都屬于兒童。可見,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兒童年齡范圍的界定也千差萬別。但是,兒童都有其專屬的年齡范圍。人的一生中蘊含了童年期,童年期一旦錯過,便不可重頭再來。
反觀當今部分父母不顧兒童的意愿和身心發展規律,急于將孩子送入培訓班,學習超出孩子年齡范圍可接受的內容,慣于用“能背誦多少首古詩”“畫得像不像”等標準衡量兒童,殊不知這些標準是成人為兒童設定的、是強行付于兒童的,未必符合兒童意愿與發展規律,這種現象背后折射的是“小大人”的兒童觀,成人沒有考慮到年紀尚小的孩子能否接受這些學習內容,違背孩子的意愿,期望孩子快速成長為知識淵博的大人,在他們眼里,童年是無價值的。
在兒童期,孩子應得到該年齡段應有的游戲與自由,成人若不承認兒童期的價值,一味地揠苗助長則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兒童本該享有的權利。
(二)兒童是兒童本身
無論成人如何作答“兒童是誰”這個問題,其回答都會受到成人自身視角的限制。學者龍寶新認為:“當我們說‘兒童是人時,兒童的世界從屬于人的世界;當我們說‘兒童是兒童時,兒童的世界從屬于‘兒童的概念;唯獨我們說‘兒童是自己時,兒童成了一個‘我,成了自己身體、生活和心靈的主人,兒童世界的豐富魅力隨之顯現。”這一表述充分體現了兒童本位的思想。盧梭曾表示自然教育的目標是培養“人”:“他既不是文官,又不是武將,也不是僧侶,他首先是人。”這種站在兒童的角度思考“兒童是誰”的主張,無疑給教育思想變革歷程上添上了濃重的一筆。
由“兒童是誰”引出的“兒童需要什么”和“我們如何應對兒童的需要”等問題皆需要成人破除成見,在豐富、科學的理論基礎之上與兒童共情,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
(三)兒童具有獨特生理和心理結構
一方面,兒童具有獨特的生理結構。兒童的發展是本性、遺傳和基因等兒童內部結構與父母教養、學校教育、社會文化等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十八、十九世紀,隨著兒童發展理論蓬勃發展,博爾曼、弗洛伊德、皮亞杰等心理學家開始對兒童進行系統全面地研究,皮亞杰提出“兒童的發展既是連續的,又是分階段的”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兒童心理發展的基本實質。另一方面,兒童具有獨特的心理結構。蒙臺梭利認為,兒童存在著天生的“吸收性心智”,用于吸收在他周圍世界中所發現的東西。
成人應當看到年幼的兒童身上具有極強的可塑性和驚人的發展潛力,把握兒童發展的關鍵期,為兒童發展提供適應性支持。
(四)兒童是獨立的個體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的生命存在被賦予了價值和意義。盧梭在《愛彌兒》一書清晰地指出:“在萬物的秩序中,人類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他的地位;應當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縱觀歷史上“童年”概念的演變,“童年”這一概念從無到有,兒童與成人未分化到逐漸分化,說明人們開始意識到并承認兒童期具有獨特的內在價值,折射了時代的進步。但當今我國部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仍為一股功利之風所左右:父母擅自做主,用課外補習班填滿孩子的假期;部分缺乏資質的民辦園為迎合家長的需求,不顧兒童身心發展規律,教授“小學化”的內容。這些現象背后隱射的是成人對兒童的控制與對兒童權利的剝奪,其本質是將兒童看作是成人的附屬品,不承認兒童是獨立的個體和童年期的價值,然而,脫離了兒童身心發展規律的教育是沒有意義的。
因此,兒童應當被視為一個個獨立的個體,有其獨特的想法和選擇,有其專屬的童年期與童真。
(五)兒童是存在于社會文化中的人
除了生物學意義,兒童還具有社會學意義。兒童自出生來到世上,生活無不受到社會的影響:向監護人和教師學習所處的社會文化;遵守班級規章制度;遵守國家法律……兒童親歷的世界屬于社會文化的領地,他們的生活無時無刻不受到社會文化的浸染,又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發揮主觀能動性,建設自己的精神世界。
一方面,成人不能強制地向兒童灌輸成人的觀念和社會規范,剝奪兒童的人生體驗;另一方面,兒童必須逐漸接受社會文明的道德原則,學會道德自律。我們應在成人良性引導與發揮兒童主觀能動性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平衡點。
參考文獻:
[1]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M].吳燕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2]侯莉敏.兒童的生活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
[3]盧梭.愛彌兒[M].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4]羅瑤.從“兒童的哲學”到“童年哲學”:馬修斯的思想進路及其啟示[J].學前教育研究,2019(7):21-31.
[5]單中惠.“兒童”是誰?蒙臺梭利如是說——蒙臺梭利對兒童身份問題回答之初探[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9,18(1):1-5,42.
[6]王雅楠.兒童是誰?——基于多元視角的解讀[J].文教資料,2018(17):167-168.
[7]羅蘭蘭.兒童是誰:兒童是獨立的自然-社會人[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8,38(5):1-2
[8]龍寶新.兒童是誰——重構我們的兒童哲學[J].少年兒童研究,2009(2):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