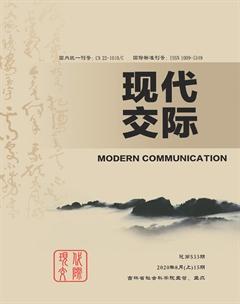韓非“以法代德”思想研究
冷汶倩
摘要:韓非依據(jù)戰(zhàn)國時期的“亂世”特征,以其“因時制宜”的發(fā)展眼光,提出了“稱俗而行”的觀點。他在批判儒家“德治”的同時提出了“不務(wù)德而務(wù)法”。他認(rèn)為“法”可以矯正不直,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德治”不再適用于當(dāng)下社會,唯有“法治”可以解救“亂世”危機(jī)。因此,以“法、術(shù)、勢”為一體的治國之道是達(dá)到理想社會的可靠途徑。
關(guān)鍵詞:德治 法治 不務(wù)德而務(wù)法
中圖分類號:B22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15-0228-02
戰(zhàn)國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jì)與社會結(jié)構(gòu)發(fā)生急劇轉(zhuǎn)變,是一個處于大變革的“亂世”時期。如何重建社會秩序、何以成為新型社會規(guī)范成為一個時代課題。韓非正是根據(jù)當(dāng)時的社會條件,提出有別于儒家“德治”的“法治”,為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重建社會秩序、君主的治國之道起到了指導(dǎo)作用。
一、時代背景
韓非生于戰(zhàn)國末期,此時在歷經(jīng)了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貴族勢力的激烈斗爭后,新興地主階級已基本在各諸侯國中取得了統(tǒng)治權(quán),但封建主貴族仍有強(qiáng)大的殘余勢力。因此出現(xiàn)了新舊勢力斗爭、諸侯割據(jù)的紛亂場面,征戰(zhàn)與兼并成為一項重要的時代課題。韓非處于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其思想的形成亦是時代使然的因素。
二、“稱俗而行”的社會進(jìn)化思想
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急劇的社會變革之下,先秦各家有著重要的理論建樹。關(guān)于歷史觀,出現(xiàn)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主張“法先王”的觀點,另一種則是以韓非為代表的主張變法革新的觀點。韓非在對歷史與傳統(tǒng)的分析中,提出了“稱俗而行”的社會進(jìn)化思想。他認(rèn)為時代是不斷向前發(fā)展的,治國理念也應(yīng)當(dāng)隨之改變。那么,韓非的歷史觀究竟如何?其與先秦儒家的歷史觀究竟有何差異?這為我們進(jìn)一步探索韓非思想留下了一定思考的空間。
儒家學(xué)派的孔子認(rèn)為現(xiàn)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都源于人們拋棄了古代社會的美德。他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54“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1]164-165在孔子看來,夏商周三代是美好的小康世界,現(xiàn)在社會的問題癥結(jié)在于缺乏德、禮的教化,因此他主張用仁、義、忠、孝等道德來教化人們,以期恢復(fù)到小康世界的美好社會。孟子與孔子一樣,他堅持復(fù)古觀并認(rèn)同“以德服人”。他提出:“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nèi),必為政于天下矣。”[1]288孟子的復(fù)古觀則更為鮮明,他認(rèn)為“文王之政”是“為政于天下”的基石。同時,他對于“以力服人”與“以德服人”有著深刻的見解,他提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236-237“力”即土地甲兵之力[1]236。他認(rèn)為“以力服人”實屬霸道治國,使民“心服”而“力不贍”;而“以德服人”可謂王道治國,使民眾心悅誠服。在孟子看來,“文王之政”猶如一個亙古不變的施政之方,“以德服人”是治國的長久之計,“以力服人”終將使人心生抵觸。他崇尚王道,而輕賤霸道。同為儒家學(xué)派的荀子,他的歷史觀存在著“法先王”與“法后王”之辨。他提出:“今夫仁人也……圣王之蹤著矣。”[2]97他認(rèn)為,堯、舜之制,仲尼、子弓之義,應(yīng)為今人務(wù)之。在他看來,行“仁人之事”便是明智之君的蹤跡。
而韓非提出的三世論,則與儒家學(xué)派孔孟荀三人的觀點有所不同,他主要從當(dāng)今社會現(xiàn)狀出發(fā),旨在論證“法治”的必要性,以解決現(xiàn)實中的問題。他的思想核心在于“異”與“變”,欲救“急世之民”,便不能用古代的“寬緩之政”,他力主“以力服人”與“不務(wù)德而務(wù)法”。時代變遷、事態(tài)有別,此謂“異”;根據(jù)事情的“異”,而采取不同解決問題的策略,此謂“變”。而韓非根據(jù)“異”與“變”,進(jìn)而提出“以力服人”。那么,韓非所言的“異”與“變”,主要依據(jù)為什么呢?
韓非對法家商鞅的歷史觀有所繼承。商鞅提出:“天地設(shè)而民生之……下世貴貴而尊官。”[3]商鞅認(rèn)為,“親親而愛私”將會導(dǎo)致“親親有別”與“愛私則險”的人際關(guān)系,這也是民亂的根源。因此,“立君”的概念應(yīng)運而生,便出現(xiàn)了“上賢廢而貴貴立矣”,即下世的“貴貴而尊官”。商鞅在承認(rèn)社會發(fā)展進(jìn)步的同時,從歷史發(fā)展的事實中提出不同的社會制度,他的觀點是變化與發(fā)展的。韓非繼承了商鞅的觀點,他提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dāng)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4]483-484韓非認(rèn)為,在上古之世,主要的矛盾為人民與禽獸之間的矛盾。因此,“構(gòu)木為巢”與“鉆燧取火”便能受民眾愛戴而王于天下;中古之世,“構(gòu)木為巢”與“鉆燧取火”則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鯀、禹決瀆”;近古之世,則需湯、武征伐桀、紂。在韓非看來,每個歷史時期都存在不同的社會矛盾,圣人應(yīng)根據(jù)當(dāng)代的實際情況而采取相應(yīng)的措施。并不是一味地仿照先王的政治原則,否則無異于守株待兔。韓非提出;“故罰薄不為慈,誅嚴(yán)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4]486在他看來,并不能因為懲罰的輕重、誅殺的嚴(yán)厲而評論“慈”與“戾”。政事會因時代的變遷而發(fā)生不同的轉(zhuǎn)變,因而君主應(yīng)采取不同的措施以適應(yīng)政事的變化。“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故曰‘世異則事異”。[4]486韓非認(rèn)為文王施行仁政而治理天下,這只適用于文王之時,而并不是長久有效的治國之方。由此看來,韓非以辯證地眼光來看待“仁”,他并未否認(rèn)仁義,而是認(rèn)為仁義的施用在于時代的變遷。在時代變遷的潮流下,仁義不適用于當(dāng)下。因此,他提出:“夫古今異俗,新舊異備。”[4]487他認(rèn)為如果用古代的“寬緩之政”來治理當(dāng)下的“急世之民”,就如同沒有鞭子與繩索而去駕馭烈馬一樣。寬緩之政不適宜急世之民,正確的治國之道應(yīng)由社會的主要矛盾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那么,在韓非看來,以當(dāng)下的社會情況,應(yīng)當(dāng)如何治理國家呢?韓非提出:“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當(dāng)今爭于力。”[4]465他認(rèn)為古代社會可以“以德服人”,然而在當(dāng)今社會并不適用,當(dāng)今社會應(yīng)當(dāng)“以力服人”。他提出:“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故不務(wù)德而務(wù)法。”[4]504在韓非看來,“人之為吾善”者罕見,君主治國在于使人們“不得為非”,而并非“恃人之為吾善”。因此,他主張治理國家要采取適合于大眾的措施,致力于“法治”遠(yuǎn)勝于致力于“德治”。韓非否認(rèn)道德教化對于人們的作用,他認(rèn)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占社會少數(shù),他否認(rèn)“德”在現(xiàn)實社會普遍性的可能。因此,他反對在當(dāng)時的社會中依舊施行“以德服人”,他提出“不務(wù)德而務(wù)法”。
由此可見,韓非在批判不合時宜的復(fù)古觀的同時,提出“世異則事異”的觀念。韓非認(rèn)為,只有實行有利于促成大一統(tǒng)的政策,才能順應(yīng)時代潮流的發(fā)展。韓非的這種變化發(fā)展的歷史觀,為其主張“以法代德”的政治哲學(xué)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與思想武器,具有重大的進(jìn)步意義。
三、韓非的“法治”思想
韓非認(rèn)為,實行“法治”可以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他提出:“法者,憲令著于官府……此臣之所師也。”[4]433韓非所謂的“法”是由官府著出的“憲令”。何以解釋“憲令”?兩者關(guān)系如何?熊十力對此解釋道:“人主身總?cè)f幾,有其手定之國法朝章,是謂憲……憲令二者,總稱法,皆人主之所自出圣裁或集眾議而核定者。”[5]據(jù)此我們可以得知,“法”由“憲”與“令”構(gòu)成。“憲”是直接來源于“人主”而制定地普遍的“法”;“令”是由“內(nèi)外臣工”上奏“人主”,再由“人主”最終核定的“法”,屬于間接源于“人主”。“憲”與“令”兩者的結(jié)合,統(tǒng)稱為“法”。韓非提出:“一民之軌,莫如法。”[4]41他認(rèn)為,“法”的作用在于矯正不直,使人們的行為準(zhǔn)則整齊劃一。因此,“法”必然是要具有統(tǒng)一性的。關(guān)于法令不一的情況,他提出:“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4]433-434他以“晉之故法”與“韓之新法”為例,批評了法令不一的壞處,若是“故新相反”或“前后相悖”將導(dǎo)致奸臣有所辯解。他旨在說明“法”要堅持統(tǒng)一性,即“是以賞莫如厚而信……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4]489。韓非主張通過“賞”與“罰”來規(guī)范與引導(dǎo)民眾的行為,“賞”與“罰”便是君主實行“法”的兩種工具。但韓非并不主張君主可以隨心所欲地去使用這兩種工具,而是要堅持“法”這個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以“法”作為規(guī)范人們行為的準(zhǔn)則。
韓非在提倡運用“法”的同時,提出了與“法”相并列的“術(shù)”的概念,他認(rèn)為“法”與“術(shù)”都是君主治國所運用的工具。“術(shù)者,因任而授官……此人主之所執(zhí)也。”[4]433在韓非看來,君主可以通過“術(shù)”來考核臣下,從而依據(jù)臣下的能力來授以官職。“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wù)必知之術(shù)也。”[4]466-467君主要施用“術(shù)”使得臣子不得不忠于職守,而不是依賴臣子的自身品德。然而,臣子何以為君主所驅(qū)使呢?韓非將其歸結(jié)為“勢”的所在。他提出:“君執(zhí)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4]470韓非認(rèn)為,“柄”即“賞”與“罰”二柄,“勢”即生殺大權(quán)與控制群眾的資本。君主處于位高權(quán)重的地位,利用賞罰二柄便可以掌控民眾的言行。他強(qiáng)調(diào)“勢重者,人主之淵也……人主失其勢重于臣而不可復(fù)收也”[4]262。君主失去“勢”,便如同魚失去了淵一樣。權(quán)勢是由君主所獨自占有的,不可以假借于臣,也不可以與人共操。以此來避免臣子借君主的勢力來獲取自己的利益。這也是其政治理論的必然邏輯。因此,“勢”是最高的權(quán)力象征,是君主意志與利益的體現(xiàn)。而“法”與“術(shù)”是兩種具體維護(hù)君主“勢”的方法。“法、術(shù)、勢”為一體的理論則是韓非所提出的治國之道。
四、結(jié)語
韓非以其發(fā)展的眼光批判儒家的“德治”,批判不合時宜的復(fù)古觀念。他提出“以力服人”取代古代社會的“以德服人”。并在批判儒家“德治”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法、術(shù)、勢”為一體的“法治”理念,為君主的治國之道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參考文獻(xiàn):
[1]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新編諸子集成)[M].北京:中華書局,2012.
[2]王先謙.荀子集解(新編諸子集成)[M].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3]中華書局.四書備要第五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
[4]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新編諸子集成)[M].鐘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
[5]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5卷[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責(zé)任編輯:趙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