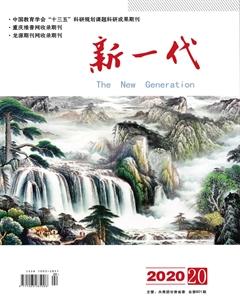閱讀教學中主問題設計的基本要求
曹建瑜
摘 要:當引導學生閱讀全文和解決生字新詞之后,通常就進入解讀文本的環節。如何正確、深入而又順暢地解讀呢?
關鍵詞:閱讀教學;解讀文本;問題設計
關于讀讀解讀文本環節有經驗的教師都會設計一個能貫穿全文的主問題,然后沿著這根線,抓住若干個點,一步步推進,一層層深入。主問題猶如一根長長的藤蔓,若干個點好比藤蔓上結出的葫蘆。這幾個葫蘆都由藤蔓牽引著、滋養著,藤蔓拐彎葫蘆就拐彎;藤蔓上爬葫蘆就跟上。這樣的文本解讀方式,叫線清點明,既有主線,又有重點。只有這樣解讀,文本才能順暢而清晰地深入到學生的頭腦里。在這里,主問題的設計和點的確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比較而言,還是主問題更重要些,或者說應放在更優先考慮的地位。主問題設計錯了,大方向偏了,點也肯定沒法正確選擇。綜觀當前的閱讀教學,我們發現,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比較普遍的毛病。突出的有兩類:一類是沒有主問題。有些教師在引導學生解讀文本時,根本沒有考慮主問題,往往是小問題一大堆,東一榔頭西一棒,整個解讀過程就雞零狗碎,串不起來;一類是主問題設計錯舛。有些教師不知道應該怎么設計主問題,不尊重文本個性,隨便抓了一個作為主問題,結果把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帶歪了。閱讀教學中的主問題應該怎么設計呢?
一、要充分體現文體的特征
小學教材中的主要文體是四大類:記敘、說明、議論和詩歌等。其中記敘文的比例最大。各種不同的文體自然有不同的特性,所謂理解,就是把握其特性,讀出這一種文體與另一種文體的區別,讀出這一個文本與另一個文本的差異。在設計主問題時,就要充分考慮不同的文體特性。即使同樣是記敘文,也因為側重點不同而有所不同。有的記敘文側重于寫人,有的側重于敘事,有的側重于繪景狀物,在設計主問題時,都必須充分考慮這些個性。比如民間故事《獵人海力布》(部編本五上),它的主題是贊揚海力布的善良與為民犧牲精神,是寫人的。主問題可以設計為:海力布是怎樣一個獵人?主要通過哪些事情來刻畫這個人物的?而郭沫若的《白鷺》(部編本五上)是散文詩,主要是贊美白鷺的美,主問題不妨設計為:“白鷺是一首精巧的詩。”這是課文的第一句,在結尾處作者又重復了一遍,它究竟美在哪些方面呢?《什么比獵豹的速度更快》(部編本五上)是一篇說明文,主要通過比較的方法來說明多種事物的速度,主問題可以設計為:大家一看就明白,這篇文章是從慢寫到快的,就是說,所寫的事物是越來越快,那么寫了哪幾類事物呢?引導學生抓住人和動物、人造事物、天體和光,理清速度之線。受淡化文體觀念的影響,解讀文本時,有些教師不顧及文體特性,這是非常錯誤的。葉圣陶先生在《教學二十韻》中說:“作者思有路,遵路識斯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與親。”作者在寫作的時候,想表達什么,試圖通過什么文體來表達,都有明確的指向,我們在閱讀理解時,就必須遵其路,才能“識其真”。文體恰似人之性別,性別不同,性格脾氣與興趣愛好習慣自然也不同,要尊重人理解人,不能不考慮性別。
二、要精準把握文本的主旨
主問題的設計是否正確與恰當,往往與教師對文本主旨的精準理解直接相關。主旨,即文章的主題或立意,猶如人的思想感情。了解一個人,首先就要認清其想法;讀懂課文,首先就要讀懂主旨。小學語文教材中的課文,看上去都好像比較淺顯,似乎篇篇一見到底。其實,有些課文要準確理解也是有一定難度的。有些主問題設計不當,就是因為對主旨的理解不當,或者存在著偏差,或者過于膚淺。比如《掌聲》,筆者多次見到有教師是這樣設計主問題的:英子先后發生了怎么樣的變化?(由原先的自卑怯懦到后來的自信大膽)根據這個主問題設計,實際上就把這篇課文的主旨確定在:贊揚英子敢于戰勝自我。這顯然嚴重偏離了課文實際主題。《掌聲》(部編本三上)一文的主人公,不是英子,她只不過是個線索人物,文章的主人公是同學們的“掌聲”。課文的主旨是:對缺少自信和怯懦的人,要多一些鼓勵,多一些贊美。教學此篇時,主問題可設計為:文章一共寫了幾次掌聲?各為什么而響起?它產生了什么積極作用?即使這篇課文的標題改為《英子》,如果下面的具體內容沒有變動,主問題也不能確定為英子的前后之變,何況標題本來就是《掌聲》呢。有些主問題設計的不夠理想,不是教師對課文的主旨理解有偏差,而是理解得過于膚淺,不夠深入和到位。例如對《去年的樹》(部編本三上),有教師設計了這樣一個主問題:第二年,鳥兒在尋找樹的過程中一共問了哪些事物?(樹根、大門、火柴)這說明了什么?(誠實守信)根據這個主問題設計來理解課文,雖不能算錯,但不夠深入和到位。本篇課文的主題屬于誠實守信的要義范疇,但它又有特殊的意義。表現鳥兒的誠實守信,只要第二年來唱歌就足矣。而這只鳥兒不見樹后,卻要一直追蹤下去,最后的燈光,與樹已經是物非人非了,由樹到光,性質都變了。本文的主題應當是:贊美鳥兒矢志不渝,決意找到兌現承諾的對象,哪怕對象面目全非。教學本篇是,主問題不妨設計為:第二年,鳥兒不見樹后,為什么還要一個個追尋下去?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怎樣的意志和誠信?根據這個主問題,學生對課文就有可能達到較為深入的理解。事實上,閱讀這個童話,也只能理解到這一步,才可以說是真正讀懂了。
三、要注重思維流程的品質
閱讀教學肩負著學生思維能力培養的重任。思維品質有高下之分,思維流向有強弱之異。正像水質有清濁,流速有快慢。啟發學生思考時,用什么思維方法,這決定了要培養什么樣的思維品質和思維習慣。在設計主問題時,就應當充分考慮思維品質的問題。解讀文本時,經常采用的思維方法是:歸納法和演繹法。演繹法的思維過程是:從一般到特,即先得出結論,然后尋找符合結論的具體對象。歸納法的思維過程則正好相反,它是從特殊到一般的推理。也就是說,通過觀察很多個別事物的特殊性,然后概括出同類事物的特征。它們的思維流程正好相反。閱讀材料(課文)絕大多數是具體、形象、復雜和豐富多樣的,對它的理解,主要是概括、提煉、歸類和分析。因此,歸納法更切合于閱讀教學,也更有利于思維能力的培養。優秀的語文教師,在主問題設計時,一般不大會采用演繹法,不會先下結論,然后再去尋找符合結論的具體材料,而是經常采用從具體語言材料出發讓學生概括的歸納法。例如教《慈母情深》(部編本五上),有一位教師設計的主問題是:“慈母情深”這個標題就告訴我們,作者有一位慈祥的母親,究竟慈在哪里?請大家仔細找一找。根據這個主問題,學生先后找到下面的材料:勞動環境十分艱苦(噪音嚴重)、經濟收入低微(一把毛票),給“我”買書卻慷慨大方(先后給了兩次書款)。教師根據學生的回答,最后問:從這些情節中,能不能說明這是一位慈母呢?回答當然是相當肯定的一致。這就是演繹法,先有定論再找符合的內容,好像先有一個規定尺寸的箍,然后去找能放入箍的蘋果。從思維上說,是受到束縛的,大大限制了學生獨立思考的空間,對文本也不能完整而全面的消解。如果把主問題設計成:課文主要寫了哪些情節?從這些情節中可以看出這是怎樣一位母親?根據這個主問題,學生除了會研究勞動環境十分艱苦、經濟收入低微等情節外,還肯定會關注下面這段對話——
旁邊一個女人停止踏縫紉機,向母親探過身,喊道:“大姐,別給他!你供他們吃,供他們穿,供他們上學,還供他們看閑書哇!”接著又對著我喊:“你看你媽這是在怎么掙錢?你忍心朝你媽要錢買書哇?”
母親卻已將錢塞在我手心里了,大聲對那個女人說:“我挺高興他愛看書的!”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什么呢?母親的與眾不同。旁邊那個停止踏縫紉機的女人,難道不愛自己的孩子嗎?難道不慈嗎?當然也愛也慈。但“我”母親與她不一樣。“我挺高興他愛看書的!”這一句話,不是用一個“慈”就能概括得了的?這段對話,表現出母親的遠見卓識,表現出母親對孩子獨特的關愛。如果用演繹法,往往會忽略這段對話。從比較中我們能夠發現:演繹法只是對符合條件的材料進行研究,而歸納法是對所有材料進行一一推敲。演繹法多于尋找,歸納法重在發現。因而,采用歸納法就有可能更全面更準確解讀文本。從閱讀教學的現狀來看,采用演繹法來解讀文本還比較普遍,原因是教師操作起來比較方便。可是,教師怎能為了自己便于教學無視閱讀教學中的思維品質呢?
四、要體現簡捷易懂的原則
如何提起一件西裝?抓住一只袖子、或者拎住衣服下巴、或者捏住一粒紐扣等都可以提起,但這樣提拎起來的西裝看上去還像西裝嗎?不。只有提住領子,才能讓人知道:這是一件什么西裝。提領子,叫提綱挈領。同樣,解讀文本時,也應該抓住文章的“綱”和“領”作為主問題。有些教師為了避免俗套,為了體現獨特,刻意從某個細節,或某個詞句來設計主問題,這是不可取的。例如,在解讀《一個豆莢里的五粒豆》(部編本四上)時,有教師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先讓學生讀課文最后一個自然段:
此刻,頂樓窗子旁那個年輕的小女孩——她臉上射出健康的光彩,她的眼睛發著亮光——正注視著豌豆花,快樂地微笑著。
然后問:小女孩為什么眼睛里發著亮光?她為什么快樂微笑著?當學生回答說因為她看到豌豆花后,教師又問,看到豌豆花為什么會快樂,學生回答說看到了生命力的旺盛后,教師又問,這是哪一粒豌豆開的花?其它幾粒怎么樣?這樣設計雖然也能撬起全文,但總感覺相當吃力,總感覺過于麻煩。何必繞這么大的一個彎呢?完全可以用最簡捷易懂的設計作為主問題直接切入,比如:課文寫了五粒豌豆的不同命運,你覺得哪一粒最有意義?為什么?直截了當,不用轉彎抹角,直逼主題,快捷易懂。教學設計要創新,但不能為創新而創新,創新必須有利于學生理解內容,必須有利于正確、準確和快捷解讀文本。
文章寫得好不好,同作者的思路清不清直接相關,思路就是文脈;閱讀教學效率高不高,同主問題的設計好不好密切相關,主問題就是教學思路的綱要。有些課為什么散沙一堆,主要原因就是主問題設計不好。
參考文獻:
[1]孫衍明.閱讀教學中問題設計方法略談[J].語文教學通訊,2020(08):27-28.
[2]林慧.淺談小學語文中年級閱讀教學中的主問題設計[J].求知導刊,2020(08):55-56.
[3]劉俊峰.整本書閱讀教學中主問題的設計探究[J].新課程研究,2019(27):51-52.
[4]高艷紅.問題支架在深度閱讀教學中的設計與運用——以《合歡樹》教學為例[J].福建基礎教育研究,2019(10):53-55.
[5]劉波.小學語文閱讀教學“主問題”設計的實踐與思考[J].基礎教育研究,2019(14):71-72.
[6]李欣.淺談語文閱讀教學中“主問題”的設計[J].現代農村科技,2019(6):69.
[7]魯仁華.語文閱讀教學的實施策略[J].文學教育(上),2019(0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