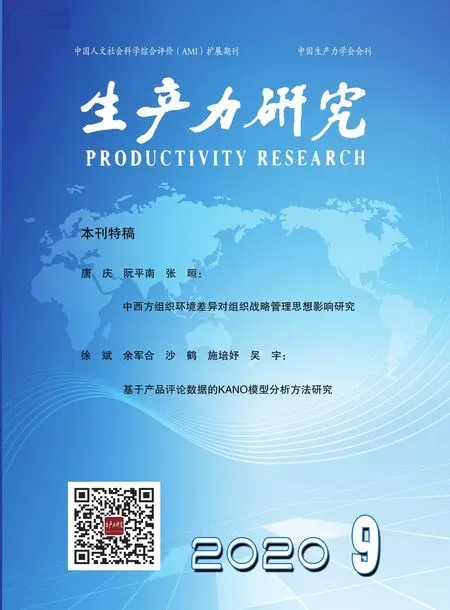旅游多目的地治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席麗莎,劉建朝
(1.天津城建大學城市藝術學院,天津 300384;2.天津城建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天津 300384)
有效的治理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我國現代旅游業發展本身起步較晚、時間較短,旅游治理的相關研究集中于景區的治理結構、經營模式或者旅游治理的利益相關者等單一目的地治理層面,在景觀、景點、景區的治理實踐中也起到了指導作用。但隨著旅游的跨越式發展,單一目的地治理已經開始向空間尺度更大、需求層次更高、效用滿足程度更強的多目的地治理轉變。在理論上,為了抵消行政邊界的負面影響,多目的地旅游治理可以有效發揮旅游業跨越邊界區障礙實現區域協同發展的作用,促進區域社會空間平衡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但目前學術界對旅游多目的地治理的整體性系統性梳理仍然缺乏。鑒于此,本文著重梳理了多目的地治理的兩大文獻主流:跨邊界旅游治理和旅游目的地治理,厘清旅游治理的軸勢和脈絡,剖析其概念源流、機制模式、治理網絡等關鍵議題,進而提煉主要發現并初步構建了旅游多目的地治理分析框架,從而進一步豐富旅游治理理論研究。
一、跨邊界旅游治理
旅游業可以作為克服邊界障礙實施區域協同戰略的工具,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治理過程通過所有與旅游相關的利益相關者的授權行為,推動旅游發展促進目的地的社會和空間平衡[2]。
(一)跨邊界治理的概念
跨邊界治理是超越行政邊界的行為[3]。一般來說,對跨邊界旅游治理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不同邊界對旅游的類型、規模、范圍和功能的影響,發展跨邊界目的地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效益,跨邊界目的地建設的障礙與跨邊界合作的行政約束[4]。跨邊界旅游目的地是指旅游活動發生的功能區,該功能區超越行政邊界[5],游客都可以在跨境流域范圍內消費,相鄰跨邊界旅游企業之間的產品差異會刺激跨邊界合作[6]。
(二)跨邊界治理的協作機制
跨邊界旅游治理的基本原則是區域整體利益主導,但受到現有的區域組織和機構對跨境發展態度的影響[7]。地區跨邊界行動者之間的聯系并不是自然發生,建立有效的跨邊界機構是持續努力的方向。Ilbery 和Saxena(2011)認為跨邊界合作倡議是自上而下的,在國家范圍內植根于區域結構中,地方政策的相對封閉性造成了獨立的政治單位,無法發展具有區域特征的獨特旅游市場品牌。由于邊界雙方的權力是不對稱的,在地區之間很難建立信任[8]。Weidenfeld(2013)認為跨地區利益相關者之間由于文化差異導致的相互信任水平較低,阻礙了跨地區治理協作機制的正常發展。Lovelock 和Boyd(2006)也發現盡管中央政府權力下放,區域地方政府機構卻并不愿承諾達成跨境規劃和管理協議,導致旅游目的地治理的主導權不清晰[9]。
(三)跨邊界治理的中介組織
跨界中介組織的培育是目的地治理的關鍵組成部分,其在發展和維持跨界通訊和資源交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Tosun 等(2005)基于行為者對跨境旅游組織發展潛力的感知,發現為了取得成功,需要邊界雙方建立聯合跨境旅游組織機制,增加商業集團和非政府組織的參與[10]。跨邊界旅游治理的主要鴻溝是制度落差。因此,跨境目的地需要建立能夠同時處理多重部門和機構分歧的治理結構[11]。
二、旅游目的地治理
旅游目的地治理是一個新興的熱點研究課題。2007 年,旅游目的地治理首次出現在文獻中。現有研究探討了旅游目的地治理的形成及概念、治理模式與績效、網絡治理的形成與演變等。
(一)旅游目的地治理的概念
治理是指為了保護利益相關者的一整套內部和外部的權力、過程和控制機制。因此,目的地治理是制定能夠將所有組織和個人結合起來的策略、規則和機制。Sara Nordin 和Bo Svensso(2007)提出了目的地治理的概念框架,將治理視為自組織的網絡化過程。在這個網絡中,所有的參與者相互依賴、自動交換資源并遵守協商制定的規則,擁有自主權[12]。旅游目的地參與者眾多,具有復雜性的特征。在目的地,公共部門和私人組織依賴于資源而相互作用。因此,復雜性、公私關系和對資源的相互依賴性是目的地治理研究的三個維度。Eagles(2009)同時認為,治理是一個社會或組織決定由誰來承擔選擇的責任和由誰來承擔成本的過程[13]。目的地治理包括政治、經濟和行政三個方面,涉及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個人。
(二)旅游目的地治理的模式和維度
相較于一般的旅游治理,目的地治理有兩種主流的治理模式:企業社區模式和傳統的市場層級網絡。Pietro Beritelle 等(2007)從產權理論、代理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聯盟與網絡四個角度,選擇交易成本、權力不對稱、相互依存、信任/控制、知識和非正式人際關系六個維度探討了旅游目的地治理的兩種模式:基于社區的模式和基于企業的模式[14]。他們也確定了目的地治理的主要內容:目的地的歷史及其發展、當前的規模和目的地的績效、發展的驅動力、相互信任和內部情緒。這些維度和項目有助于形成目標治理的模式。
在基于網絡的目的地治理背景下,Nyaupane 等(2015)進一步將地方旅游網絡劃分為三種運營模式:理事會主導的治理結構、參與者主導的社區治理結構和地方旅游組織主導的產業治理結構[15]。Sara Nordin 和Bo Svensson 選擇了目的地的復雜性、公私組織的相互作用和資源的相互依賴性三個方面研究目的地治理。更具體的研究包括對相關行動者及其角色和關系的分析,治理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政策網絡的形成和運作等。
(三)旅游目的地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及其績效
到目前為止,對各種目的地治理模式有效性的研究較少。Angella 等(2010)是這一研究領域的探索者。他們通過識別良好治理的特征來檢查地方旅游治理網絡的有效性[16]。這些方面包括:積極的文化、有效溝通和高參與度的社區;高透明度和公正的問責制;遠見和領導力;接受多樣性,追求公平和包容;重視知識,學習和分享專業知識;參與者明確的角色和職責,明確的運行結構和網絡流程。Eagles(2009)提出了善治標準,他重視歷史和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選擇中的重要作用。
(四)旅游目的地治理網絡的形成與演變
Eric 等(2011)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了旅游目的地的演變和轉型過程。他研究了網絡結構的密度和集中度,重點分析了組織之間的關系如何演變成為目的地的自組織機制的動態性過程,揭示了這個過程如何幫助隱性知識嵌入目的地開發網絡中。還有一些研究探討了政策網絡的形成、功能和作用,認為制度安排、治理模式的選擇和人們改變舊規則的意愿有關。雖然現有研究涉及到治理結構的類型、幾種類型治理結構績效的比較分析、善治是否存在等議題,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框架,經驗證據還很有限。
三、旅游多目的地治理分析框架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者、旅游企業、社區居民、學術機構和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重要地理空間,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合作與協調是區域發展的基礎。治理沒有確定統一的概念,且已經以各種方式被使用,有時甚至是誤用,這增加了建立一個普適的旅游治理分析理論框架的難度。
治理涉及協調、協作和利益相關者合作的過程,以確保旅游業的社會和環境發展在當地經濟中的乘數效應。旅游業的固有復雜性要求旅游業的發展必須以可持續為基本原則進行有效規劃和管理。國家與地方政府觀點之間的差異在于兩者對地方和私人利益創造的傾向不同,并不以當地居民需求的社會公平發展戰略為優先。面對有效管理的挑戰,在不斷變化的治理模式環境中,制度、經濟和社會環境變遷使得合作和治理難以實施,必須進行理論研究創新與實踐應用創新。
有效的治理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旅游治理的研究表明,文化旅游政策正在加速從政府管理向多元治理轉變,影響文化旅游的新型網絡化、后現代治理形式興起、目的地管理組織角色的變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中旅游治理的多元性,促進了文化旅游治理研究從一般案例分析轉向具體實證研究,從關注本地福利轉向關注區域總福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嘗試構建旅游多目的地治理的分析框架。第一,確立旅游多目的地治理的基本準則,即:有效溝通與協作、社會學習、權利責任與決策共享、適應能力與韌性建設。第二,以基本準則為基礎,將治理劃分為兩個階段:實施前階段(商詢、計劃設計)和實施后階段(執行、控制、評估、調整優化),治理原則在治理進程的不同階段有所差異。第三,歸納治理所需的一系列的變量,他們確定了12 個不同的變量,包括學習、知識、網絡、共享權力、組織互動、信任、領導力、授權條件、沖突、共同責任、連接組織和激勵。這些變量影響治理過程及其結果,同時又是相互關聯,且適用于治理準則過程。第四,依據治理原則與治理變量,生成關鍵治理機制,包括決策權力機制、利益分配機制與爭議解決機制,以支撐治理過程并促進治理產出。第五,從社會總福利的角度,提出了治理績效(見圖1)。
四、研究展望
進一步的研究需要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致力于回答以下科學問題:如何構建行政分割的跨邊界的旅游目的地?如何形成與之相匹配的文化旅游的治理模式?在什么情況下,面向跨邊界多目的地的旅游治理的特定形式可能是有效的?其進化機制和路徑是什么?為什么一些無效的治理形式會長期存在?
具體而言,一是確定面向多目的地的旅游治理的維度、治理績效的指標體系并實施;二是分析文化旅游治理模式與績效的關系;三是通過不同目的地的對比分析,找出影響旅游治理績效的關鍵因素;四是通過邏輯與歷史分析,研究治理模式的選擇及其績效的語境依賴,從而確立其系統邏輯;五是隨著環境變遷,旅游治理的路徑而不斷調整適應,多元共治如何在治理績效最大化的條件下得到實踐檢驗的支持。

圖1 旅游多目的地治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