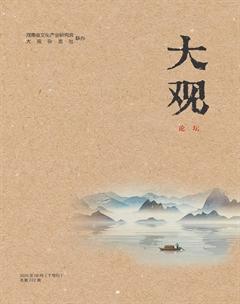文人畫及其在宋代的發展探析
張卓元
摘 要:文人畫最早可追溯到漢魏六朝時期。在我國古代,社會的等級制度是非常鮮明的。漢代始,張衡、蔡邕等士大夫階層參與繪事,開啟了文人作畫的歷史。到了北宋時期,以蘇軾為代表的文人畫派,又對文人畫進行了深刻的探討。文章主要討論一些文人畫及其發展,尤其是宋代文人畫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深入。
關鍵詞:文人畫;蘇軾;宋代
談到文人畫,我們不得不去追尋它的歷史由來,文人畫僅僅從字義上考證,最早可追溯到漢魏六朝時期。從漢代文人士大夫參與繪事起文人畫家就和畫工區分開來了,即在當時,張衡、蔡邕等士大夫階層參與繪事,開始了文人作畫的歷史[1]。在等級森嚴的古代社會,階級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法逾越的,把從事繪畫的人進行區分,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常理。其主要是依據他們的出身、學識或者社會地位來加以區別。在漢代的宮廷制度里,有專門為皇室服務的畫院,在這里工作的人在當時被稱為“黃門畫者”或“尚方畫工”,是在宮中使用的一般畫工[2],這些畫工由太監管理,有名的畫工有毛延壽。在漢代畫家就出現了幾種不同的階層,一是尚方畫工,二是民間畫工,三是文人畫家,文人畫家為數不多。
在南北朝時期,“士體”之稱開始出現。《歷代名畫記》中記載:“傷于師工,乏于士體。”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畫家如陸探微、張僧繇、蔣少游、楊子華、曹仲達等文人畫家。還有一些繪畫方面的論述,例如宗炳的《畫山水序》、王微的《敘畫》、謝赫的《古畫品錄》、姚最的《續畫品錄》等。隋唐五代37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繪畫史上繁榮昌盛的時期,尤其是唐代,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最為輝煌的時代,我國的繪畫,無不由此開始成熟而趨于更大進步[3]。唐代的繪畫理論著作有20多種,這些著作中有著很重要的理論價值和資料價值,例如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裴孝源的《貞觀公私畫史》等。張彥遠對于文人畫有著他自己的見解:“自古善畫者,莫非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為也。”此種言論在當時無疑又對士人從事繪畫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對畫工的社會地位又是一次較為嚴厲的打擊。這以后出現的鄙夷畫工之風也越來越強烈。
到了10世紀中葉,宋統一全國,結束了五代的軍閥統治。宋代初年,在農業上采取各種有利措施,緩和一個時期的階級矛盾,使農業和手工業恢復到了唐代原有水準,與此同時,城市商業經濟也興旺起來。南宋時,南方經濟和文化繼續發展,這些對當時的繪畫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宋代也有專門的畫院,嚴格錄用畫家。畫院畫家的官職較低,待遇較差,升級有限,服飾不同,畫家按照出身的不同被分為“士流”和“雜流”。民間繪畫在宋代可以說是相當繁榮,這與宋代時小農經濟的發展與市民階層的擴大有著很密切的聯系,民間畫工不僅在城市相聚,也在山鄉水村活動。畫家的區別嚴格上說有兩種,一是在身份上的區別,分為“畫士”與“畫工”;二是畫風的區別,分為“士人畫”與“工匠畫”[4]。畫士,是指社會上的士大夫畫家,畫院里的“士流”以及王門貴族中的能畫者。畫工在當時的工作可以說是多而雜,據史料記載可分為,為村舍節日作畫、為書刊作畫,畫道釋卷軸,為寺觀、石窟及墓室作畫,設棚“寫真”,賣畫[5]。我們通過這些史料記載可以看出,畫工所從事的工作,多為社會上較為低級的,這些都是文人畫家所不愿意做的,也是被文人稱為“有辱斯文”的事。
在我國古代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中,從事一種職業,是要世代相傳的,最為簡單的例子,一個人的父親是瓦匠那么這個人還有他的兒子、孫子在將來也要是瓦匠。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脫離,那就是通過科舉考試而成名。對于畫匠來說也是一樣,其通常需要繼承父業,需要子孫的世代堅守,然而這只不過是封建統治者為了穩固統治而采取的一項政治決策而已,但這畢竟是“藝術”,文人決不允許這種高雅的東西被當時人們所認為的畫工這一低等的職業所玷污。由于繪畫對文人有很強的吸引力,繪畫本身蘊含著無窮魅力,再加上皇室的極力推崇,文人參與繪畫就逐漸興盛起來,文人不僅僅是議論,而且也要親身實踐。文人在一開始的時候把繪畫當作為小道,僅“游于藝”。對于藝術,我們現代的觀點是全民參與,并沒有一些等級的劃分,而對于古人來說等級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對于藝術古人更加是有所想法。所謂文人無非是一些讀圣賢書的人,君子善假于物也,有時為了聊表內心的傷感情懷,他們既可吟詩作對,或是揮筆潑墨,也會寄情于山水,或工或寫,在幾尺宣紙上盡情抒發情感。文人繪畫并非是以此為生存的依靠、手藝,而是一種作為他們在感情郁悶苦澀時的一種發泄對象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于繪畫的認識不僅僅限于對客觀事物的簡單描述,而更為深層次的是在畫中深刻表達了自己的情感。
文人在此所指的是富有文學和書法修養的文人官吏,他們以部分時間和精力作畫[6]。宋代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時期,文人在社會上有著很高的地位,文人自然而然就會有一種優越感,在此之時,雖然與畫工從事著相同的事業,但文人都有自身獨特的繪畫觀點。
文人畫對于畫者來說是抒發情感、寄托和表達品格的一種雅好,繪畫的價值取向和畫工的文化修養,則會帶來文人畫和畫工畫的價值差異。文人除了在政治上要有所作為,還要在不同程度上要把自己在政治上失意與得意寄托在自然山水之中,在畫風上不會拘泥。
鄧椿的《畫繼》被視為文人畫在中國畫壇獨樹一幟的標志。其首先提出了“畫者,文之極也”的嶄新論斷,認為“畫豈獨藝”,應以文為先。他是第一個把文和畫聯系起來的,為文人畫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礎。蘇軾、米芾等也以為凡氣韻畢在生知,不可巧密得,不可歲月到。
蘇軾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中寫道:“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直截了當地說出論畫不以形似的觀點,并作詩來印證詩和畫在審美追求上是一致的,詩追求的是詩意,畫所追求的當然是畫意,而不僅是畫中物象的形似。詩是每一個文人必備的基本功,比繪畫還要普及,并且詩的發展要走在文人繪畫藝術的前面,故而蘇軾以詩論畫,文人更易于明白。蘇軾提出了文人畫和詩規律是一致的觀點,即“詩畫一律”的觀點,開啟了繪畫進入文學化追求的時代,文人在繪畫中追求詩意,并以詩的要求來論畫。
宋代文人畫思潮中的文人畫家,雖然對文人畫都有一些簡單的描述,但都是不成系統的理論,但是這些言論都已經從根本上說明了文人畫與畫工畫的本質區別,文人在繪畫之形的問題上提出了“常形”“常理”“遺物以觀物”等在意不在形的觀點,以區別于畫工畫的關注物之形等一系列的觀點。北宋文人畫思潮標志著文人畫的自覺,雖然在北宋時代,文人畫還沒有成為繪畫的主流,但是文人繪畫的主要精神框架在以蘇軾為中心的文人的表述中已經基本確立,文人階層對繪畫的觀念已經不自覺地影響到繪畫實踐,一些文人畫家更是身體力行,在繪畫之中實踐著文人畫的觀念,文人畫的基本形態得以生成。
文中大篇幅地談到了畫工與畫士的區別,是為了說明文人畫在其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較為細膩的環節。我們追溯文人畫的起源無疑是更加清晰地來了解文人繪畫的發展進程。我們在此研究文人畫,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為文人畫解釋和渲染。我們處在一個變革的社會里,不得不做出一些變動,對于古代文人畫來說也是一樣,唯有變才能應不變,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參考文獻:
[1][3]林木.論文人畫[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1.
[2][4][5]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上冊)[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117,416,416.
[6]張晨.張安治美術文集[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84.
作者單位:
山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