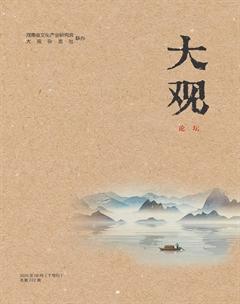從劇情與音樂的結合看歌劇《托斯卡》真實主義的藝術風格



摘 要:《托斯卡》可以說是普契尼最為出色的一部富有悲劇色彩的歌劇,被譽為普契尼真實主義藝術創作的里程碑。在這部歌劇中普契尼努力探尋優美的旋律風格,充分為歌唱者提供發揮、展示才華的平臺,以聲樂為中心,巧妙運用和發揮人聲的技巧,實現與戲劇內容的表現完美統一。
關鍵詞:普契尼;歌劇;真實主義;《托斯卡》
一、《托斯卡》的真實主義寫作風格
真實主義是文學藝術創作的觀念之一,“除細節的真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最早這一概念由恩格斯提出,之后現實主義就成為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初文藝創作的主要潮流,具體體現為注重實際和理性,講究客觀的觀察,重視社會問題和科學的研究態度,在藝術上從對美的追求轉向追求生活的真實等。普契尼就是成長在這樣一個現實主義文藝思想盛行的時代,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那關注社會、熱愛社會的偉大胸襟,使他成為真實主義歌劇藝術的代表人物之一。
普契尼是浪漫主義時期意大利歌劇作曲家,真實主義風格的代表人物[1]。意大利真實主義歌劇的發展是從《鄉村騎士》開始的,當時觀眾第一次接觸到這種以小人物的喜怒哀樂為主要戲劇沖突的創作手法,感到非常激動。歌劇故事的發展就像身邊的故事,劇中的主人翁好像活在人們的生活當中,再加上真實主義的舞臺布景、人物服裝以及演員們近似瘋狂的表現手法,使得真實主義歌劇一出現就深得觀眾的喜愛,經常演出時間還沒到一半,觀眾就坐不住了。普契尼看到了真實主義歌劇貼近普通人民群眾的特性,他在以后的創作道路上一直堅持真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托斯卡》的問世奠定了普契尼作為19世紀真實主義歌劇代表人物的地位。
《托斯卡》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創作的三幕歌劇[2],其創作特點主要表現為劇情戲劇沖突明顯,摒棄了以前只是簡單加入真實主義元素的創作方法,徹徹底底地采用真實的人物、地點及故事(《托斯卡》劇本源自話劇,其中幾位主人公根據真實人物改編而成)。歌劇的舞臺布景及服裝的表現手法真實;表達方式上吸收了話劇式的對話手法;音樂語言豐富,旋律優美明媚,器樂演奏與和聲技術高超;劇情遵循“有趣、驚人、動人”的原則,善于駕馭舞臺戲劇效果,具有極強的歌唱性及觀賞性[3]。
二、《托斯卡》的真實主義劇情與聲樂演唱及器樂演奏的聯系
歌劇《托斯卡》以現實生活中的故事為原型進行創作, 它具備了真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大部分要素[4],以真實主義劇情為依托的器樂演奏不僅為聲樂演唱伴奏,還起到了推動劇情發展、表現人物性格、增加舞臺效果等作用。在樂隊的編制上,不僅增加了弦樂的數量,而且還加入了大量的管樂和打擊樂,樂器數量多達51種。在聲樂演唱方面則摒棄了傳統的以嘩眾取寵為目的美聲演唱,更注重情感的表達與人物的刻畫,聲樂演唱更加戲劇化,舞臺表現使觀眾耳目一新。整個歌劇的開始打破了常規,并沒有以序曲的形式拉開序幕,緊張而帶有少許悲劇色彩的旋律風格,將觀眾迅速拉進了歌劇的劇情當中。
(一)歌劇第一幕
伴隨著緊張的音樂,歌劇第一個人物政治犯安杰洛提出場,他第一次出場的時間非常短,并沒有向觀眾交代清楚劇情的發展,僅僅是為之后的劇情埋下伏筆。這一部分的聲樂演唱更傾向于話劇,旋律近似自言自語,緊接著整個音樂風格從緊張急促轉向歡快,伴隨歡快的器樂旋律,歌劇中唯一的喜劇人物教堂司事出場。音樂風格迅速轉換,使觀眾很快對人物的性格有了一定了解。歡快的切分音、跳音和大幅度的音程轉換讓觀眾暫時擺脫了開場的悲劇情緒,融入人物的歡樂中(圖1)。
歌劇男主人公卡瓦拉多西的出場伴隨著非常抒情的旋律,表現出他與托斯卡愛情的音樂主題。詠嘆調《奇妙的和諧》是整部歌劇的一個閃光點。《托斯卡》整體的音樂旋律與劇情的發展結合得非常巧妙。詠嘆調有一個較長的前奏,在這段夢幻般旋律的映襯下,卡瓦拉多西端詳著圣母的畫像,腦海浮現自己的愛人托斯卡,不禁唱出自己的情懷。
詠嘆調之后是卡瓦拉多西與政治犯的一段簡單對話,這段對話非常簡短,器樂的演奏和聲樂演唱幾乎沒有任何聯系。兩位老朋友以這種形式見面,本來應該有很多話要說,但器樂演奏則以激進的旋律向前推動,直到引出女主人公托斯卡。這種器樂演奏與劇情發展的激烈沖突讓人感覺到兩人的話沒有說完,無形中加劇了愛情的甜蜜與政治斗爭的戲劇沖突。在隨后的男女主人公的二重唱中,器樂的鋪墊也為妒忌與愛情兩種情緒的轉換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整個二重唱中,演員在不失真實主義精神的同時,很好地汲取了19世紀的羅西尼、多尼采蒂、貝利尼美聲演唱的精髓,用優美的旋律和甜美的嗓音向觀眾詮釋著二人忠貞的愛情。托斯卡走后是一段表現感恩節的童聲合唱,這也許是整個歌劇中最輕松的情節,歡快的音符讓人們忘記了歌劇中的陰謀、背叛與殺戮。作曲家試圖用天真無邪的兒童淡化激烈的劇情沖突,但警察局長斯卡爾皮亞的出現徹底打破了這種可能性。伴隨一連串的打擊樂和管樂,邪惡的斯卡爾皮亞首次出現在劇中,他一出現,便運用咆哮般的命令口吻譴責在場的每一位。此時,器樂停止了演奏,整個舞臺只剩下斯卡爾皮亞的咆哮,使得在場的每一個人都驚恐地屏住了呼吸。緊接著是一連串不規則的音程,包含眾多的變化音。在斯卡爾皮亞詢問教堂司事的過程中,反復出現一個代表權力的主題,在這個主題的威迫下,懦弱的教堂司事知無不言(圖2)。
斯卡爾皮亞與托斯卡的碰面以卡瓦拉多西和托斯卡的愛情主題為引子,但與之前不同的是,斯卡爾皮亞的聲音凌駕于旋律之上,使得主題的表現性非常微弱。托斯卡沒有見到卡瓦拉多西,妒忌的心理使她情緒很低落,而狡猾的斯卡爾皮亞則喬裝成一個天真的孩子。作曲家以清脆的敲鐘聲來表現斯卡爾皮亞的偽裝,這段音樂評論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音樂同時展現出了天真、善良和邪惡三種不同的性格。”聲樂演唱與器樂演奏部分表現得非常歡快,似乎在托斯卡眼前的并不是邪惡的警察局長而是一位可敬可愛的長輩。天真的托斯卡對斯卡爾皮亞的話堅信不疑,斯卡爾皮亞用各種狡猾的手段,使得托斯卡的妒忌之火燃燒得越來越旺。兩人的對話結束后,愛情主題再次出現,與之前不同的是器樂演奏得非常緩慢,使得這種愛情變得非常凄涼,伴隨著這段凄涼的旋律托斯卡下場。此時斯卡爾皮亞迅速撕破偽裝的面具,邪惡主題迅速回到了歌劇中。伴隨著邪惡的旋律,斯卡爾皮亞的演唱逐漸融入進來,引出了著名的詠嘆調片段“去吧,托斯卡”。這首詠嘆調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斯卡爾皮亞的邪惡與狡猾,伴奏部分的主題音樂幾乎沒有停止過,而斯卡爾皮亞則用邪惡的語言迎合著這個主題:“去吧,托斯卡,在你的心里已經有了斯卡爾皮亞,愛情的誓言在強烈的妒忌心理下一文不值……托斯卡你使我忘記了上帝。”當斯卡爾皮亞將整個旋律推向高潮時,音樂家巧妙地加入了教堂的彌撒音樂,兩種音樂風格的融會帶給觀眾更加強烈的震撼。
(二)歌劇第二幕
在斯卡爾皮亞的宮殿中,他正為自己完美的計劃而洋洋得意,聲樂演唱與器樂的演奏也表現得比較歡快,直到警察的出現,音樂開始轉向緊張,一段激烈的進行曲節奏后,引出了第二幕最重要的刑罰場景。在審訊過程中,器樂演奏風格的轉換表現了劇中人物內心情緒的轉換,而神圣清唱劇的演唱,則襯托出整個刑罰場景的骯臟。在斯卡爾皮亞的威逼利誘下,天真的托斯卡說出政治犯安杰洛提的藏身地點,以為這樣能換來她想要的自由,但斯卡爾皮亞想要的遠不止這些。為了霸占托斯卡的身體,音樂推動著斯卡爾皮亞徹底露出了本性,器樂的演奏從表現刑罰場景的殘酷重新回到著重刻畫人物的狡猾。這一部分的聲樂演唱淋漓盡致地表現出真實主義歌劇的演唱風格,兩人的爭吵幾乎沒有任何旋律感,完全是內心情感的宣泄,演員也忘掉了美聲演唱的技巧,全身心投入劇情的發展,這部分音樂將戲劇沖突推向了頂峰(圖3)。
在片刻的內心活動之后,托斯卡唱出了著名的詠嘆調《為藝術,為愛情》。而斯卡爾皮亞顯然沒有同情她的無奈,任憑托斯卡一次又一次地祈求,他絲毫沒有終止自己的邪惡欲望,這一部分的音程變化相對簡單,充分表現出了托斯卡的無助。面對斯卡爾皮亞的威脅,托斯卡別無選擇,只有同意。當斯卡爾皮亞假裝同意釋放卡瓦拉多西的時候,器樂演奏用連續的變化音和跳音暗示他的不真實。在簡短的幾句對話后,樂隊緩緩的奏響了整部歌劇最凄慘的旋律,連續的雙附點下行音程,仿佛暗示著劇中人物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正當觀眾以為斯卡爾皮亞要得手時,伴隨著音樂風格的快速轉換,一把尖刀插入斯卡爾皮亞的胸中。聲樂演唱與器樂的演奏用盡全部的力量。斯卡爾皮亞死后,樂隊用較為舒緩的旋律將觀眾重新拉回平靜,第二幕在連續的保持音型中結束。
(三)歌劇第三幕
這一幕以預示著勝利的旋律開場,音樂旋律非常歡快,與第二幕沉重的音樂風格形成鮮明對比。牧羊少女的演唱使整個劇情仿佛脫離了故事發展,讓觀眾緊張的情緒得到了舒緩,但是一陣急促的敲鐘聲和悲傷的旋律將觀眾又重新拉回劇情中。整個第三幕的開頭有相當長的器樂演奏,即便在卡瓦拉多西與監獄看守人員的對話部分,旋律伴奏也從未停止過。短暫的平靜后迅速引出著名詠嘆調《星光燦爛》的旋律,這種憂傷的情緒使觀眾不禁為男女主人公的悲慘命運所惋惜。著名的音樂評論家曾說:“這首詠嘆調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它凄美的前奏,這仿佛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旋律,將演員與觀眾的悲傷情緒推到極點。”宣敘調部分的器樂演奏與聲樂演唱像兩位知心的朋友在對話,共同感慨悲慘的命運,而進入詠嘆調部分,伴奏與聲樂演唱合二為一,共同推動悲傷的情緒發展。詠嘆調后緊接著是托斯卡的愛情主題,這一部分的聲樂演唱鏗鏘有力,表現對未來生活的無限憧憬,而器樂伴奏部分則以進行曲式的風格為主。在二人商量好以假死逃脫死刑后,器樂演奏也表現得比較調皮,以連續不斷的6連音烘托著這一情緒(圖4),但不時跳躍的尖銳音符卻向觀眾透露悲劇即將到來。在死刑場景中,完全由托斯卡口述推動劇情的發展,器樂演奏部分不斷重復著之前的頑皮旋律。在死刑后,同樣的旋律卻以管樂的形式出現,讓人感受到些許的沉重。隨著托斯卡不停地呼喊,伴奏停止,整個舞臺只剩下托斯卡的呼喚聲。在一聲撕心裂肺的呼喊之后,伴隨警察密探們的議論聲,整個樂隊再次奏響了星光燦爛的主題旋律,托斯卡墜樓身亡,歌劇在一連串快速的和弦中結束。
綜上所述,普契尼的不朽名作給后人留下了無盡的音樂寶藏, 掀起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意大利真實主義歌劇的高潮[5]。這部《托斯卡》升華了真實主義歌劇的思想內涵,使整部歌劇既有傳統的體現,又有風格的創新。通過對《托斯卡》中劇情與音樂的分析,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普契尼歌劇作品的風格特點,加深了對《托斯卡》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內涵的理解,能夠更準確地把握好這部作品,更好地用感情和聲音去表現和塑造人物形象。
參考文獻:
[1]路潔.關于普契尼歌劇作品中真實主義風格的文獻綜述[J].當代音樂,2017(4):78-80,85.
[2]文廈.詠嘆調《奇妙的和諧》音樂特點與演唱分析[J].當代音樂,2017(22):65-67.
[3]李秀華.從普契尼歌劇談詠嘆調的戲劇性[J].音樂探索,2003(4):62-64.
[4]傅偉林.普契尼歌劇的創作風格與特點[J].當代音樂,2015(23):130-131.
[5]李珍妮.歌劇詠嘆調《為藝術為愛情》演唱分析[J].當代音樂,2016(24):58-59.
作者簡介:
陳家寧,鄭州升達經貿管理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聲樂教學與音樂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