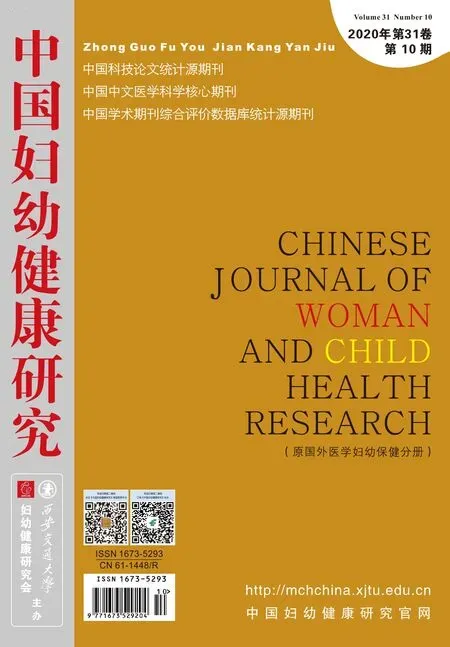二孩政策對不同指征剖宮產率的影響評價
夏曉燕,肖晚晴,劉慧慧,黃培元,于 佳,楊 麗,邱 琇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 1.出生隊列研究室;2.婦女保健部;3.計劃生育與婦幼信息部,廣東 廣州 510623)
有醫學指征的剖宮產術可挽救孕產婦和胎兒的生命,而非必要的剖宮產術可能對孕產婦和新生兒結局產生不利的影響[1-3]。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剖宮產率不應超過10%~15%[4],并指出人群剖宮產率高于10%時不能進一步降低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5]。廣州市依托“母嬰安康行動計劃”實施了改善產科質量的綜合措施,剖宮產率明顯下降[6]。但隨著生育政策的調整,高齡和瘢痕子宮等妊娠比例增加,給控制剖宮產率帶來了新的挑戰。本研究通過對廣州市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剖宮產指征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為新形勢下控制和降低剖宮產率提供參考啟示。
1資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收集所有于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間在廣州市全部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內分娩的≥28孕周的產婦作為研究對象,其中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是指在產科技術力量較強、具有一定服務規模的助產技術服務機構[7],由廣州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評定發布的單位。
1.2研究方法
1.2.1數據來源
回顧性提取廣州市婦幼信息系統[6]的產婦資料,包括產婦年齡、產次、分娩孕周、胎數、胎方位、分娩方式、產時高危因素、產時并發癥。
1.2.2二孩政策時間分期
根據二孩政策實施的時間依次分為基線期(2013年1月至12月)、單獨二孩時期(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和全面二孩時期(2016年1月至12月)。
1.2.3剖宮產指征分類
結合2014年剖宮產手術專家共識[8]和廣州市孕產婦保健管理分類標準[7],將剖宮產的原因分為非醫學指征和醫學指征兩類,其中醫學指征為:①胎兒宮內窘迫;②產道異常(骨盆異常和可能影響分娩的軟產道異常);③瘢痕子宮;④胎位異常(橫位,足先露);⑤前置胎盤;⑥雙(多)胎妊娠;⑦胎盤早剝;⑧其他妊娠合并癥和并發癥,包括輕度高血壓或輕度子癇前期、心臟病、肝病、慢性高血壓、腎臟病、紅斑狼瘡、中重度貧血、肺結核、精神病、性病、嚴重感染、重度子癇前期、子癇、慢性高血壓并發子癇前期、急性闌尾炎、急性膽囊炎、膽結石癥、妊娠合并婦科腫瘤(≥5cm)和妊娠合并惡性腫瘤;⑨疑似巨大胎兒。
1.3評價指標
剖宮產率=剖宮產例數/產婦數×100%;指征別剖宮產率=某一指征剖宮產例數/產婦數×100%,指每100例分娩產婦中,因某一指征行剖宮產的例數。指征貢獻比C=(Xj-Xi)/(Yi-Yj)×100%,C是各剖宮產指征對降低剖宮產率的貢獻比,指某一剖宮產指征對剖宮產率變化所產生的直接影響,i指不同二孩政策時期,j指基線。如果研究期內剖宮產率降低,指征貢獻比為負值表示該指征對降低剖宮產率有益,為正值表示該指征是剖宮產率升高的因素之一[9]。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AS 9.4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用趨勢卡方檢驗剖宮產率總體趨勢;用時間序列分段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不同生育政策期間每月非醫學指征和醫學指征剖宮產率的變化;為使回歸模型的初始截距(基線剖宮產率)有意義,對年齡進行中心化處理(又稱零均值化,即產婦年齡減去年齡的均數)后加入模型進行調整,用直條圖展示不同政策時期指征貢獻比及其變化,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一般情況
2013年至2016年廣州市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共有250 249例產婦,將48個月的剖宮產率納入分析。高齡(≥35歲)產婦比例由9.72%上升至13.67%,有瘢痕子宮的經產婦比例由12.77%上升至17.94%,見表1。
2.2總體剖宮產率和指征別剖宮產率變化情況
總體剖宮產率在不同時期呈下降趨勢(Z=20.700,P<0.001),從2013年的39.02%下降到2016年的33.34%;非醫學指征剖宮產率顯著降低(Z=39.987,P<0.001),從2013年的18.01%下降到2016年的10.37%;醫學指征剖宮產率呈上升趨勢(Z=-9.661,P<0.001),從2013年的21.01%上升到2016年的22.98%,見表1、圖1。

表1 2013年至2016年廣州市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分娩產婦基本特征

注:a 單獨二孩時期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b 全面二孩時期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
二孩政策實施前,非醫學指征和醫學指征剖宮產率均呈下降趨勢,月均變化速度分別為-0.161(95%CI:-0.288~-0.034)、-0.201(95%CI:-0.367~-0.036)。單獨二孩時期,非醫學指征剖宮產率下降速度繼續增加[斜率變化為-0.162(95%CI:-0.297~-0.027),P=0.023],但在全面二孩時期,其下降速度減少0.262(95%CI:0.128~0.397)。醫學指征剖宮產率在二孩政策實施后逐漸上升,單獨二孩時期和全面二孩時期斜率分別增加了0.246(95%CI:0.070~0.421)和0.283(95%CI:0.107~0.458),即從基線期每月平均減少0.20%,變為單獨二孩時期每月增加0.05%,再到全面二孩時期每月增加0.33%。在調整年齡后,醫學指征剖宮產率在二孩政策實施期間上升的效應減弱,單獨二孩時期上升速度增加僅為0.020(95%CI:0.020~0.370),且在全面二孩時期未有繼續上升。具體見表2和圖2。

表2 2013年至2016年廣州市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醫學指征和非醫學指征剖宮產率分段線性回歸結果

注:a 單獨二孩時期指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b 全面二孩時期指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
2.3指征貢獻比情況
2013年至2016年廣州市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整體剖宮產率下降,見表1、圖1;其中非醫學指征剖宮產率下降帶來的貢獻最大,貢獻比從單獨二孩時期的72.88%上升至全面二孩時期的133.33%。瘢痕子宮是引起剖宮產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貢獻比從11.86%上升至78.95%。前置胎盤、雙(多)胎妊娠、產道異常、胎盤早剝、疑似巨大兒、胎位異常、其他妊娠合并癥和并發癥的指征剖宮產率的影響比較穩定,見圖3。

圖3 2013年至2016年廣州市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在不同二孩政策時期指征貢獻比的變化
基于瘢痕子宮是剖宮產率上升主要原因的發現,本研究對控制初產婦剖宮產率的效應進行了估算,與2016年全國監測數據相比,當初產婦的剖宮產率控制在本研究中2016年單胎足月初次分娩的剖宮產率水平(27.13%)時,2016年至2018年全國的初次分娩后再次分娩行剖宮產的潛在人群可減少304萬人,見表3。

表3 控制初產婦剖宮產率引起的再次分娩行剖宮產潛在減少人數估計結果
3討論
3.1二孩政策對剖宮產指征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2013年至2016年廣州市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分娩產婦剖宮產率下降,非醫學指征剖宮產的減少對整體剖宮產率下降影響最大。在二孩政策實施后,醫學指征剖宮產率逐漸上升,瘢痕子宮貢獻比最高。用中心化年齡進行調整后,政策的實施對醫學指征剖宮產率上升的影響減弱。
3.2關注高齡和瘢痕子宮妊娠及安全避免初次剖宮產
既往研究顯示孕婦年齡與不良妊娠結局密切相關,生育政策的調整為孕產婦年齡構成及母嬰并發癥帶來了變化[11]。本研究也發現二孩政策期間,在廣州市Ⅳ類助產技術服務機構分娩的高齡產婦增加。為了消除年齡結構不同引起的指征變化,本研究對年齡因素進行了調整,調整后二孩政策對醫學指征剖宮產率的影響減弱,提示要重視和重點監測高齡孕產婦的圍產保健。
本研究還發現,非醫學指征剖宮產減少對整體剖宮產率下降影響最大,側面反映了廣州市實施干預措施安全有效[6]。本研究中瘢痕子宮的經產婦比例從基線期的12.77%上升到了全面二孩時期的17.94%,與2016年全國監測數據顯示有瘢痕子宮產婦17.7%一致[10]。美國婦產科醫師學院和美國母胎醫學會聯合發布了《安全避免初次剖宮產》的產科醫療共識[12],其指出最容易實現的是降低足月單胎初產婦剖宮產率。李志斌等[13]研究亦提示,控制“初次剖宮產”手術指征是降低剖宮產率的重要手段。經測算,當全國的初產婦剖宮產率下降到本研究足月單胎初產婦剖宮產水平(27.13%)時,2016年至2018年全國初次分娩的產婦再次分娩行剖宮產的潛在人群可減少304萬人。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剖宮產,提高順產率,應制定完善的健康促進方案和干預措施[14]。
3.3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于數據收集的局限,研究中醫學指征比專家共識[8]寬泛,如本研究的心臟病沒有具體分級,可能高估了醫學指征剖宮產率;其次,本研究未收集與剖宮產有關的產婦、家庭和社會等社會因素,不能進一步分析非醫學指征中的主要因素。
綜上,二孩政策的實施帶來了孕產婦人群結構的變化。本研究提示應積極控制非醫學指征原因的剖宮產率可有效降低總體剖宮產率,新生育政策背景下宜關注高齡和有瘢痕子宮妊娠的圍產保健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