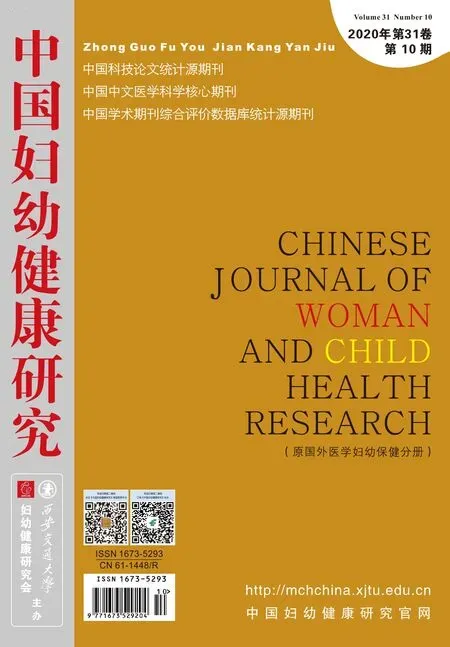早產兒自發性腸穿孔5例臨床特征分析
李亮亮,李苗苗,王雯雯,卞春暉,姜 紅,李向紅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新生兒科,山東 青島 266000)
新生兒自發性腸穿孔(spontaneous intestinal perforation,SIP)又稱為新生兒單純腸穿孔(isolated intestinal perforation),是新生兒期無明顯誘因的胃腸道單個穿孔,常發生在回腸末端。SIP是新生兒時期的常見胃腸道急癥,發病率僅次于壞死性小腸結腸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曾被認為是NEC的一類良性病變,但現在趨于認為SIP是一種單獨的疾病[1]。有關SIP的報道多集中在極低出生體重兒(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ELBW)[2]。國內文獻對這種疾病報道較少,本文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收治的5例SIP病例進行資料整理,現總結如下。
1病例基本資料與穿孔情況
1.1病例基本資料
收集2013年6月至2019年6月青島大學附屬醫院收治的SIP早產兒,納入標準:①孕周小于37周;②手術證實存在腸穿孔。排除標準:①合并消化道畸形;②足月兒;③手術證實為多發腸管壞死病變。共收集SIP病例5例。
2013年6月至2019年6月這6年間我院新生兒科共收治出生體重1 000~1 499g的極低出生體重兒(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VLBWI)435人,出生體重小于1 000g的超低出生體重兒(extreme low birth weight infant,ELBWI)183人。共有5例患兒發生SIP,男3例,女2例;出生體重為880~1 350g,平均體重為(1 030±183)g;其中4例為ELBWI,SIP發生率為2.2%(4/183),1例為VLBWI,其發生率為0.2%(1/435);胎齡為25~29周,平均胎齡為(27.1±1.7)周;分娩方式:2例為順產,3例為剖宮產;1分鐘Apgar評分4~10分;喂養方式:1例為母乳喂養,2例為配方奶,2例未開始喂養;腸穿孔發生時日齡2~12天,平均(7.4±3.6)天,見表1。

表1 5例患兒的基本情況
1.2穿孔情況
病例1生后7天顯著腹脹,腹壁顏色呈藍黑色,腹壁靜脈顯露,觸診軟,腸鳴音消失,見圖1。腹部立位片可見膈下大量游離氣體,見圖2。5例患兒均在全身麻醉下行剖腹探查術,術中發現3例患兒穿孔部位在回腸位置,距離回盲部約10、20、40cm處,穿孔直徑分別為1、0.6、0.2cm;1例患兒在距離Treiz韌帶15、20cm處出現2個穿孔,穿孔直徑分別為0.4、0.8cm;1例患兒在距離Treiz韌帶40cm處出現1個穿孔,穿孔直徑為0.7cm。病例1穿孔部位在距離回盲部40cm回腸位置,為單一穿孔,直徑約0.2cm,穿孔周圍腸管紫黑色,其余腸段正常,見圖3。給予全程縫合破裂處,漿肌層包埋縫合。另4例患兒行切除穿孔病變腸管進行腸管吻合術。5例患兒均給予生理鹽水沖洗腹腔,留置引流管。術后給予輔助呼吸治療,禁食減壓,抗感染治療,全靜脈營養治療,見表2。

注:病例1生后7天顯著腹脹,腹壁顏色呈藍黑色,腹壁靜脈顯露,觸診軟,腸鳴音消失。

注:可見膈下大量游離氣體,消化道穿孔。

注:術中可見距回盲部約40cm處回腸穿孔,直徑大約0.2cm,穿孔局限在回腸一處,周圍腸管紫黑色,其余腸段正常。

表2 5例SIP病例術中發現及手術方式
2預后結局
1例患兒腸修補術后出現反復腹脹,給予灌腸、推拿按摩等治療后恢復良好;2例患兒并發腦室旁白質軟化;1例患兒在術后6小時內并發肺出血并嚴重呼吸衰竭,搶救無效死亡;余1例患兒經一期手術均順利康復出院,見表2。存活的4例早產兒隨訪時間大于6個月,生長發育良好,未發現腸狹窄、腸梗阻等癥狀。
3討論
3.1 SIP病例的特點
SIP是新生兒期無明顯誘因發生的胃腸道的局灶性穿孔,多為單個穿孔,常發生在回腸末端。SIP主要發生在VLBWI和ELBWI[3]。有研究表明,新生兒期SIP發生率為0.02%,早產兒發生率為7%[2],其中VLBWI發生率為2%~3%[4],Attridge等于2006年報道ELBWI發生率為3%~8%。SIP患兒出生體重中位數為812.9g[5];在男嬰中更為常見[5-6]。本組患兒孕周在25~29周,男女比例為3∶2,平均胎齡為(27.1±1.7)周,新生兒體重在880~1 350g之間,4例為ELBWI,發生率為2.2%,1例為VLBWI,發生率為0.2%,低于既往文獻報道。
SIP臨床上可分為早期SIP和晚期SIP兩種類型[2]。早期SIP多發生在早產兒生后0~3天,患兒出生體重相對較大,發育較成熟,易出現氣腹征,常不伴有危險因素。晚期SIP多發生在早產兒生后4~14天,患兒出生體重相對較小,發育較不成熟,腹腔常無氣體。除了早產和極低出生體重外,目前關于其發病機制和潛在危險因素的證據仍存在爭議[7]。早產兒皮質醇和吲哚美辛的使用、早產兒全身感染、孕母絨毛膜羊膜炎和抗生素使用、硫酸鎂的使用、子癇前期、肌力、延遲喂養等是新生兒發生SIP的高危因素[8-9]。本組病例腸穿孔發生時的日齡為2~12天不等,平均(7.4±3.6)天,應該歸于第二種類型,但本組部分病例無發生SIP的高危因素,對ELBWI的研究亦報道有50%的SIP患兒并無上述危險因素,說明這些危險因素并非形成SIP的必要因素,更可能扮演二次打擊的角色,增加了因肌層發育先天不足導致本已脆弱的腸壁發生穿孔的風險[10]。穿孔部位常發生在回腸末端,也可發生在橫結腸和降結腸等部位[11]。本組患兒中3例患兒病變部位在回腸末端,2例患兒腸穿孔位于空腸,與以上結論相符。術中發現,腸管病變范圍比較局限,病變部位主要位于穿孔處及臨近穿孔處的1~2cm段腸管。我們發現即使出現2個穿孔部位,但腸管大體形態并不如NEC節段性樣病變,仍然局限。這些臨床特征表明SIP病變有別于NEC。SIP曾被認為是NEC的一種特殊類型,現已逐漸認識到SIP是一種單獨的、不同于NEC的臨床疾病[12]。這提示我們在治療SIP時不能照搬NEC的治療方法。
3.2 SIP治療方式的選擇
國內對于消化道穿孔患兒一般采取急癥手術的治療方式,而Rao等[13]認為早產兒發生SIP時,當患兒出現代謝紊亂癥狀時,如血小板減少癥、代謝性酸中毒、中性粒細胞減少、中性粒細胞核左移、低鈉血癥、敗血癥和低血壓時,可選擇開腹手術或者腹腔引流。回顧性研究了79例因SIP行手術的ELBWI,比較了腹腔引流或開腹手術后15例SIP患兒的結局,發現二者在治療效果、存活率及住院時間方面并無差異[14],類似研究亦發現單純腹腔引流和開腹手術在短期(>30天)存活率上并無區別[15]。本組5例患兒均采用了開腹手術進行腸修補、腸管切除吻合術。4例患兒術后恢復良好,治愈出院。1例患兒因合并嚴重肺出血而導致死亡。
3.3預后
任何腸穿孔都可導致預后結局不良,但相對于NEC所并發的腸穿孔,SIP出現預后不良結局的危險性要低[7]。研究發現需要外科手術的NEC入院前的病死率和遠期神經系統并發癥為53.5%和82.3%,而SIP分別為39.1%和79.3%[16]。SIP的預后因素是低出生體重兒的并發癥,如神經系統疾病(顱內出血)、呼吸窘迫(支氣管肺發育不良)和心臟疾患(先天性心臟病)。有研究發現超過一半患有NEC或SIP的早產兒在剖腹手術中表現出腦血管自動調節機能受損的跡象[17]。本組患兒中,2例患兒出現了腦室旁白質軟化,提示發生SIP后的早產兒神經系統損傷的相關并發癥仍然較高。
綜上,我們目前認為SIP在早產兒特別是ELBWI散發可見,體重越小發病率越高,是獨立于NEC外的一種單獨病變,病變腸管多局限在末端回腸,胎兒和孕母的一些高危因素可能會誘發SIP。對于腹腔污染輕、一般狀況良好的患兒,可施行一期手術,早產兒SIP多數預后較NEC好,但要密切關注其神經系統并發癥等,預防不良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