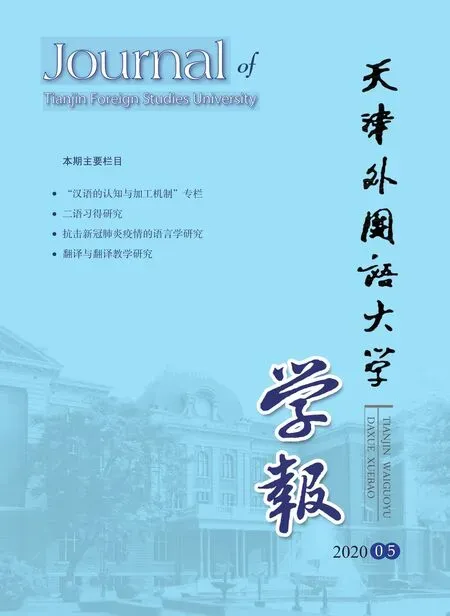“政治等效+認知趨同”:認知翻譯觀視閾下的政治文本翻譯研究
龍新元,李秋霞
(鄭州輕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
一、引言
近代肇始,政治文本翻譯歷時演進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由“主觀神秘”(虛幻化)走向“忠實至上”(結構化),最終形成“多元綜合”(圓融化)實踐模式(龍新元,2020)。易言之,翻譯家最初將其視為一種藝術,而后歸于一種科學,最后上升為藝術與科學的共同體。新時代,翻譯重心由“譯入”轉向“譯出”(2011年首占54%,2014年起穩定在60%左右),對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意義非凡。然而,由于意識形態、政治生態、文化故態等影響因子,國際社會中以發達國家為首的政治聯盟仍對中國的內政外交存有誤解,政治思想、文化走出去、走進去任重道遠。鑒于此,胡開寶等(2018)、秦洪武等(2019)和魏向清等(2019)提出政治話語傳播途徑、傳播效果必將是今后很長一個階段的研究重心。誠然,政治文本外譯的傳播學研究視角是必要的,但追根溯源,文化、意識形態不合拍背后本質上的、跨種族的認知差異則更值得深挖。
政治文本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意識逐漸增強,胡開寶等(2018:79)從批評話語分析理論出發,自建語料庫,分析外交話語英譯所塑造的中國形象。趙祥云(2018:52)推介圖里(Gideon Toury)描述翻譯學的規范概念,評述領導人著作英譯本。楊明星等(2018:89)以文學翻譯為鏡,非文學為本,歸納出外交修辭翻譯的“梨”式(PEAR)原則。此類研究多趨向于“以小見大”,剖析具體詞、句、段的譯法以作出宏觀性的探討,少有將目光轉向譯文讀者的認知思維結構;闡明某種譯法更能為受眾所理解,卻鮮有涉及為何這種譯法使“另一方水土”的讀者也能意會與原文讀者理解相近的文本意義。誠然,政治文本翻譯認知化研究也確有“百花齊放”之勢,侯學昌等(2019:18)從識解觀出發,洞悉政治文本英譯現狀;孟筱筠等(2019:71)對政論詞、政論語篇翻譯中出現的范疇化現象進行解讀;周紅等(2010:85)在概念隱喻理論指導下,剖析政治演講中隱喻翻譯技巧,然而類似研究趨于細化(碎片化),學者多引介認知翻譯框架內的某一理論作為指導,縱向深度毋庸置疑,卻少橫向宏觀視野,較難揭示認知翻譯觀對政治文本翻譯研究具有何種整體意義,或影響學科間進一步的交叉融合。
認知源于實踐,指導實踐,建構實踐。具身哲學(embodied philosophy)視角下,同處現實世界的人類憑借相同身體結構和相近感性經驗深化認知,建構概念,思維故具有共性,思維外顯——語言也相互關聯,指涉人類認知能力的“趨同”;意義理解、衍生則取決于人類對事物原型的主觀認知加工——識解(construal),“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同母語者形容同一事物在表達式上也可能存差。認知、語言的關聯性、差異性明確了跨語交際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困難程度,認知化翻譯上升為一項“使命”。本文立足現有研究成果,從認知翻譯觀的整體視角出發,揀選框架內四大維度(認知范疇觀、隱喻觀、轉喻觀、識解觀),管窺政治文獻及譯本背后的認知理據,明確何為“使命”。基于楊明星教授于2008年構建的“政治等效”翻譯原則,思考“政治”、“認知”、“翻譯”的外化關系與內在邏輯,以期回歸政治文本翻譯即認知趨同的本質,豐富政治等效既有認知體系。
二、“政治+認知”翻譯研究視角
1 政治文本翻譯研究
政治文本翻譯研究以國內外權威機構、主流媒體、學者等發布的政治評述、文獻及相關譯本為主要對象,涉及黨政會議記錄、領導人重要講話、領袖著作、政府工作報告等文件實體。紐馬克(Peter Newmark)在《翻譯教程》(The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中將此類文本歸于“表達型文本”,語義翻譯為其主線,譯者要在確保較高翻譯忠實度的同時依據讀者認知審美能力作出“讓步”(make small concessions to the readership)。
孫吉勝(2017:5)于《國際政治語言學:理論與實踐》開宗明義:“政治通過語言得到表述,語言反映政治,語言為政治服務。”謝旭升(2018:1)的“翻譯政治說”可視為對“語言政治論”的升華:“翻譯歷來屬于上層建筑,其傳輸內容和方式無不與政治意圖相關聯。”政治與翻譯的合道關乎國際政治的語際屬性,是尋求國際話語權,厘定翻譯、政治、權力、意識形態之間聯系的必然過程。田海龍(2002:23)早年曾探討政治語言學的核心議題:“語言與政治的密切聯系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方面是研究語言的政治問題,一方面是研究政治的語言問題。”由此及彼,翻譯與政治的關系研究應也有分野:翻譯的政治和政治的翻譯。前者外延較寬,凌駕于后者之上,指導后者的進行。質言之,譯者需有較強的政治敏感性,堅持本國的文化取向和政治導向,不再局限于語言轉換表象,轉而思考如何將政治內涵融入文本,不折不扣地傳遞給讀者。如何在提升譯文認知接受度的同時“完整”輸出原文政治意義是不容回避的問題,本文試從認知翻譯研究角度進行討論。
2 認知翻譯研究
霍姆斯(James Holmes)于1972年宣讀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將翻譯研究分為純翻譯研究(pure side)和應用翻譯研究(applied side)。純翻譯研究涉及描述翻譯研究(DTS),包括成品研究(product-oriented DTS)、過程研究(process-oriented DTS)和功能研究(function-oriented DTS)。學界視過程研究為認知翻譯的理論源點。霍氏(1972:72-73)指出:“翻譯過程研究涉及譯者在翻譯時思維的‘小黑匣子’內所發生的一切。心理學家一直致力于尋求系統的研究方法,分析和描述其他復雜的心理過程,翻譯過程研究在未來有望得到進一步關注,構建‘翻譯心理學’或‘心理翻譯研究’。”①后延伸至認知層面,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逐漸完善的同時,西方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著手構建認知翻譯理論模型。新世紀,國內譯界也漸將翻譯理論研究版圖拓展至認知領域,學者王寅(2005:15;2006:581)率先提出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截至2020年1月1日,借助CNKI高級檢索功能,以“認知”和“翻譯”為主題詞,共得5 903條文獻結果(如圖1所示),可管窺“認知+翻譯”研究視角的可塑性。認知翻譯研究是多維的,涉及認知隱喻、轉喻、范疇、識解、意象圖式、概念整合、意義建構、框架等,各維度彼此交互,孤立研究易導致理解的片面性。本文綜合討論認知隱喻、轉喻、范疇、識解的實踐應用,嘗試探尋各領域交叉的整體意義。

圖1
3 認知對政治的觀照
認知、政治的“翻譯之緣”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時期,亞氏于《詩學》(Poetics)闡明“修辭”的功能(工具化),即保障語言效果,幫助言語者說服言語對象,獲取政治權威,構建社會秩序。亞氏列舉了包括隱喻在內的諸多手法,視隱喻為“用一詞代替另一詞而不悖意義”(認知隱喻)。古典修辭學早便將“政治”與“隱喻(認知)”相勾連,后者觀照前者。習總書記(2014:162)呼吁:“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從認知角度來看,“三力”要求譯者“繪聲繪色”,求新的同時考慮認知共性;“三好”則要求譯者不能“自說自話”,要減少認知負荷。話語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直接參與社會個體、網絡的構成,是思維的顯化;翻譯內嵌于話語建構,服務于共性認知,表現出與生俱來的政治屬性(認知、政治、翻譯三位一體,呈現梯度性)。要克服政治文化差異,化解“逆流而上”伴隨的邊緣化話語危機,發出受眾“愿聞其詳”的中國聲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有的放矢地對接原文作者、原文讀者、譯文讀者的認知世界是必要的(原作意識+讀者意識≈翻譯意識)。
三、認知“四觀”指導下的政治文本翻譯研究
傳統語義翻譯觀和解釋派哲學翻譯觀②視點不同,各有側重,譯者分飾不同角色:奴仆、傳聲筒、轉述者、鐐銬舞者、闡釋者、改寫者、反理性者等,日中則昃,風格由極端忠實走向極端放縱。認知翻譯觀認為,人類是基于知識儲備(語言+百科)獲取自然經驗、生成概念、固化語言、開展翻譯。“體驗性概念化”(王寅,2008:211)指導翻譯研究,相似體驗之上的再概念化是翻譯的充分必要條件,這與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提出的經驗現實主義一脈相承;政治文本翻譯中觀原則“政治等效”追求的是內涵神似,非表達式的形似,也體現有認知化傾向。綜上所述,“認知+政治”翻譯研究視角下,譯者可視為“理性的創造者”。下文從“四觀”出發論證這一身份定位的合理性。
1 政治文本翻譯的認知范疇觀——變化
吉雷爾茨(Dirk Geeraerts,1994:13)強調“認知語言學相關研究圍繞著語言內部或語言間的范疇化(categorization)現象而展開”。亞里士多德《范疇篇》確立經典范疇觀,后經演繹形成西方二元對立的(翻譯)研究思維,而以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為指導的原型范疇框架打破藩籬,范疇邊界模糊化而產生范疇連續體,范疇成員地位不等化。范疇劃分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范疇對應抽象概念,范疇化的概念構建涉及主觀感知、知識結構、實體功能、現實語言、社會文化等內外部因素。王寅(2006:91)將范疇定義為“認知主體對外界事物屬性所作的主觀概括,是以主客觀互動為基礎對事體所作的歸類,是由一些聚集在一起的屬性所構成的‘完形’概念構成的。”在此意義上,廣義的翻譯可視作體認觀之上的范疇“延異”,狹義的翻譯即兩種語言或語言變體間的范疇轉換。譯者借助容器圖式對原作者所劃分的范疇系統進行認知重構,動態轉換,依照重新劃分程度及表達方法的不同,大體涉及范疇移植、范疇對應、范疇替換和范疇轉層。
1.1 范疇移植
范疇移植針對翻譯過程中的范疇零對應現象,多由政治文化極差導致,譯者為“重塑”文化精髓,翻譯“暴力”③在所難免。換言之,異質文化以翻譯為媒走出國門,走進異域,碰撞和距離客觀存在,文化磨合、矛盾消解需要過程,只有化矛盾沖突為交流互鑒,文化才能走向統一。具體實踐采用“音譯”和“義譯”,是期望讀者主動迎合接受的“窄眾”翻譯路向。政治文本翻譯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涉及政治文化原則問題,譯者要立場鮮明,堅定文化自信。
(1)ST:中國太極和印度瑜伽、中國中醫和印度阿育吠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④。
TT:There are amaz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s Taichi and India’s Yoga, and China’s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India’s Ayurveda.
太極源自《莊子》,凝聚了道家文化的精華,除是功夫名稱外,更作為一種為人處世的傳統與中華兒女血脈相連。因此,太極的政治文化價值不容模糊,在功夫或文化范疇內盲目尋求橫向替換。范疇移植可激發譯文讀者認知主動性,留下一定的解碼空間,通過以中釋中的形式激活讀者腦海中的太極框架,為中國話語在國際社會爭得生存空間。
1.2 范疇對應
結構主義翻譯觀強調工具理性,聚焦符號轉換的表象;認知翻譯觀主張發掘表象背后的意義再生路徑,翻譯服務于跨文化交流,體現出認知趨同的本質。具言之,原文與譯文讀者可能存在概念認知重合,跨語范疇可直接對應。這種情況下,譯者宜采取直譯策略,復刻原文范疇中的意象,同化認知體驗。國家領導人身份地位相仿,隱喻思維存在共性。政治化群眾語微言大義,蘊藏著引人深思的哲理。
(2)ST: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
TT:Since it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in 2012, the CPC has been committed to both caging the “tigers” and swatting the “flies”.
習總書記以老虎、蒼蠅喻指大小腐敗分子,隱喻認知機制下文另有詳述,“老虎”、“蒼蠅”直接對譯為tigers,flies,生動形象,讀者結合語境可輕松領會實指貪官污吏。
1.3 范疇替換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類認知事物的主觀方式不同,劃分范疇的客觀標準不同,對應范疇所涵蓋的意義可能大相徑庭,不同范疇的具體意義也可能趨于統一。面對主客觀差異,譯者相機采取范疇替換策略,主動求“易”,易為變,變為達旨。新時代,之所以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及諸多中央文獻外譯本一經問世就全球“圈粉”,出版量、關注度、影響力等方面均開創先河,“送去主義”發揮了重大作用。
(3)ST:各級政府必須真正過緊日子。
TT: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must truly tighten their belt.
原文譯文借助不同的喻體(范疇)對政府必須節流的現狀進行隱喻化敘事。原文中“過緊日子”是我國具有代表性的群眾語言,若采用范疇對應策略可能會對給譯文讀者造成認知障礙。是故,譯者主動發掘譯語資源中適切的喻體進行替換,tighten one’s belt作為英語世界耳熟能詳的俚語,譯文讀者可心領神會,范疇替換既照顧了受眾的認知能力(翻譯效度),也滿足了其審美需求(翻譯溫度),真正實現了認知趨同。
1.4 范疇轉層
范疇具有層次性。范疇化縱向維度(自上而下)是種從抽象到具體的層次關系,不同層次范疇抽象度有別,依次呈現“種類包含關系”(class inclusion)(文旭、肖開容,2019:21)。概念范疇具有三大層次:上義層次、基本層次、下義層次,結構上類似于金字塔(王寅,2006:141)。上義層次不具備體驗“完形”,不易于識別,具有高度概括性,是模糊化的基本層次。基本層次是人類認識世界最直觀的范疇層次,是認知交際的基本單位,具“共有完形”,是認知經濟性原則(以最小的認知投入獲得最多的概念信息)下構建認知世界的“最優解”。下義層次兼具各大概括性屬性,是細化的基本層次,也是認知世界的最小范疇單位。例如,基本層次范疇“貓”的上、下義層次范疇可對應“動物”和“加菲貓”。政治文本翻譯也常涉及高文化負載性、文學性、情感性表述,借助范疇轉層,可以有效規避過度認知、模糊認知風險。
(4)ST: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
TT:But with the Opium War of 1840, China was plunged into the darkness ofdomestic turmoil and foreign aggression…
“憂患”自成一詞,相較于turmoil(騷亂),aggression(侵略)屬于上義層次范疇,后兩者則為基本層次范疇,可對應具體事件(下義層次如“英法侵略”)。若范疇對應,直譯“內外憂患”(hardships)難以引起共鳴。外敵入侵是致使近代苦難的直接原因,上義層次轉向基本層次,讀者可直觀認識苦難源頭。若由上義層次直接轉換為下義層次Western aggression,忽略受眾意識,缺乏客觀性,譯文讀者可能滋生抵觸情緒,難以平衡認知。
2 政治文本翻譯的認知隱喻觀——映射
隱喻(metaphor)具有創造性,被認為是感知世界,解釋世界的必要手段,是人類最基本的認知方式之一,構建了大部分的概念系統。換言之,大部分個體概念必須在其他概念的基礎上才能被部分理解。認知關聯性決定人類可在已有自然經驗的基礎上,借隱喻機制定義其他模糊化的自然經驗(部分定義)。自然經驗“隱喻式輻射”導致概念隱喻化:某一概念域的突出屬性映射到另外一個概念域中。這種概念跨域映射實質是尋找認知上的概念共同點。翻譯跨語變化和隱喻跨域映射彼此交互,某種程度上,翻譯即隱喻。翻譯引進新知,隱喻創造相似⑤,以已知喻未知,最小化認知代價,具高性價比。文旭和肖開容(2019:25-32)認為,翻譯隱喻有對應性、解釋性、創造性、文化性。竊以為,翻譯隱喻還體現聚焦性、變異性。既定概念應是多維度多層次完備化的,隱喻創造的是概念群,彼此之間不可能涇渭分明,這是概念隱喻化、翻譯隱喻化的基礎。一則隱喻至多部分構建、框定一個概念,認知上的概念共同點作為突出屬性得以前景化,各概念域的獨有屬性默認背景化,如下文所引“抗擊疫情的巍峨長城”,強調了中華兒女抗擊疫情決心之堅定、人心之團結,卻無法細細刻畫抗疫過程中的點滴暖心細節等。譯者要把握概念間的隱喻性聯系,確保“張冠李戴”的合理性,預估受眾的認知能力,借助喻體保留、喻體轉換、喻底補充、喻義直敘等翻譯策略進行跨語跨域映射。王斌(2010:91)對隱喻的翻譯和隱喻式翻譯加以區分,本文側重前者,兼顧后者。
2.1 喻體保留
具身認知決定具身翻譯,人們同處一個客觀世界,身體結構、感知能力、認知方式相近,認知必然趨同,即使語言種類、表達不同,借助翻譯進行切實有效交流的目的始終是一致的。基于此,隱喻翻譯必定存在平行映射,雙語喻體功能對應,譯者保留喻體直譯,賦予受眾相近的認知體驗。保留喻體即保留“文學味”,增強文本可讀性,直觀說明問題,旨在“翻譯本土,理解世界”(translate local,understand global),彰顯文化自信。
(5)ST:中華兒女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筑起了抗擊疫情的巍峨長城。
TT:Through all these efforts, we, all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have stood together in the most trying of times and built a Great Wall of solidarity against the epidemic.
原文以“巍峨長城”模糊化處理抗疫過程中人民的所作所為,涉及喻體長城。自始皇帝下令修筑起,長城作為拒匈奴于蠻夷之地的屏障,歷朝歷代皆受重視,以“巍峨長城”比擬抗疫實景,彰顯人民之偉大。采取直譯保留喻體,譯文讀者稍加聯想,便可通曉其意。長城是我國的名片,直譯處理有助于知識(文化)遷移。
2.2 喻體轉換
認知翻譯觀提倡“聚同化異”,各民族思維習慣、語言表述有別,有時也會以不同喻體定位同一事物。若譯者在此時保留喻體,或將阻礙讀者理解,甚至可能導致誤讀。為保證政治意義傳遞,需尋找讀者廣泛接受的喻體替代原文喻體,謀求語用等效。政治文獻中常引經據典,以群眾語貼近讀者,“四兩撥千斤”,文化認知障礙相應存在,譯者常轉換喻體,降低認知難度。
(6)ST: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TT: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none other than gold and silver mines.
“兩山論”是新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外交“金句”,譯本眾多,可從不同層面對譯者譯為進行分析。本譯文摘自楊全紅教授(2018:97),《十九大報告》將“金山銀山”模糊化為invaluable assets,譯者考慮到認知壁壘,舍棄了喻體。楊教授借助機器翻譯提出新譯,以金礦銀礦喻指無窮財富,關于金礦的寓言在西方廣為流傳,金礦銀礦概念更易為讀者接受,化解了不必要的概念沖突。
2.3 喻底補充
《圣經·舊約·創世紀》載有巴別塔之謎,上帝搞亂人類語言,溝通障礙產生,塔建計劃擱淺。語言差異性的“上帝假說”有待商榷,但差異是客觀事實,譯者使命就在于消融語言隔閡。由于文化極差,譯文讀者可能對原隱喻關系聞所未聞,概念認知零對應。譯者可直譯原喻體,并增譯喻底補充說明,解釋性文本更易接受。要同步實現文化輸出、政治信息傳遞,喻底補充是上佳策略。
(7)ST:這次教育實踐活動借鑒延安整風經驗,明確提出“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
TT: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for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the Party’s mass line have been clearly defined: “Examine oneself in the mirror, straighten one’s clothes and hat, take a bath,and treat one’s disease.”
此處采用一連串的隱喻策略,如僅對號入座,直譯“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難以實現交際目的。譯者增譯,將一串隱喻直接與黨的群眾路線總要求掛鉤,確保意義傳遞。
2.4 喻義直敘
南京大學中文系葛桂錄教授認為比較文學沖決了曾經是人為的界限,能使學生“在多元的文化語境中重新認識自己,為自己提供一種認識自身的他者眼光。它能啟發我們在閱讀和分析作品時,要具有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化的宏闊視野,不斷嘗試更換一種角度理解作品,才能有新的發現、新的啟示。這對于打破既有的思維框框和認識局限,擴大學生的知識視野與信息容量,更新知識結構,培養一種觸類旁通的辯證比較思維能力,都有很大的現實意義”。[10]
語言是政治文化的載體,翻譯涉及諸多難以調和的矛盾,不可譯由此而來。但這恰恰也反映翻譯的必要性,呼喚著可譯性。譯可譯,非常譯,譯者重塑政治文化元素時,可取喻義而舍喻體。如前所述,我國政治文獻多具有高文化負載性,譯者要堅持政治性為第一性,突出喻義、舍棄喻體是跨越鴻溝的路徑之一。
(8)ST: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
TT:One way in which socialism is superior to capitalism is that under socialism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can work as one and concentrate their strength on key projects.
中國棋文化源遠流長,以圍棋為代表的棋類運動講究協調統籌的整體觀。陰陽、和合等思想精粹皆匯于“一盤棋”,西方對棋的定位并未上升到這一高度,不存在文化認知對等。譯者固然可以采用“喻底補充”策略,或另加注說明棋的文化意義,但結果往往是文本重心偏移,本末倒置。故無需浪費筆墨,白描喻義團結協作即可。
3 政治文本翻譯的認知轉喻觀——借代
萊考夫和約翰遜(2015:32-33)將轉喻(metonymy)視為“用一個實體指代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實體,包括傳統修辭學者稱為‘提喻’(synecdoche)的手法,即用部分指代整體。”也就是說,轉喻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修辭格,更是一種認知機制,體現實體間的認知關系;不僅是語言現象,更是一種概念現象:某認知域或理想化認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內,概念實體A為概念實體B提供心理通道的認知過程,不同于概念隱喻跨域映射,轉喻聚焦同一域內部分和部分和整體和部分的指稱,是域內橫向借代活動(文旭、肖開容,2019:41)。類似于隱喻,轉喻的翻譯和翻譯的轉喻也需加以區分,本文主要探討前者,稍涉后者。概念實體轉喻有賴于概念鄰近性,各民族利用轉喻認知機制建構概念的過程中,喻體常各異。因此,轉喻認知機制或可為“翻譯即改寫”提供理據。翻譯與轉喻亦有相似之處。譯無定譯,譯者永遠不可能完全復刻原文,只能基于對原文的認知嘗試“畫瓢”,是主觀的、有傾向的,是對原文核心意義的理解預估(凸顯),聚焦最具代表性的內容。宏觀來看,翻譯是“部代整”的轉喻:譯者把握核心意義,翻譯水到渠成;譯者以偏概全,誤譯產生。具體而言,譯者需明確借代關系,即整體代部分、部分代整體、部分代部分,靈活運用等化、顯化、釋化等策略,確保語際指稱效果的近似。
3.1 等化
認知共性決定各文化社團借轉喻構建概念常會選擇同一喻體,表達式結構、成分的相同或相似是基于類似的轉喻思維。在這種情況下,譯者只需對譯共同喻體,實現雙方讀者心理意象的趨同。
TT:Every Communist must grasp the truth,“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是毛主席強調武裝斗爭的經典政治話語,此處以“槍桿子”喻指武裝斗爭,屬“部代整”借代關系。中西方對槍的認知存在重合,讀者對譯文心領神會,轉喻的修辭功能也得以再現。
3.2 顯化
轉喻翻譯常訴諸于喻體轉換、喻標顯化,體現個體認知的差異性。政治文本翻譯要求譯者實現以偏概全的去主觀化,綜合考察譯文讀者的思維邏輯、現實需求和心理預期。
(10)ST:增進互信、深化合作,迎接中歐關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TT:Enhancing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to Embrace an Even Better Future of China-EU Relations
原文標題以“明天”指代未來,即“部代整”借代關系,體現我國對中歐關系發展寄予厚望,只要互信合作,美好關系就在明天。若對譯成tomorrow或與事實存在出入,可能造成誤讀。此時喻標顯化是必要的,凸顯譯文的客觀性。若以喻體轉換思維審視,此處喻體“明天”也可替換為prospect(前景)。
(11)ST:賣官帽、批土地、搶項目、收紅包,變著花樣收錢斂財……
TT:Some continue to sell official positions, illegally sell or lease out land, scramble for a cut of lucrative projects, and use every means to collect bribes…
以bribes對應原文“紅包”,是對紅包意義的細化闡釋。譯者采取文化過濾策略,紅包的喜慶、吉祥等積極意義弱化,貨幣交易屬性得到突出。
3.3 釋化
讀者的認知盲區客觀存在,轉喻功能可能無法實現,譯者要依據讀者的預認知能力進行解釋性翻譯。政治文獻寓理于史,經典人物對于西方讀者十分陌生,譯者在音譯(直譯)出姓名的同時,仍需還原歷史背景,釋其身份地位,實現跨語轉喻。
(12)ST:這少數人打倒了,“魯智深”解放了。
TT:Once this small number is overthrown, ordinary monks like “Lu Chih-shen”will be emancipated.
《水滸傳》中的人物魯智深在國內家喻戶曉,原文泛指和尚群體。顯然,這一人物形象在普遍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認知接受度較低,譯者通過釋其身份,還原喻標,或可實現讀者認知反應趨同。
4 政治文本翻譯的認知識解觀——整合
學者謝天振(2012:33)贊埃斯卡皮的“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并詳述于《譯介學》中。學界對此反響熱烈,褒貶不一,竊認為,認知識解觀(cognitive construal)或可為其提供理論支撐。認知之所以與生俱來帶有主觀色彩,是因人類或多或少有解析事物的主觀能力,對世界進行有意或無意的識解重構,總體取向可歸于“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語言是認知思維的外顯,透過既定語言形式表象,可窺探人類的識解路徑。文化翻譯觀視翻譯為創造性的意義重塑,然歸根到底,譯法有別是因譯者對原文的識解方式、角度、原則不同,翻譯是識解化的過程,是創造性的叛逆(以原文為參考點),譯者與讀者之間存在供求關系,向讀者提供原作者未涉獵的、讀者想看到的東西。蘭蓋克(Langacker)早期從詳細度、圖形-背景、突顯、視角、選擇等多方面探究認知識解,而后于Essentials of Cognitive Grammar正式規范詳細度(specificity)、聚焦(focusing)、凸顯(prominence)和視角(perspective)四大維度,可作為研究政治文本翻譯識解化的理論框架。
4.1 詳細度
人類依照自我認知進行范疇化描寫,涉及兩種趨勢:細化和泛化。“文章合為時而做”,時間、空間、環境、對象等因素不同,對語言表達式的詳細度要求不同,細化識解剖析細節,有主觀偏重方向;泛化識解則強調對事物的高屋建瓴式的理解認識。政治文本翻譯服務于政治目的和文化外宣,譯者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權衡內容、形式的關系,采用同化、細化、泛化策略。
(13)ST:……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TT:…hold high the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4)ST:真想搞建設,就要搞點骨干項目,沒有骨干項目不行。
TT:If we really want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all have to carry out some key projects.
(15)ST:……但是人道主義有各式各樣,……
TT:…But there are a thousand and one definitions of humanism.
(16)ST:現在人們議論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繼續保持繁榮,就會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
TT:The main concern of people today is that if prosperity is not maintained in Hong Kong, it might retard China’s drive for modernization.
例(13)中譯者并未泛化旗幟意象,意在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引領作用。例(14)中原文“建設”細化為經濟發展,符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興國之要,突出重心。例(15)中譯者借助夸張的量化譯法,說明人道主義的多面性。例(16)中四個現代化建設(農、工、國防、科技)泛化為現代化,因語篇層面上是談論香港問題,而非現代化建設,泛化處理,層次分明。
4.2 聚焦
譯者主動施為,干涉信息加工過程,在“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前提下選定內容,組織語言,厘定既定內容的特定表達區域,規約前景后景(foreground/background)。譯者為確保交際順利,可能會對原文既定內容和特定區域作出調整。政治文章的翻譯講政治(程鎮球,2003:20),譯者必須具備政治敏感性,借助聚焦轉換,避免誤讀,不給負面言論借題發揮的機會。
(17)ST: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包括各民主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選擇……
TT:CPC leadership is the common choice by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all political parties, people’s organizations, ethnic groups, social strata, and all walks of life.
“民主黨派”在西方存在對應表達Democratic Party,早期國內也挪用了這一說法。然二者內涵完全不同,我國的民主黨派是指除我黨外的八個參政黨,并非西方國家的民主黨。這一譯法也讓負面言論有機可乘,聲稱中國只有八個民主黨派,用心昭然若揭。譯者及時轉換思維,聚焦民主黨派的政黨性質,對“民主”進行弱化處理,實現認知層面的量身剪裁。
4.3 凸顯
凸顯亦是譯者的主觀行為,涉及信息取舍、重排,研究對象主要為勾勒(profiling)與基體(base)、射體(trajector)與界標(landmark alignment)。簡言之,勾勒較于基體是被凸顯的部分,后者是相關認知域的范圍,是背景化的。同理,射體是最凸顯的概念實體,而界標作為次凸顯的實體,為射體提供參照系(文旭、肖開容,2019:137)。中西語言分屬綜合語和分析語,語言結構存在差異。譯者前景化勾勒需要強調的部分,同時將其他部分背景化為基體,襯托前者。一言以蔽之,凸顯是主觀譯者思維與客觀文本結構協商后的結果。政治文獻邏輯連貫,句式嚴謹,譯者需權衡主次文質,重排譯文結構,迎合譯文讀者的認知閱讀習慣。
(18)ST: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
TT:We have made major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連淑能(2010:35)提出:“句中若有意思強弱、程度輕重或范圍大小的部分,英語常常是先弱后強、先輕后重、先小后大,漢語的順序相反。”經濟建設作為取得成就的領域要得到強調,故原文開門見山,譯文則娓娓道來,處理方式雖不相同,但本質都是為了突出強調。此外,譯者在無主句基礎上添加主語we,彌合中西思維認知、語言習慣上的差異。
4.4 視角
視角即認知、解釋事物的切入點,既體現在現實空間層面,又表征于非現實概念層面,主要由視點和焦點兩大元素構成。視點為語言表達式的出發點,是交際中所選擇的心理路徑(mental route),不同視點代表不同認知路向(approach),語言表述形式也相應存在差異;焦點是認知主體的認知側重點(文旭、肖開容,2019:140)。翻譯視點選擇尤為重要,視點不同,譯文的側重點隨之不同。政治文本翻譯重視政治思想的傳遞,文本的政治意義一方面來自語言本身,一方面依賴譯者的主觀賦予(言外之意)。
(19)ST:打鐵還需自身硬。
TT:1. To be turned into iron, the material itself must be strong.
2. One has to be very strong if he wants to strike the iron.
3. To strike iron, the hammer must be strong enough itself.
俗語“打鐵還需自身硬”頻出于政治文本,官方譯法不一,意義存異,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各譯法背后的認知理據有待深挖。不同于其他俗語,“打鐵還需自身硬”本身意義便有爭議。譯文1以鐵為視點,即鐵(被打)還需自身硬;譯文2以鐵匠為視點,即(鐵匠)打鐵還需自身硬;譯文3由肖坤學教授提出(2013:111),基于認知語言學框架理論和概念隱喻理論,以鐵錘為視點,即(鐵錘)打鐵還需自身硬。視點不同,所譯自然有別,雖一名多譯,卻都言之有物。“打鐵還需自身硬”作為符號集合,本身意義(政治文化意向)是不確定的,譯者基于不同語境從不同視點創造性認知,賦予符號意義,服務政治交流這一根本目的。不揣淺陋,筆者基于大語境(應用場合)和小語境(上下文),認為鐵匠視點在更多情況下更符合讀者的認知邏輯,拙譯為To make good products, the blacksmith himself must be strong.
本文從認知“四觀”出發,結合譯例對政治文本翻譯的宏觀認知機制和微觀譯法進行了討論。認知為上層追求,政治是基本前提,翻譯即具體手段。“政治+認知”翻譯研究模式的興起實為必然。翻譯,尤其是政治文本翻譯,是認知化了的,無論譯者如何建構表達式(或重形重義,或舍形取義),政治意義傳遞都具有第一性,譯文都是認知思維的顯化。認知翻譯觀賦予譯者新的身份:“理性的創造者”。“知先譯后”,譯者“謀而后譯”,譯文體現出主客觀性,迎合經驗現實主義。翻譯概念呈現多維度完形特征,是持續抽象化發展的。何為譯不存在標準答案,認知“四觀”均可充當定義翻譯的媒介,生成參考答案。換言之,翻譯可片面理解為是主觀范疇化、隱喻化、轉喻化、識解化的過程。認知導向下的政治文本翻譯是一項使命,認知盲區、文字陷阱規避是一種責任。“四觀”彼此關聯,印證人類同中守同、異中求同的認知取向,與翻譯求同的本質相互印證。政治文本翻譯依賴叛逆性認知,非單一的派生,多元綜合論替代傳統忠實論,認知學理可為其提供理論支撐。以識解為代表的認知取向在指導翻譯實踐的過程中常會造成文本內容、形式的變化,契合“變譯”,核心目的是“達旨”。
四、認知翻譯之于政治等效
1 政治等效(political equivalence)
2008年以來,學者楊明星立足于等效理論,結合外交翻譯的特殊屬性,創立并發展政治等效翻譯原則。政治文本翻譯中,譯者必須準確、忠實地反映原文和原作者(或說話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語境,同時使用譯文讀者(或接收方)所能理解的方式來表達,以追尋外交翻譯的理想目標:傳達出原文的政治內涵;實現相同或相似的交際功能(楊明星,2008:91-92;2020:153)。2018年,楊明星明確外交修辭的復雜性,認為具體翻譯實踐超出了政治等效的觀照域,故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上文所述的梨式(PEAR)原則,首創“政治等效+”翻譯框架,以復合式翻譯標準分類解釋外交翻譯實踐中的不同現象,使復合型文本翻譯得以“有法可依”。
政治等效有三性:政治性(political orientation)、平衡性(dynamics)、動態性(equilibrium),政治性是最顯著的特征,涉及國家利益、國際關系、文化 / 意識形態差異、政治立場等因素,平衡性突出對原文語境意義的把握,動態性強調譯者的多重使命,于原文與譯文、說話主體與受眾、歸化與異化間尋求平衡。實踐也分三步走:理解原文,剖析語境,聚焦難點;恰當翻譯,服務讀者,近似效果;結合“三性”,評估效率,對比原文,反思譯文(Yang & Yan,2016:664-665)。翻譯政治外交文本,譯者要充分自省,譯前三問:譯為何、何為譯、如何譯,體悟政治等效之本真(in a real sense)(ibid.:665)。
2 認知趨同(cognitive consonance)
王寅(2005:15-18)基于西方哲學發展先后歷經的本體論、認識論、語言論,歸納出體驗哲學和認知語言學的基本原理現實-認知-語言。認知是溝通現實和語言的媒介。要想生成語言,乃至翻譯,必牽涉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原文讀者通過理解原文意義創造性地還原原作者眼中的這兩個世界;譯文讀者理解譯文還原譯者兩個世界,原作者、譯者實為語言文化交流中介。認知趨同的前提在于文本創造者(作者、譯者)的概念認知存在共生關系。換言之,譯者需有意識地復刻原作者勾勒的兩個世界,滿足譯文讀者。誠然,譯者與原作者“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讀者認知反應完全相同”也只是一種悖論。譯者要預估譯文讀者的認知世界,并作為第一讀者構建對原作的自我認知世界,實現對接。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別,讀者對文本的認知體驗也必然存在差異,譯者的使命就是盡量消解差異及差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3 “政治等效+認知趨同”:政治文本翻譯的認知視角
學者呂俊(2001:9)提出,“(結構主義)翻譯研究始終沒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也始終是對同一性與一致性的追求”。類似表述在學界有很多,結構主義的非完美、局限性客觀存在,這是無法回避的,但其跨學科適用性(applicability)也是不容抹去的,Yang(2012:5-8;2016:663)言及聚焦外交語言的翻譯問題,學者的質疑對奈達等效翻譯理論的適用性并未帶來很大的影響,奈達的等效翻譯原理雖有一些缺陷,但并未過時,對當今的翻譯理論研究,特別是外交語言翻譯實踐,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質言之,政治等效雖借助西方語言學框架,內在卻統合和合、中庸之道,體現傳統哲學的整體觀、發展觀,真正實現了“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政治等效+認知趨同”復合標準的構建也并非空穴來風,要實現“意義不倍原文”,譯者的語境認知能力(contextual cognition capacity)是關鍵(Yang,2012:672)。語境釋義、制約話語,話語反過來操縱、構建語境。譯者介于語、境之間,以主觀認知實現二者互動,服務于讀者認知。整體來看,政治等效是回答對不對的問題,認知趨同是追求好不好的問題;政治等效是認知趨同的前提綱要,認知趨同是政治等效的反證之道。
五、結語
中國故事博大精深,做到講好實屬不易;政治文本翻譯方興未艾,翻譯中國任重道遠。政治文本翻譯因其特殊性從應用翻譯體系中脫穎而出,只有系統把握受眾的認知能力,才能“投其所好”,發揮文本交際和政治文化播撒功能。本文基于認知翻譯“四觀”,考察政治文本翻譯語言現象背后的認知理據,明確除了要講政治,也要講認知。譯者是“理性的創造者”,極端化的翻譯思想是不足取的,合格的翻譯建立在主、客觀“圓滿調和”的基礎上,對文本政治性的追求可落腳于認知層面,對接認知世界,實現政治文本翻譯認知化。認知趨同是實現“民心相通”的充分必要條件,譯者要做到“因時因勢因地制宜”,才能“譯有所為”,完成翻譯的認知使命。基于楊教授構建的“政治等效+”理論框架,思考認知、政治的內在關聯,擬提出“政治等效+認知趨同”(PECC)復合翻譯框架,以期更好地指導政治文本翻譯實踐。
致謝:感謝楊明星教授為本文修訂提供的寶貴意見。
注釋:
① 本文所引英文文獻均由筆者自譯,有所側重,不再重復標注。
② 王寅(2007:569)在《認知語言學》中指出,傳統語義觀涉及指稱論、觀念論、功用論、替代論、語境論和關系論,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迦達默爾的解釋主義、德里達的解構主義之間具有觀點上的傳承關系,并將其統稱為歐陸解釋派哲學理論。
③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主張翻譯“暴力”(violence)說,十全十美的翻譯只存在于烏托邦。翻譯或多或少都涉及“暴力”,“暴力”在此并不是貶義詞。
④ 本文所用譯例中的粗體均為筆者所加,不再重復說明。
⑤ 概念相似性并非是固有存在或者約定俗成的,存在習得的過程。與其說隱喻所涉及的概念實體具有相似性,不如說隱喻創造了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