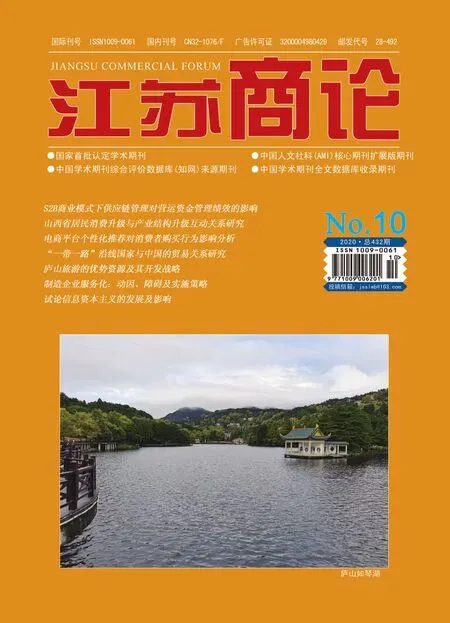山西省居民消費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互動關系研究
閆海鷹
(山西農業大學 信息學院,山西 太谷030800)
一、研究背景
目前, 我國居民消費與產業都呈現升級現象,并都呈現持續增長趨勢。2018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大力發展創新消費業態和模式,推動消費升級,不斷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相關數據表明, 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在2019 年已經達到57.8%,消費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挖掘消費潛力,引導消費升級,推動產業升級是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主旋律。
相關研究表明,當人均GDP 達到5000 美元時,科技創新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此時需加大培育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和創新型等產業。 大量研究證明,居民消費與產業結構升級存在高度相關。 國外學者庫茲涅茨早在1989 年就提出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密切相關①。 國內學者如崔海燕研究了山西省居民消費升級與產業結構發展的現狀及問題,并提出意見建議②。 肖國東系統分析了在“新常態”發展模式下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存在的雙向影響關系③。 劉宛晨等通過建立PVAR 模型,驗證我國中、東、西三個地區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對產業結構轉型的推動效應, 提出優化消費結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以促進產業結構更加合理的意見建議④。 宋毅等基于VAR 模型分析了廣東農村消費水平與產業升級關聯性研究,研究發現二者存在長期動態均衡關系⑤。 朱云娜等以東北地區消費數據為基礎, 研究認為消費結構能促進經濟增長,同時經濟增長又可帶動消費結構升級⑥。 侯春輝等選取甘肅省居民消費結構和三大產業結構數據,建立VAR 模型, 對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分析顯示,居民消費升級對產業結構升級貢獻度更高⑦。
以上研究都表明消費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長期互動關系,同時,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會帶動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社會、經濟效益。
二、山西省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發展情況
(一)山西省居民消費升級發展趨勢
本文通過整理分析山西省近10 年數據可知,在山西省城鎮和農村食品、衣著、居住、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務、教育、醫療、其他服務八大類消費結構指數數據中,食品消費支出占比最大,但所占比例一直處于下降趨勢;教育、醫療、居住、交通通信支出比重持續增長。 相關數據顯示,城鄉居民在不斷提升生活質量,消費結構趨向更加復雜化和合理化。 當前,山西省居民消費升級呈現出從大眾產品到高端產品轉變,消費結構更為均衡,并從生存型消費向享受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轉變的升級趨勢。 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杠桿率的增加,儲蓄率的下降和中高等收入人群占比的增加是促進消費升級的關鍵因素。
(二)山西省產業結構發展趨勢
通過分析山西省2000—2018 年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變動趨勢可知,山西省三大產業整體都呈現增長現象。 其中,第一產業增長趨勢較平穩;第二產業在2008 年后出現大幅波動,有增有減;但第三產業始終保持平穩增長趨勢, 增速在2014 年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增速和增量最大的產業。 綜合來看,近年來山西省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和優化, 第二、第三產業已經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性產業。
三、山西省居民消費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互動關系分析
(一)變量選取及指標構建
本文對山西省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結構數據進行處理,采用信息熵分別計算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指數。對山西省GDP 及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數據進行處理, 從而計算得出產業結構升級系數。借鑒居民消費結構信息熵代表消費結構,公式計算如下:

其中:i 表示消費項目種類,且i=1,2,…n, Pi表示第i 種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且通過消費結構信息熵的大小表示消費結構變化程度,H 值增加, 說明消費結構復雜程度和合理程度更高;H 值減少, 說明消費結構復雜程度和合理程度更低。 分別用CC、RC 來表示山西省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信息熵。
用第二、三產業之和占GDP 的比重來表示山西省產業結構升級指標,公式計算如下:
SC=(I2+I3)/GDP
其中:I2和I3分別表示山西省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增加值,GDP 表示國內生產總值, SC 的大小表示產業結構的級別,指標越大,說明產業結構越高端;指標越小,證明產業結構越低端和不合理。 計算整理結果見表6。
(二)模型構建及分析
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AR),驗證山西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雙向作用,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 yt=(CC,RC,SC)T,c 是常數項,Ai為參數估計矩陣,q 為向量自回歸滯后期數,εt為隨機擾動變量。
1.單位根檢驗分析。 首先檢驗山西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指數及產業結構升級指數的平穩性,檢驗通過后再對模型進行估計。 通過采用Eviews8.0 進行單位根檢驗,變量CC、RC、SC 原假設檢驗都存在單位根,模型不穩定,分別對CC、RC、SC 進行一階差分優化,檢驗結果表明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都通過檢驗,且均是平穩的,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

表1 山西省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指標

表2 變量單位根檢驗
2.最優滯后階數分析。 運用LR、FPE、AIC、SC、HQ 五種檢驗方法最終確定模型滯后期數, 檢測結果顯示所有變量值均選擇滯后3 期,確定最優滯后期數為3,建立VAR(3)模型進行后續分析,見表3。
3.模型穩定性分析。 方差分解的前提是模型穩定性高,構建“單位圓”模型,依次觀察是否所有檢測值均落在單位圓內,若都在單位圓內,則模型是穩定的,檢測結果如圖1 所示。 從圖1 可知,所有檢測值的倒數都在“單位圓”內,模型比較穩定。

表3 最優滯后期檢測分析

圖1 模型穩定性檢驗圖
4.格蘭杰因果檢驗。 表4 反映了變量CC、RC、SC 之間的格蘭杰因果,從表中可看出,在顯著性水平10%下,山西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互為格蘭杰原因,兩者互為因果變量。 居民消費升級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升級也提升居民消費水平,促進消費結構更加合理化。

表4 格蘭杰因果檢驗
5.方差分解。 通過方差分解分析山西省城鎮居民消費升級指數CC、農村消費升級指數RC 以及產業結構升級指數SC 的變化趨勢, 預期影響值設定為10,分析結果如表5 所示。
同理可對山西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進行方差分解,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山西省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化的影響為0.00%—5.36%;對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化的影響為0.00%—19.18%,并且影響力是不斷升級增加的。 在產業結構變動中7.89%—32.49%由城鎮居民消費升級推動,12.33%—35.48%由農村居民消費升級推動。 同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并不同期,而是滯后于產業結構升級對消費升級的影響。 從方差分解結果依然可看出,山西省居民消費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存在雙向影響關系。

表5 山西省城鎮居民消費升級方差分解結果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建立VAR 模型, 對山西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進行實證檢驗,實證分析表明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二者具有顯著相互作用,緩解供需失衡的關鍵在于產業結構升級。
為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不斷提高山西省城鄉居民收入,減小高低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導致消費結構、規模的變動,同時也帶動產業結構轉型, 因此要提升中高等收入人群數量,通過收入推動消費提升,優化產業結構。 二是調整優化消費結構,擴大服務型消費影響力。 針對不同人群收入水平推廣相應產業結構,推進消費結構優化,大力發展旅游、文化、健康、醫療、體育、家政等服務業領域,提升服務型消費水平,帶動第三產業發展,不斷提升實物消費檔次,補齊服務消費短板,培育新經濟增長點。 三是創造公平消費服務環境。出臺系列政策支持企業科技創新,通過技術、產品和服務創新拉動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 同時增強產品和服務標準體系建設,建立重要產品質量溯源體系, 持續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與市場信用機制,創造公平公正的消費環境。四是加強新興產業的培育發展。 隨著政府利好政策對消費升級的推動,“互聯網+” 的深入推進和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應加大傳統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并不斷培育新興產業。
注釋:
①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②崔海燕.居民消費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調整研究——以山西省為例[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5):82-84.
③肖國東.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趨勢分析——基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思考[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5,36(04):106-111.
④劉宛晨,胡永翔.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基于PVAR 模型[J].商業經濟研究,2015,(20):56-59.
⑤宋毅.消費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互動關系分析——以廣東省為例[J].改革與戰略,2018,34(09):49-52+64.
⑥朱云娜, 王雅婷. 消費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互動關系分析——以東北地區為例[J].商業經濟研究,2018,(19):137-139.
⑦侯春輝.甘肅省居民消費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的互動關系研究[D].蘭州財經大學,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