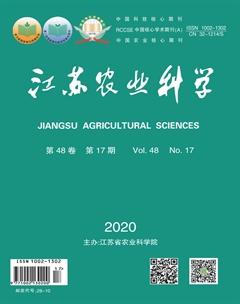精準治理:中國食品安全管理范式轉換研究
鄭曉敏 田富俊

摘要:食品安全問題作為社會公共安全問題,關系到國民健康,受到政府與公眾的密切關注。傳統的食品安全管理在主動性、政策的靶向能力以及治理主體的反應能力方面尚不能應對我國目前劇烈轉型期的各種矛盾。梳理我國食品安全管理的發展歷程,在總結我國食品安全管理現狀的基礎上提出“精準治理”范式,闡述治理的概念和特點,并基于政府精準治理的社會實踐提出關于食品安全精準治理中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推進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主要策略,為深入探討食品安全精準治理提供可借鑒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食品安全;精準治理;互聯網;管理范式
中圖分類號: TS201.6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0)17-0326-07
食品安全是人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標志,食品安全問題關乎社會穩定和國民生命健康,國內外都從國家安全的戰略角度對待食品安全問題[1]。《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GB/T 15091—1994《食品工業基本術語》對食品的概念界定為各種供人食用或者飲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療為目的的物品。而食品安全則是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食品安全的概念已由早期側重食品數量安全轉變為當前側重食品質量安全。
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如皮革奶事件、蒙牛強致癌物質事件等。食品安全問題已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食品安全管理成為飽受爭議的話題。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實施食品安全戰略,目標是到2020年,我國食品工業規模化、智能化、集約化、綠色化發展水平明顯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顯著提高,推進健康中國建設[2]。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食品生產技術的不斷提升,信息技術革命的到來,信息傳播和交流的效率不斷提高,特別是“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治理需求不斷發生變化。在這種背景下,傳統食品安全管理已不能符合時代的需求,食品安全管理正面臨轉型。基于此,本研究以食品安全的精準治理為主題進行深入分析,探索突破傳統食品安全管理范式的方法,從而實現在新時代背景下食品安全管理范式的轉換,提高食品安全治理的精準性。
1 食品安全管理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1.1 管理體制變革過程
我國食品安全管理自新中國成立至今實現了從空白到規整,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基于監管部門設置和監管職責集中度,我國食品安全管理發展歷程可以歸納劃分為4個階段(表1),包括單部門為主的分散化管理時期、多部門分散管理時期、多部門協調管理時期、一體化管理時期[3-4]。
1.1.1 單部門為主的分散化管理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基本延續抗戰時期公共衛生管理工作方式及蘇聯經驗的借鑒,食品安全管理主要由衛生部門負責。1950年起開始設立省級、市級、縣級衛生防疫站,1959年開始增設鄉(鎮)級衛生防疫站。但隨著衛生防疫站規模的不斷擴大,其食品安全管理職能弱化,一些職能逐步轉移至新成立的農業部、食品部、商業部中。1965年,我國第1部國家層面的食品安全管理法規《食品衛生管理條例(試行)》出臺,隨后相繼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試行)》等法律法規。在計劃經濟時代,一些食品實施定量供應,食品生產企業具有國有企業屬性,呈現出明顯的政企合一特點。政府監管以國有企業的“從屬關系”為基礎,企業管理人員兼具官員的雙重身份,重視晉升而非利潤,那時食品安全事故多數是由生產技術、經營管理等客觀因素引起的,管理部門分散,管理方式多為思想教育和質量競賽等,很少使用法律治理及標準化管理手段。
1.1.2 多部門分散管理時期 1978改革開放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食品種類不斷的豐富,食品安全管理部門增加。食品安全管理的重點從防止腸道傳染病轉為預防一切食源性疾病,從初步的衛生管理逐漸擴展至農藥獸藥殘留和食品添加劑控制等。1995年國務院出臺《中國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確立了以衛生行政部門為主,有關部門共同參與的食品安全管理方式,規定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主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有關部門在其職責范圍內輔助負責食品衛生管理工作[5]。1998年機構改革后,食品安全主要由國家衛生部、國家農業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10多個部委按其各自職能進行分段及分散監管,雖然法制化水平顯著提高,但各部門管理工作難以有效協調,處于多部門分散管理狀態,存在諸多管理漏洞,國家層面缺少綜合性協調機構,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2002年。
1.1.3 多部門協調管理時期 2004年阜陽劣質奶粉和2009年蘇丹紅化學制劑等食品安全事故,充分暴露了之前食品安全管理部門因各自為政而出現體系不完善、交叉執法的管理漏洞。針對效率問題,我國在2003年設立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主要負責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協調和監督,形成了國家統一領導,地方政府聯動的管理格局,標志我國在食品安全管理上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200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確立了我國以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食品安全監管模式,強化了農業部、衛生部、質檢局、工商局等部門職責。在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職責被歸為衛生部,省級以下的垂直管理被改為地方分級管理。2009年頒布施行的《中國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明確由衛生行政部門綜合協調食品安全工作,農業部、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分別對食用農產品生產、食品流通、食品生產實施監管,進一步明確了分段監管的管理體制。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國務院在2010年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務院食品安全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食品安全理念逐步形成法律層面的認識,我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力度不斷加大,部門職責分工進一步明確,形成了統一領導、分工負責的監管體制,但未從根本上解決職責交叉與界面不清等問題。
1.1.4 一體化管理時期 新階段的改革主要依據的是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的相關要求,通過精簡管理部門,降低部門間溝通成本,提高行政效率[6]。國務院機構改革中由農業部主要負責農產品安全管理,諸如食用農產品進入批發、零售市場或加工企業前的監管工作;新組建了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要負責食品安全標準制定及風險評估;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職責、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公室的職責、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生產環節食品安全管理的職責、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流通環節管理的職責整合,組建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主要職責是對食品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實施統一監管。本次改革最大的突破是將食品安全管理職責統一整合,提高了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效率,但也面臨是否能真正實現一體化管理,各部門管理工作無縫對接銜接的挑戰。在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進一步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職責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職責進行整合,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1.2 我國食品安全管理現狀
1.2.1 權力邊界日漸清晰,但依然矛盾交織 我國已經形成了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為監督主體,由國家層面的食品安全委員會進行綜合協調、集中統一的監管機制。然而監管運行機制設計不科學,實效性不強,雖然從理論上講已經在體系方面上實現了從食品源頭到生產、加工、倉儲、運輸、銷售的系統化管理,但監管的邊界范圍未明確,存在監管“真空”地帶,這必然會為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的展開帶來負面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在大多時候采用的方式是事后處理,事先預防和檢測的意識薄弱[7]。
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經過多年發展改革,但仍不完善,與國際相比,我國食品安全法律涉及到的種類范圍相差甚遠,需進一步更新完善。我國的諸多法律如《中國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僅僅停留在法學理論的研究上,而未在框架上進行論證,仍然游離于基礎的權利和責任的論證中,未基于法權的角度確立食品消費者權利和生產經營權利以及它們與行政權利的關系[8]。
在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職責整合,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食品安全管理的總體職責,但體系透明度較低,由此造成信息不對稱、縱向協調不合理、行政扁平化未落地等問題。另外,機構改革調整時間過長,作為中間層的市級部門政令的協調和功能的整合缺失,無形中增加了上下協調的成本,且無法將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落實到實處,省市縣政府間權利與利益沖突導致矛盾多發[9]。
1.2.2 監管制度體系框架初步形成,但仍然有待探索
1.2.2.1 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有待理順 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指的是依據食品安全監管法律法規確立的監管部門在分工與協調過程中的關系。我國于2004年發布施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確定了我國食品安全新的管理體制,即以分段管理為主、品種管理為輔的管理機制,明晰了各部門食品安全管理的職責[10]。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表決通過的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食品安全管理的相關職責得到了整合,其中,將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職責整合,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但各部門之間仍存在部門職能交叉、職責界定模糊等問題,需進一步理順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
1.2.2.2 食品安全監管機制有待加強 食品安全監管機制指的是對監管客體進行監管時,監管主體所采用的監管方法,包括正向激勵機制、信息溝通機制和懲罰機制。目前,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正向激勵機制主要有薪酬、官員晉升以及行政問責等方法;懲罰機制主要針對食品企業生產者,包括刑事責任、吊銷營業執照和罰款等;信息溝通機制主要是面向消費者,通過信息標識、網站公開等方法滿足廣大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信息知悉的需求,以及在發生食品安全事故之后減少消費者不必要的恐慌,維護社會穩定。但目前我國的輿情監測相關工作僅覆蓋了國家和省級2個層級,存在較大的監測漏洞及安全隱患,如輿情匯集不全面、反饋不及時、評估不準確等現象。
1.2.2.3 食品安全監管體系有待完善 我國目前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包括認證體系、檢驗檢測體系與風險分析、標準體系、消費者教育體系與社會監督等[11]。現行的食品安全認證體系包括綠色食品認證、無公害食品認證等;食品安全監管標準體系與檢驗檢測體系是指政府及食品行業規定的各項食品安全標準,如食品安全管理體系(ISO22000);消費者教育體系包含對青少年、重點人群如孕婦或特殊疾病人群的食品安全知識基礎教育。由于我國食品行業上至管理者下至員工的食品安全基本知識缺乏,基于無知而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數不勝數,然而食品安全管理相關體系的培訓費用高昂,小型企業無力承擔管理體系的成本。因此,亟需加強食品安全知識教育宣傳工作,加強政府監督、社會監督、消費者監督力度。
1.2.3 技術支撐體系日益完善,但薄弱環節明顯
1.2.3.1 監管執法技術方面 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執法以工作人員現場抽查等傳統檢查模式為主,國內外正積極發展智慧監管技術,但我國的監管技術發展水平較低,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較低,無法滿足食品安全監管的技術需求。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食品經營正不斷呈現新的管理方式,傳統監管技術亟待突破[12]。
1.2.3.2 應急處置技術方面 我國的食源性致病微生物基因組溯源技術才剛剛起步,全基因組技術仍未成熟,相關數據庫和信息分析平臺還未構建。在應急演練方面,以知識傳授為主,缺乏有效的實戰演練,缺乏實戰性、實用性和科學性[13]。
1.2.3.3 評估評價技術方面 我國對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評估模型和數據完善方面。其中,在評估模型方面,主要針對化學危害物建立基準劑量模型以及暴露邊界比法等;在數據完善方面主要側重于毒理學研究和食物消費量調查等[14]。但由于我國在評估評價技術方面起步較晚,滯后于其他發達國家,以傳統方法應用較多,新技術仍未取得明顯進展,實踐價值不高,亟待加快食品安全評估技術研究,為食品安全科學管理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
2 精準治理:一個新的食品安全管理范式
2.1 治理的概念及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特點
2.1.1 治理的概念解析 治理概念起源于希臘語與拉丁語,都包含掌舵或指導的意思[15]。就治理研究而言,有3個里程碑式的機構和人物,分別為經濟學家威廉姆森,美國外交官、教育學家克利夫蘭,世界銀行[16-19]。以世界銀行為例,“治理”一詞最早出現在世界銀行在1989年年底出版的報告《撤哈拉以南非洲:從危機到可持續增長》中[20]。隨后幾年中,世界銀行不斷推動治理的發展,1992年發布了報告《治理與發展》,重點強調“good governance”,為推行良治提出了4個關鍵點,即公共部門管理、問責、法治、信息透明[21-22]。隨后組建專門研究治理衡量指標的團隊,不定期發布各國的治理水平排行榜,“治理”一詞不斷激發學者們的興趣[23]。1990年為治理研究的一個轉折點,學術論文數量爆發式增長,治理研究蔓延到各大領域,比如“城市治理”“環境治理”“網絡治理”等。原“治理”是指統治、管理和控制某個包含國家的行為和方式的實體或事物,本研究中的“治理”指的是由政府及公共部門或者經授權的組織為實現公共政策、滿足公眾需求、維護社會的持續平穩發展,以政策的分析、制定、發布、實施、調整為主要內容的行動或過程[24]。
對于管理范式轉換,過去二三十年,熱衷于治理研究的國內外學者認為范式轉換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普遍趨勢。具體來說,從前的公共管理是政府自上而下進行的層級管理,現在政府在公共管理中不再是獨角戲的角色,強調多元組織參與、社會共治。關于政府管理范式轉換主要有“新自由主義治理”“社會自理”“分權治理”“全球治理”理論[25]。在本研究中,食品安全管理范式轉換指的是以各種方式推動政府角色轉變,從傳統的以政府規制行為、具體管理技術為主的食品安全管理轉變為回應技術變革和主動型治理的食品安全治理,以科學有效的數據分析判斷為治理前提,以全面精準的數據化信息系統為治理基礎,以切實可行的政策知識推理為治理參考,以相宜切合的政策需求匹配為治理目的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創新再造過程。
2.1.2 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特點
2.1.2.1 預知性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給政府食品安全管理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在使其技術提升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因素。各方面的挑戰對政府的前瞻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乃至現在的食品安全管理強調危機發生后的事故處理,而精準治理強調的是危機發生前的預警處理,通過數據采集和監控的全程留痕治理,主動識別食品安全危險因素存在于哪個食品生產環節,記錄數據采集者行為,為責任監管提供最原始的數據,極大提高政府對突發事件的預知能力。
2.1.2.2 科學性 任何領域的管理過程都要避免治理主體的主觀因素對政策制定和生產過程產生過多的影響,但技術驅動的精準治理能夠保證食品安全管理的科學性,這是因為可以運用大數據建立食品安全生產信息庫、網絡治理等手段,依照科學的治理流程發揮科學的作用。由于我國地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各級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建設、體系、能力方面參差不齊,通過建立系統的信息庫可使治理過程統一化和標準化,增加決策的科學性,最大限度消除地區發展和治理主體間的差異性帶來的治理效果差距。
2.1.2.3 精準性 治理以精準為基本標志,基于對個體化數據的把握和適宜的分析方法,在大數據技術支撐下實現對食品生產相關信息的全面整合,在具備完整的信息庫后,管理者對數據進行挖掘分析,通過網絡分析等技術能夠保證食品安全管理決策和管理需求之間的精準匹配,尋求管理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及其與管理需求之間矛盾的解決方法。
2.2 精準治理的本質是食品安全管理范式的進化
在公共管理范式下,雖然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引入了“微博”“客戶端”等電子平臺,但仍然處于被動式治理模式。作為治理主體的政策制定者是理性的政治家,以食品安全相關部門為治理中介,施行相關政策。但在考核約束下,相關部門往往會考慮績效問題,有限信息的挖掘考慮到了食品安全問題,甚至瞞報。在精準治理范式下,公共部門作為治理政策的推理提供者和專業科學化信息的挖掘分析者,在治理過程中發揮智庫的作用。有作為的治理者主動分析政策需求,做出適宜的政策預案,治理的信息和政策互動通過知識網絡體現,而不是像公共管理那樣,將集中的政策需求和問題自下而上的通過治理中介反饋給治理主體。“精準治理”突破了傳統“食品安全管理”政治化的政府地位及管理主義的治理傾向,借助于數據化網絡的治理過程,記錄跟蹤食品安全治理過程的各個環節[26]。在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中,主要尋求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精準治理。
目前,我國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建設與評價機制采用的是以效率和結果為導向的企業化管理模式,不僅會出現唯績效論等治理失誤,而且會由于權責模糊,無法實現對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中問題的分析和責任的追究。技術驅動下的“精準治理”全程可記錄、可還原再現,同時可借助知識源的網絡學習特性,實現治理能力建設的績效評價。“精準治理”跟蹤記錄了食品安全治理全部過程,通過記錄食品生產、流通各個環節和數據采集者行為以及編碼、儲存數據,系統自動分析威脅因素,實現危機前處理,進而實現了食品安全治理的預知性。
由于我國各地區和各級政府的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存在差距,而食品安全數據網絡平臺實現了智能科學化共享和治理最優策略集合,公共部門可從中選取與當地特點相符的治理方式,提高治理的有效性,以相對科學的治理方式解決政府治理能力建設差異化問題。“精準治理”通過挖掘食品安全治理數據網絡,找到相同類型的最佳治理實踐,致力于食品安全治理數據網絡平臺的建設,實現食品安全治理的科學性。
“精準治理”以精準為基本標識,依托于食品安全數據網絡的治理過程及適宜的科學分析,全程跟蹤記錄“從田間到餐桌”的各個節點,實現了食品安全治理的精準性。數據網絡不僅是食品安全治理的源頭,也是治理績效的歸宿,食品安全治理全過程都作為食品安全數據網絡的一部分被記錄下來,進而實現精準化分析、精準化治理、精準化決策[27]。
3 實施食品安全精準治理中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3.1 制度價值觀重塑問題
近年來,加入“治理”熱潮以及鼓吹范式轉換的人無非是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推動政府角色的改變,但是大多數支持民主治理的學者傾向于否認或者貶低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主張推行治理必須削弱政府的職能。在以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為價值觀的西方公共管理過程中,政府決策也常常被詬病。“精準治理”的提倡和實踐引發我國政府部門對行政方式的思考,食品安全精準治理并非必須政府部門的絕對放權,往往是與政府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的局面。在“精準治理”范式下,食品安全管理部門基于對分散化信息的收集整合和歷史知識的挖掘分析,對治理需求進行把握判斷,在政策選擇過程中規避主觀判斷,將科學技術滲透到整個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中,而不是通過管理者主觀意識進行民主決策。
3.2 政府的權利邊界問題
精準治理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食品安全管理者的主觀行為,但在決策過程中,仍會出現選擇何種政策,以什么樣的力度施行政策,政策實施廣度如何等問題,并且還存在管理者仍可以數據信息不完善、突發因素過多等為由推翻決策的情形。基于精準治理的機制,大數據挖掘和知識推理技術的發展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上述情況的存在。但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施行將會引發人們對數據倫理的思考,包括民眾的需求在主觀上是不是愿意公開,對食品安全生產危機發生前的預警處理對于企業來說會不會是過度治理,對信息的采集應該止于何種程度和管理者如何使用分析結果等。信息安全、數據分析、資源共享等一系列問題值得人們對政府權利邊界的界定進行思考。
3.3 新舊體制的有效融合問題
我國管理進入深度轉型階段,在其他領域的治理實踐中已取得一定的實踐成果。相對而言,在食品領域,與“精準治理”相結合的實踐經驗較少。但在轉型過程中,一個新的管理模式的出現必然會解決新的問題以及產生新的問題,也可能伴隨舊問題的重新產生。雖然精準治理打破了過去“碎片化”的常規監管,最大限度解決差異化治理的問題,但食品安全精準治理能否和我國食品安全管理舊體制有效結合,現行的相關法律能否進行較全面的制約,企業是否能夠接受新興技術帶來的監管機制也是食品安全管理范式轉換期間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4 推進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主要策略
4.1 厘定政府職能,促進跨部門協同治理
通過厘定政府職能,細化行政環節,優化治理流程,以食品安全治理協調委員會打破部門間的獨立治理局面,促進各環節銜接有序,解決跨部門、跨地區的協調問題,使政府職權在每個政府行政流程中實現科學、高效、低成本運行,滿足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治理的合理期待。
首先,厘定政府食品安全職能是推進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關鍵過程,尤其要強化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過程中的監管職能、引導職能以及協調職能。此外,還需按照縱向統一合理配置和橫向分工合作的需求,對政府的職能進行進一步的梳理和理順,只有把政府、社會、市場的職能劃分清楚,細化分工,食品安全精準治理才會取得較快的成效。與政府職能厘定相平衡,還要科學配備和調配優化政府職權和政府資源,實現職能與治理結構的合理銜接,是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核心。對職權進行科學配備、協調優化,包括對行政資源、成本和人員等有形資源以及制度、公信力和權力等無形資源的配置。
其次,食品安全治理中的跨部門協調已成為精準治理理論與現實實踐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雖處于一體化監管時期,但各部門間缺乏協調,跨部門、跨地區的協調問題仍然無法解決。環境污染、農業生產與食品安全相互影響,而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涉及農業、國土、環保等多個管理部門,分段式監管和部門職責交叉造成協調成本高、協調時間長及相互推諉等問題。為此,有必要以國務院為名義在國家層面建立跨部門、跨地區的食品安全治理協調委員會,定期召開相關會議,協調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有效推進部門協商、溝通與合作。在地方層面上,可設立省級、市級食品安全協調委員會,構建綜合決策以及跨部門協調的協同機制,強化統一監管,協調職能。此外,考慮到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實踐困難和政治體制約束,需進一步確立食品安全治理協調委員會的權威。
4.2 優化政策議程,規引核心行動者
核心行動者是指在食品安全治理過程中具有根本決定權和主導話語權的被正式制度納入權力體系的核心成員,是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支配力量。一般而言,政府核心行動者大多對食品安全治理缺乏動力,而視可見的經濟績效、可預期的政績收益、可感知的體制壓力等效用目標優于食品安全目標。因此,優化政策議程,規引核心行動者是推進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核心。
首先,通過協商民主優化政策來規制政府核心行動者。隨著不同利益主體的逐漸分化,人們對食品的訴求產生了差異,從經濟層面出發,大多傾向于從經濟利益的角度關注生產收益;從政治層面出發,大多傾向于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收益;從普通公民的層面出發,大多傾向于健康安全、品質保證和幸福感。多主體的各方利益很難達成一致甚至產生沖突,是一個互相博弈的過程。因此,需要一個像協商民主這種既能夠包容利益分歧,又能分解利益矛盾的制度設計。提出各種相關理由,在充分考慮公共利益基礎上,公開審議協商,從而賦予決策實現政策合理性,做出一元主體更為科學化、民主化的政策建議,以達到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目的。
其次,建立有效的激勵問責機制。這是推進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發展的催化劑,對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核心行動者實施激勵機制和進行有效的行為偏差規引,是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前提。建立激勵約束時最重要的是將諸如法律法規等文本性規范的正式制度變成現實中可評估、可實踐、可細化的實踐機制,不斷以意識形態教化對政府核心行動者進行思想熏陶。此外,可采取差異化的績效考核辦法制定食品安全治理路徑與對策,促使各地區核心行動者因地制宜,提升對核心行動者激勵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最后,以制度化的問責機制約束政府核心行動者。以保障食品安全為目標,問責對象為各級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核心行動者),對其所承擔的職責和行政情況進行監督考核。依據法定程序對問責對象的不作為、慢作為和亂作為開展責任追究制度。食品安全責任問責的目的不僅在于讓政府官員為其失職和瀆職行為接受責罰,更重要的是建立激勵約束機制,對于轉變政府官員的政績觀,推動政府官員進行食品安全精準治理具有極大的激勵約束作用。
4.3 構建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體系,推進食品安全精準治理
食品安全社會共治強調多元主體的參與,在解決市場失靈的同時,有效克服政府單一監管的缺陷。其形成包括2個方面:(1)由單一主體變多元主體,動員更加廣泛的社會力量,如非政府組織、企業、消費者等共同參與到食品安全治理中,打破政府單一監管的狀況;(2)從監管方式變為治理方式,構建自下而上主動協調的運作機制,改變被動的監管方式。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理念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中得到了確立,社會共治注重政府與非政府部門間的聯系,強調多主體間在法治或政策框架內各司其職又相互合作,是我國食品安全精準治理不斷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結果。
首先,應賦予非政府部門更大的自由權。非政府組織與群眾的聯系更加緊密,較政府而言更能發現食品政策問題以及通過低成本構建合理有效的機制,進而能夠有效應對食品安全問題,從而實現從預防到反饋的治理過程。通過由上而下的賦權和信息共享,催生民主政治,促進社會共治模式的發展。吸納不同參與主體,將多元化訴求引入規范化表達通路中,可嘗試通過合同承包、政府補助等方式,將食品安全治理任務委托授權給志愿者組織或私營部門,充分發揮私營部門的趨利性和志愿者組織的公益性。通過共享食品安全治理權力,來形成無縫覆蓋的食品安全治理網絡。
其次,形成有效的食品安全社會共治動力機制,激活社會多元主體在食品安全精準治理中的積極力量。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實施離不開特定的動力機制,政府、社會組織、第3方檢測機構專家、企業、消費者等共治主體獨立且相互制約和影響,產生競爭關系;同時,多方主體間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而進行合作與協調形成了合作關系。社會共治的價值取向是各主體間合理的利益關系,這也是保證多方治理主體間良性競爭和合作的基礎。因此,要形成有效的食品安全社會共治動力機制,關鍵在于充分發揮多方治理主體的積極作用,通過各種方式將各方利益中的“對立關系”調整為社會共治的“雙贏關系”。
歸納而言,精準治理力求跳出食品安全傳統管理范式,拓寬食品安全管理的視野和深度。根據我國管理體制變革歷程及現狀探討傳統食品安全管理的局限性,探索一個新的食品安全管理范式,積極推進食品安全精準治理的策略,可持續推動我國食品安全工作從傳統向現代治理轉型。
參考文獻:
[1]陶光燦,譚 紅,宋宇峰,等. 基于大數據的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模式探索與實踐[J]. 食品科學,2018,39(9):272-279.
[2]凌俊杰,程 禹,梁 超. 國內外食品安全追溯及系統分析[J]. 食品工業,2013,34(5):186-190.
[3]周潔紅,武宗勵,李 凱. 食品質量安全監管的成就與展望[J]. 農業技術經濟,2018(2):4-14.
[4]牟少飛. 國內外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對比[J]. 世界農業,2013(12):73-77.
[5]劉 鵬,張蘇劍. 中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縱向權力配置研究[J].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54(1):28-34.
[6]薛 瀾,李希盛. 深化監管機構改革推進市場監管現代化——以杭州市為例[J]. 中國行政管理,2018(8):21-29.
[7]黃 強,陶 健. 國內外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對比分析與建議[J]. 經濟研究導刊,2012(16):97-98.
[8]衛學莉,寧玉嶺,李麗靜,等. 食品安全法律治理問題研究[J]. 中國衛生法制,2018,26(1):29-32,39.
[9]涂永前,馬海天. 食品安全法治研究展望:基于2009—2016年相關文獻的研究[J]. 法學雜志,2018,39(6):105-114.
[10]劉 鵬. 中國食品安全監管——基于體制變遷與績效評估的實證研究[J]. 公共管理學報,2010,7(2):63-78.
[11]周應恒,王二朋. 中國食品安全監管:一個總體框架[J]. 改革,2013(4):19-28.
[12]衛曉明,顧芙蓉. 基于遠程監控技術的食品安全監管平臺構建研究[J]. 上海食品藥品監管情報研究,2012(1):18-24.
[13]毛 婷,姜 潔,路 勇. “十三五”期間食品安全監管技術支撐體系研究重點領域建議[J]. 食品科學,2018,39(11):302-308.
[14]林衛華,吳志剛. 我國近年食品毒理學應用與研究進展[J]. 中國熱帶醫學,2014,14(8):1019-1022.
[15]薛 瀾,張 帆,武沐瑤.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研究:回顧與前瞻[J]. 公共管理學報,2015,12(3):1-12.
[16]Harlan C. The future executive:a guide for tomorrow's managers[M]. New York:Harper & Row,1972.
[17]Oliver E W.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1,61(2):112-123.
[18]Oliver E W. Markets and hierarchies:some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63(2):316-325.
[19]Snowden P N.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9:financial systems and develop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1,11(2):187-188.
[20]Landell-Mills P,Agarwala R,Please S. Sub-Saharan Africa: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a long-term perspective study[M]. 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1989.
[21]Boeninger 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issues and constraints[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1,5(S1):267-288.
[22]World Bank.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1[M]. 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1991.
[23]王紹光. 治理研究:正本清源[J]. 開放時代,2018(2):153-176.
[24]Bekkers V,Dijkstra G,Edwards A,et al. Governance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assessing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practices[M]. London:Ashgate Publishing,Ltd.,2007.
[25]李大宇,章昌平,許 鹿. 精準治理:中國場景下的政府治理范式轉換[J]. 公共管理學報,2017,14(1):1-13.
[26]許世衛,王東杰,李哲敏. 大數據推動農業現代化應用研究[J]. 中國農業科學,2015,48(17):3429-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