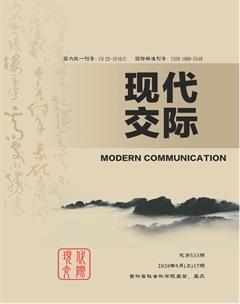《中蘇文化》與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接受(1936—1945)
魏秋菊
摘要:《中蘇文化》是抗戰(zhàn)時(shí)期由中蘇文化協(xié)會(huì)創(chuàng)辦的特殊刊物,旨在宣傳中蘇兩國(guó)文化,促進(jìn)兩國(guó)人文交流。無(wú)論在當(dāng)時(shí)還是現(xiàn)在,《中蘇文化》作為抗戰(zhàn)歷史和抗戰(zhàn)文化的重要載體,都有其獨(dú)特的地位和作用。以《中蘇文化》與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接受情況為切入點(diǎn),從不同角度反映1936—1945年期間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傳播的情況,對(duì)進(jìn)一步發(fā)掘中蘇文化、重新認(rèn)識(shí)抗戰(zhàn)文學(xué)史、解釋蘇聯(lián)電影的工具理性在中國(guó)的影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guān)鍵詞:《中蘇文化》 蘇聯(lián)電影 傳播 接受
中圖分類(lèi)號(hào):J90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9-5349(2020)17-0065-04
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外來(lái)電影的日漸涌入,使得中國(guó)本土電影發(fā)展不可避免地帶有舶來(lái)品電影的鮮明特征,中國(guó)電影受影響最大的要數(shù)好萊塢電影和蘇聯(lián)電影。兩種風(fēng)格迥異的電影在中國(guó)傳播,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特點(diǎn),《中蘇文化》作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文化和蘇聯(lián)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對(duì)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傳播情況有著較為全面、客觀和真實(shí)的記錄。重點(diǎn)回顧1936—1945年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如何傳播和接受,不僅有利于進(jìn)一步發(fā)掘中蘇文化,重新認(rèn)識(shí)抗戰(zhàn)文學(xué)史,而且《中蘇文化》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之一,以其為基本載體和主要線索來(lái)研究1936—1945年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接受情況,還有利于闡釋理解大眾傳媒與公共領(lǐng)域的建構(gòu)關(guān)系,豐富中國(guó)電影史的研究。
一、1936年前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接受
1.1936年以前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傳播概況
早在20世紀(jì)20年代初期,蘇聯(lián)電影就曾在哈爾濱上映,但“當(dāng)時(shí)觀看的人群只是中東鐵路職工,不具有商業(yè)性質(zhì),社會(huì)影響也相當(dāng)有限”[1]。1924年,蘇聯(lián)紀(jì)錄片《列寧的葬禮》開(kāi)始逐步在中國(guó)一些城市上映。1926年,在南國(guó)電影劇社的主持下,蘇聯(lián)蒙太奇學(xué)派的代表作品《戰(zhàn)艦波將金號(hào)》在中國(guó)非公開(kāi)放映。1931年,蘇聯(lián)電影《亞洲風(fēng)云》(原名:《成吉思汗的子孫》)在中國(guó)的傳播打破了非公開(kāi)放映的局面。
“九一八”事變后,蘇聯(lián)電影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guó),并在中國(guó)公開(kāi)放映,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30年代早期在中國(guó)放映的就有200余部[2]。“十四年抗戰(zhàn)期間,在重慶、桂林、貴陽(yáng)等地共計(jì)放映約七十余部蘇聯(lián)電影”[3],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艾克導(dǎo)演的作品《生路》。1933年2月16日,上海大戲院正式公映蘇聯(lián)有聲影片《生路》,1933年2月19日晚,魯迅與許廣平在國(guó)民黨特務(wù)的跟蹤下來(lái)到上海大戲院一同觀看了一部蘇聯(lián)電影《生路》。這是第一部在中國(guó)公映的蘇聯(lián)影片,激進(jìn)的電影評(píng)論家給予高度評(píng)價(jià),在他們看來(lái),這是“中國(guó)電影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生路》的上映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電影界的極大關(guān)注,此后,蘇聯(lián)的名片不斷地來(lái)到中國(guó),播放了《迎展計(jì)劃》(《重逢》)《金山》《傀偏》等影片。
2.蘇聯(lián)電影與美國(guó)電影在中國(guó)接受度比較
在蘇聯(lián)電影傳入中國(guó)之前,無(wú)論是普通的觀眾還是電影從業(yè)者看到的最多的還是美國(guó)電影,由于這樣的原因,美國(guó)影片在不知不覺(jué)中給中國(guó)觀眾戴上了一幅有色眼鏡。沈西苓在《關(guān)于蘇聯(lián)電影的雜志》中說(shuō)道,在蘇聯(lián)電影最初到上海放映的時(shí)候,常會(huì)聽(tīng)到這樣的話(huà):“硬線條,消化不下去,我是比較喜歡看美國(guó)電影的。” [4]另外,在《電影》周刊上有一篇題為《俄美兩國(guó)電影的比較》的文章,文中比較了蘇聯(lián)電影和美國(guó)電影的相異之處:“美國(guó)聲片和默片的愿望和觀念,是陳述一個(gè)故事,它以其前或現(xiàn)在的故事告訴我們。蘇俄聲片和默片是以將來(lái)應(yīng)當(dāng)怎樣或?qū)?lái)會(huì)怎樣為出發(fā)點(diǎn)的。美國(guó)的有聲片是一幅圖畫(huà)。蘇俄的有聲片是一張告白。美國(guó)的電影是一部羅曼史。蘇俄的電影是一篇詩(shī)、一首歌。美國(guó)的電影是講到實(shí)際和現(xiàn)在的,蘇聯(lián)電影是講到理想和未來(lái)的。從美國(guó)來(lái)的是熱,從蘇聯(lián)來(lái)的是光。”這樣有一種前瞻性、宣傳性,也有藝術(shù)性的電影類(lèi)型,恰好符合了當(dāng)時(shí)許多左翼電影人士對(duì)于電影的追求與祈望。據(jù)司徒慧敏回憶,當(dāng)時(shí)蘇聯(lián)影片在上海大戲院上映的時(shí)候,他和夏衍多次利用同這個(gè)戲院的管理人和另一個(gè)放映師的關(guān)系去看電影。等到放映結(jié)束后,再到放映間用倒片機(jī)一個(gè)個(gè)鏡頭,一段段把他們要學(xué)習(xí)的地方記錄下來(lái)。但是在這場(chǎng)看似風(fēng)風(fēng)火火的蘇聯(lián)電影進(jìn)京事件卻并沒(méi)有在普通觀眾中引起廣泛關(guān)注。
3.蘇聯(lián)電影與國(guó)產(chǎn)電影在中國(guó)接受度比較
在1936年以前中國(guó)的主要?jiǎng)?chuàng)作作品中,因大多受到好萊塢電影尤其是好萊塢類(lèi)型電影的影響,傾向于對(duì)好萊塢電影進(jìn)行適度地復(fù)制、模仿或改裝。雖然國(guó)產(chǎn)電影進(jìn)行復(fù)制、模仿沒(méi)有遇到太大的困難,但并不意味著就能順利播放。事實(shí)上,在大眾的接受上,還是以好萊塢電影為主,更不用說(shuō)蘇聯(lián)電影是否占據(jù)一席之地。鄭伯奇曾評(píng)論道:“中國(guó)的電影觀眾只是好萊塢的俘虜,中國(guó)的電影事業(yè)只是好萊塢的附庸。在以前,中國(guó)的電影市場(chǎng),完全為好萊塢的幾家公司所壟斷。德法英各國(guó)的影片想在京滬平津各大都市的影戲院中,求一個(gè)上演的機(jī)會(huì)都不容易。國(guó)產(chǎn)影片也只能在美國(guó)影片活動(dòng)的空隙中尋找一席可憐的生存的余地。國(guó)產(chǎn)影片的主要市場(chǎng)是大都市的第二輪影戲院、落后的農(nóng)村都市和南洋華僑而已。” [5]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guó)的影戲館以播放好萊塢電影為主,英德法各國(guó)的影片已經(jīng)很少,盲目模仿好萊塢電影的國(guó)產(chǎn)電影業(yè)只能在好萊塢電影放映的夾縫中求生存,而蘇聯(lián),其影片數(shù)量在中國(guó)市場(chǎng)上更是寥寥無(wú)幾。有關(guān)數(shù)據(jù)顯示,1935年3月下旬到9月底,中國(guó)從蘇聯(lián)引進(jìn)的影片數(shù)目是5部,而同時(shí)段引進(jìn)的美國(guó)片卻有179部,英國(guó)片15部。魯迅一生所看的152部影片中,蘇聯(lián)影片也只有9部。總的來(lái)說(shuō),雖然當(dāng)時(shí)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有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的傳播,但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普及情況并不樂(lè)觀。1936年5月,中蘇文化協(xié)會(huì)創(chuàng)辦了《中蘇文化》,作為促進(jìn)中蘇文化交流的重要刊物,《中蘇文化》較為集中地介紹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傳播情況。
二、《中蘇文化》與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接受
1.蘇聯(lián)電影的理論譯介
《中蘇文化》作為一本研究和宣傳中蘇文化的綜合性刊物,在中國(guó)抗戰(zhàn)時(shí)期的中國(guó)文化與蘇聯(lián)文化的交流中,充當(dāng)著橋梁和紐帶的重要作用。據(jù)《中蘇文化》記錄,中國(guó)電影藝術(shù)的理論幾乎全部源自蘇聯(lián)電影。本來(lái)電影是最年輕而又最復(fù)雜的藝術(shù),德國(guó)的電影藝術(shù)家以前雖有一些理論的著作發(fā)表,大都是片段的。只有蘇聯(lián)的十月革命,真正解放了資本家對(duì)于電影的束縛,建立了系統(tǒng)的電影研究,出版了專(zhuān)門(mén)的電影理論著作。蘇聯(lián)的這種自電影藝術(shù)的科學(xué)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電影工作者的注意,中國(guó)電影工作者當(dāng)然也不例外。1932年,中國(guó)出版了普特符金的名著《電影導(dǎo)演論,電影腳本論》,這是中國(guó)電影藝術(shù)理論的第一譯著,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正在開(kāi)始轉(zhuǎn)變的中國(guó)電影界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洪深氏這樣評(píng)論:“在這劇本恐慌的時(shí)候,看到蘇聯(lián)最優(yōu)秀,最偉大的導(dǎo)演者普特符金的關(guān)于電影的著作不同,這不是桌子上的空泛的理論,而是一個(gè)日夜的考慮著每一方膠片,研究每一個(gè)攝影機(jī)角度,而熱烈地企圖在銀幕上把握真實(shí)的實(shí)踐者的體驗(yàn)。在這兒誠(chéng)懇地介紹了關(guān)于劇本創(chuàng)作的基礎(chǔ)的方法的原則的知識(shí)。我深信在這國(guó)產(chǎn)影片復(fù)興氣運(yùn)中的電影界,一定會(huì)有很大的貢獻(xiàn)的。”此后,蘇聯(lián)電影藝術(shù)理論的著作,陸續(xù)被介紹到中國(guó)來(lái),中國(guó)的電影工作者從這些譯著中得到了理論上的武器,而電影批評(píng)者由此獲得了批評(píng)的尺度。
2.蘇聯(lián)電影的社會(huì)評(píng)論
《中蘇文化》中詳細(xì)記錄了當(dāng)時(shí)一些著名的電影工作者對(duì)于蘇聯(lián)電影的評(píng)價(jià),這些評(píng)價(jià)從不同的視角反映了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社會(huì)對(duì)于蘇聯(lián)電影的基本態(tài)度。如葛一虹提到,“九一八事變?cè)谝欢ǔ潭壬细淖兞酥袊?guó)的社會(huì)格局,中國(guó)電影也迎來(lái)徹底轉(zhuǎn)變的時(shí)機(jī),開(kāi)始逐步擺脫美國(guó)好萊塢電影的控制和支配,轉(zhuǎn)而向蘇聯(lián)電影的內(nèi)容和方法學(xué)習(xí)。”[6]何非光在《蘇聯(lián)電影給我的印象》中談到,蘇聯(lián)電影,“與美國(guó)好萊塢電影之類(lèi)的資本主義電影不同,它不反映低級(jí)的生活行為和表現(xiàn)低級(jí)情緒,而是為了開(kāi)啟一種新的生活,建立必勝的信念,加強(qiáng)堅(jiān)毅的精神,培養(yǎng)革命的熱情,最終實(shí)現(xiàn)遠(yuǎn)大的人類(lèi)社會(huì)理想”[7]。史東山在《抗戰(zhàn)以來(lái)的中國(guó)電影》中談道:“蘇聯(lián)抗戰(zhàn)電影具有鼓舞人心的強(qiáng)大力量,表現(xiàn)在對(duì)傷兵和民眾的深刻影響,很多傷兵看了影片,受到激勵(lì),會(huì)毫不猶豫請(qǐng)求馬上回到戰(zhàn)場(chǎng),而部分民眾看了蘇聯(lián)抗戰(zhàn)電影,為軍隊(duì)的英勇和熱誠(chéng)所感染,會(huì)主動(dòng)請(qǐng)求參戰(zhàn)”[8]。歸納起來(lái),當(dāng)時(shí)的電影工作者大都對(duì)蘇聯(lián)電影持肯定態(tài)度,認(rèn)可蘇聯(lián)電影具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色彩和強(qiáng)大的宣傳教育意義。
3.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放映情況
列寧說(shuō):“當(dāng)群眾握有了電影,當(dāng)電影是在真正從事社會(huì)主義文化的人們手中,它就成了教育群眾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1933年,《生路》在上海放映,《生路》的上映為中國(guó)電影界應(yīng)該指明了一條全新的發(fā)展道路,促進(jìn)了中國(guó)電影的轉(zhuǎn)型,那就是革命藝術(shù)并不需要夸張。同年中國(guó)還放映了蘇聯(lián)電影《重逢》,雖然片子剪得太厲害了,太支離破碎,對(duì)于在中國(guó)觀眾面前剛獲得好感的蘇聯(lián)電影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但是中國(guó)觀眾和電影工作者用自己的想象去補(bǔ)充視覺(jué),用理論去把握技術(shù),這樣不僅觀眾得到了滿(mǎn)足,電影工作者也發(fā)現(xiàn)了這個(gè)片子在技術(shù)上的特點(diǎn)。
此后,質(zhì)量上乘、內(nèi)容豐富的蘇聯(lián)電影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guó)的城市乃至鄉(xiāng)村,如《我們來(lái)自克隆斯達(dá)》《夏伯陽(yáng)》等作品,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中國(guó)面臨的社會(huì)形勢(shì)愈加艱難和復(fù)雜,中國(guó)人民逐漸不再喜歡“眼睛吃冰激凌”,極具現(xiàn)實(shí)意義和教育意義的蘇聯(lián)電影便自然而然開(kāi)始取代美國(guó)好萊塢電影。據(jù)資料記載,1938年全國(guó)蘇聯(lián)影片放映1150余場(chǎng),觀眾440600余人;1939年1月至7月放映蘇聯(lián)電影1000余場(chǎng),觀眾超過(guò)43萬(wàn),觀看蘇聯(lián)電影的觀眾在最多的時(shí)候接近50萬(wàn)(各機(jī)關(guān)團(tuán)體鄉(xiāng)村及戰(zhàn)區(qū)放映未計(jì)算在內(nèi))。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shí)期,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放映的次數(shù)之多,傳播速度之快,受眾群體之廣。
三、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接受和變異的原因
1.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接受的原因
《中蘇文化》雜志在1940年10月10日出了抗戰(zhàn)特刊,據(jù)《中蘇文化》相關(guān)內(nèi)容記載,蘇聯(lián)電影的工具理性之于中國(guó)“抗戰(zhàn)電影”的影響和意義,不僅在于為編創(chuàng)“新中國(guó)”電影提供了基本原則和一般思路,而且還為中國(guó)“抗戰(zhàn)電影”提供了“民主自由的新中國(guó)”的最佳學(xué)習(xí)版本。自從中蘇復(fù)交之后,蘇聯(lián)的影片可以在中國(guó)公映了,這不僅為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guó)人民增添一種比較新穎的完整的娛樂(lè)方式,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guó)電影的發(fā)展方向。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逐步普及,使得中國(guó)觀眾不再是好萊塢電影的俘虜。同時(shí),對(duì)于落后的中國(guó)電影,因?yàn)槭艿教K聯(lián)電影的熏陶,中國(guó)觀眾也發(fā)出要求進(jìn)步的呼聲,促進(jìn)了中國(guó)電影的轉(zhuǎn)變。葛一虹提到,“中國(guó)電影在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上也漸漸地脫離了歐美電影的模仿與支配,而傾向于相同于蘇聯(lián)電影影響的。”[6]
那時(shí)大多數(shù)在電影節(jié)上的進(jìn)步的從業(yè)員,都在以無(wú)窮的興趣,對(duì)蘇聯(lián)電影加以熱烈研討。蘇聯(lián)《生路》初來(lái)中國(guó),憑借自身獨(dú)特而新穎的作風(fēng),迅速在中國(guó)傳播,在中國(guó)電影界激起了熱烈的討論,許多電影工作者都會(huì)對(duì)這部電影進(jìn)行研究,至《生路》傳播至中國(guó)以后,任何一部蘇聯(lián)電影進(jìn)入中國(guó),在中國(guó)放映,中國(guó)電影工作者都會(huì)以謹(jǐn)慎的態(tài)度和科學(xué)的方式加以客觀的解讀和研討。于是在電影批判上,“蘇聯(lián)鏡頭”“蘇聯(lián)手法”“蘇聯(lián)作風(fēng)”“蘇聯(lián)演技”等理念和手法便開(kāi)始逐步流行。在多次的學(xué)習(xí)之后,左翼電影人也開(kāi)始有意識(shí)地去嘗試在自己的作品中實(shí)踐從蘇聯(lián)影片中學(xué)到的技巧。被認(rèn)為是代表左翼電影經(jīng)典之作的《狂流》和《上海二十四小時(shí)》,其實(shí)正是左翼電影人“在戰(zhàn)斗中學(xué)習(xí)戰(zhàn)斗”的結(jié)晶。尤其是其中對(duì)于仰角鏡頭以及蒙太奇的敘事手法之“拿來(lái)主義”式的運(yùn)用,恰到好處地與中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產(chǎn)生了奇妙的結(jié)合,進(jìn)而詮釋了左翼電影所宣揚(yáng)的階級(jí)對(duì)立的主題。中國(guó)電影藝術(shù)家從蘇聯(lián)電影中學(xué)到了不同于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全新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和方法。自從跟蘇聯(lián)影片接觸以后,同時(shí)也受了中國(guó)的新興的文化運(yùn)動(dòng)深入的影響,有覺(jué)悟的中國(guó)電影藝術(shù)家逐步開(kāi)始正視現(xiàn)實(shí)發(fā)展情況。而創(chuàng)作方法也大多趨向于蘇聯(lián)電影所采取的那種新的寫(xiě)實(shí)主義,即使有浪漫主義的傾向,也都走向革命的道路。
蘇聯(lián)電影之所以能在中國(guó)傳播,從根本上看,是由于蘇聯(lián)電影的性質(zhì)和功能符合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的需要。蘇聯(lián)電影作為“政治電影”,與抗戰(zhàn)前的“商業(yè)電影”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表現(xiàn)在其具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代國(guó)家民族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特征,彰顯出鮮明的工具理性色彩。蘇聯(lián)電影“沒(méi)有專(zhuān)為娛樂(lè)人設(shè)的大腿裸胸,所謂香艷肉感的電影。差不多每一個(gè)騙子都有充分的教育意義,被運(yùn)用著用以教育千千萬(wàn)萬(wàn)蘇聯(lián)大眾,告訴他們當(dāng)前的苦難在哪兒,應(yīng)該怎樣去克服這困難。”[9]常任俠在《我觀蘇聯(lián)戲劇電影》中提到“蘇聯(lián)電影和同蘇聯(lián)戲劇的相同之處在于,都表現(xiàn)了新的內(nèi)容,傳遞了新的精神,都具有大眾教育的工具意義。在蘇聯(lián),一種全新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正在萌發(fā)和醞釀,人民在接受著新思想的洗禮和改造,而電影與戲劇,作為上層建筑的表現(xiàn)形式,負(fù)有這種為新生社會(huì)關(guān)系營(yíng)造文化氛圍的重要使命。尤其是電影者,具有強(qiáng)有力的傳播效應(yīng),不僅在蘇聯(lián),無(wú)論世界上任何一個(gè)角落,凡是接受真理與光明的,都能借此迎著新社會(huì)中所表現(xiàn)的可愛(ài)的光輝。就像電影觀眾雖然沒(méi)有親自走到蘇聯(lián)國(guó)土,但是也常常能從屏幕上蘇聯(lián)電影所呈現(xiàn)的內(nèi)容感知人類(lèi)社會(huì)前進(jìn)的步伐和進(jìn)程”[10]。
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guó)社會(huì)面對(duì)內(nèi)外交迫的窘境,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元素,根植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服務(wù)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基于此,中國(guó)電影發(fā)展必須服務(wù)于戰(zhàn)爭(zhēng)需要。抗戰(zhàn)以來(lái),大家對(duì)電影的胃口也變了些,似乎已漸漸感到不只是可以做“眼睛冰激凌”,除“大腿”“歌喉”之外,尚有無(wú)數(shù)的事物可供學(xué)取,因之要求就格外高了。陽(yáng)翰笙的《我對(duì)于蘇聯(lián)戲劇電影之觀感》中談到“從九一八以來(lái),當(dāng)日本帝國(guó)主義肆無(wú)忌憚對(duì)我國(guó)領(lǐng)土開(kāi)始實(shí)施野蠻侵略的時(shí)候,中國(guó)戲劇電影藝術(shù)上的工作者,在這次空前的血火洗禮的刺激中,大都毅然地站立起來(lái)了……電影工作者呢,過(guò)去有許多本來(lái)是受好萊塢的影響很深的,也開(kāi)始了中國(guó)電影藝術(shù)上的劃時(shí)代的轉(zhuǎn)變,很熱烈的來(lái)為抗日斗爭(zhēng)服務(wù)了。”[11]客觀的需要使長(zhǎng)期停滯的中國(guó)的電影不得不發(fā)生所謂“轉(zhuǎn)變”,在轉(zhuǎn)變過(guò)程中,吸收借鑒最多的就是蘇聯(lián)的影片。蘇聯(lián)電影的題材都是現(xiàn)實(shí)的,毫無(wú)掩飾地暴露現(xiàn)實(shí)的一切,但在這現(xiàn)實(shí)主題的后面有他們最崇高的理想。也就是說(shuō),社會(huì)形勢(shì)的巨變迫使對(duì)我國(guó)的電影事業(yè)轉(zhuǎn)型,社會(huì)不再需要好萊塢那樣的理想主義和浪漫色彩,而需要真實(shí)地展現(xiàn)中國(guó)社會(huì),中國(guó)人民對(duì)電影所要求的也不再只是娛樂(lè),更重要的是精神食糧。蘇聯(lián)電影作為具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教育意義的“政治電影”,其對(duì)革命戰(zhàn)場(chǎng)真實(shí)事件和鮮活人物的再現(xiàn)與中國(guó)抗戰(zhàn)的需要契合度相當(dāng)高,能夠滿(mǎn)足中國(guó)觀眾的精神需要,這就使得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有了廣闊的市場(chǎng)。
此外,蘇聯(lián)電影能在中國(guó)得到廣泛傳播的原因之一還在于蘇聯(lián)電影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有借鑒東方的曲調(diào),和中國(guó)電影有相似的成分,比如,舊俄的作曲家許多人都用過(guò)東方的曲調(diào)作他們樂(lè)曲的主題,在蘇聯(lián)的電影音樂(lè)中也時(shí)常可以聽(tīng)到用各種木管樂(lè)器奏著悠長(zhǎng)的東方趣味的音樂(lè)。這些方面使從事電影音樂(lè)工作的中國(guó)人得到了深刻的啟示。
2.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變異的原因
蘇聯(lián)電影作為外來(lái)電影,中國(guó)電影對(duì)學(xué)習(xí)蘇聯(lián)電影的學(xué)習(xí),并不是全部吸收,而是有所取舍,正如夏衍所說(shuō):“那時(shí)候的中國(guó)電影,簡(jiǎn)單地講,理論上學(xué)蘇聯(lián),技術(shù)上學(xué)美國(guó)。”中國(guó)電影的發(fā)展借鑒了蘇聯(lián)電影的理論,但在表現(xiàn)技巧上已經(jīng)形成了一條屬于自己的敘事體系。也就是說(shuō),在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沒(méi)有被全部吸收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到好萊塢電影的影響。
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注重和諧共生,而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作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構(gòu)成,不可避免地?cái)y帶有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元素,具體表現(xià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十分講究意蘊(yùn)和情調(diào),強(qiáng)調(diào)整體布局和氛圍營(yíng)造。受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思想的影響,中國(guó)電影講求敘事的邏輯性,強(qiáng)調(diào)時(shí)間和空間的統(tǒng)一,經(jīng)常使用連續(xù)的長(zhǎng)鏡頭來(lái)表現(xiàn)人物和呈現(xiàn)內(nèi)容;而以愛(ài)森斯坦為代表的蘇聯(lián)電影學(xué)家則善于運(yùn)用割裂時(shí)空的創(chuàng)作手法,這與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思想不符合,因此,當(dāng)年的中國(guó)電影工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shí),對(duì)愛(ài)森斯坦的作品和理論吸納較少,更多的是借鑒了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論。
中國(guó)電影在吸收蘇聯(lián)電影的過(guò)程中,不僅受到了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了美國(guó)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因此,中國(guó)電影對(duì)蘇聯(lián)電影的學(xué)習(xí)也不可避免地融合了美國(guó)電影的元素。從歷史上看,好萊塢電影對(duì)中國(guó)電影的影響不僅由來(lái)已久,而且十分深刻。好萊塢電影的創(chuàng)作手法雖然善用長(zhǎng)鏡頭,但內(nèi)容上逃避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矛盾;蘇聯(lián)電影的內(nèi)容雖然擅長(zhǎng)表現(xiàn)矛盾,但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比較喜歡用短小而零碎的鏡頭。因此中國(guó)電影人在接受蘇聯(lián)的蒙太奇理論時(shí),糅合了美國(guó)電影和蘇聯(lián)電影的表現(xiàn)形式,一方面,刻意用連續(xù)不斷的長(zhǎng)鏡頭去表現(xiàn)社會(huì)矛盾,另一方面,創(chuàng)作技巧上注重應(yīng)用敘事蒙太奇技巧,最出名的例子就是格里菲斯《黨同伐異》四個(gè)情節(jié)的同時(shí)敘述和《一江春水向東流》通過(guò)四個(gè)情節(jié)線平行敘述,展開(kāi)情節(jié),同時(shí)在語(yǔ)言上也很注意平行蒙太奇運(yùn)用,而且注意不同空間的共時(shí)性。
四、結(jié)語(yǔ)
《中蘇文化》作為一本研究和宣傳中蘇文化的綜合性刊物,在中國(guó)抗戰(zhàn)時(shí)期的文化與蘇聯(lián)文化的交流中,確實(shí)是一塊不可多得的陣地。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傳播是蘇聯(lián)電影和中國(guó)電影雙方內(nèi)在互動(dòng)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既涉及傳播者,又涉及接收者。本文以《中蘇文化》為主要載體,著重研究1936—1945年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傳播,具體從1936年之前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接受、《中蘇文化》與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理論傳播、《中蘇文化》與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實(shí)踐傳播和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接受和變異四個(gè)方面闡述了《中蘇文化》與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的接受情況,既具有時(shí)間上的連貫性,內(nèi)容上的系統(tǒng)性,又具有理論層面和現(xiàn)實(shí)層面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科學(xué)性和合理性。
參考文獻(xiàn):
[1]程季華.中國(guó)電影發(fā)展史:第1卷[M].北京:中國(guó)電影出版社,1963.
[2]蘇聯(lián)影片在我國(guó)放映受到觀眾熱烈歡迎已被當(dāng)作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重要工具[N].人民日?qǐng)?bào),1950-03-09(3).
[3]姜椿芳.蘇聯(lián)電影在中國(guó)[J].電影藝術(shù),1959(5);轉(zhuǎn)引自路曉會(huì).俄蘇文藝傳播與近代中國(guó)社會(huì)[J].株洲師范高等專(zhuān)科學(xué)校學(xué)報(bào),2006(4). ? ? ? ? ? ? ? ? ? ? ? ? ? ? ? ? ? ? (下轉(zhuǎn)第25頁(yè))(上接第68頁(yè))
[4]沈西苓.蘇聯(lián)電影給我的印象[J].中蘇文化,1940(7):4.
[5]鄭伯奇.蘇聯(lián)電影給予中國(guó)電影的影響[J].中蘇文化,1940(7):4.
[6]葛一虹.蘇聯(lián)電影與蘇聯(lián)戲劇給予了我們以什么?[J].中蘇文化,1940(7):4.
[7]何非光.葛一虹[J].中蘇文化,1940(7):4.
[8]史東山.抗戰(zhàn)以來(lái)的中國(guó)電影[J].中蘇文化,1941(9):1.
[9]司馬森.我對(duì)蘇聯(lián)電影的觀感[J].中蘇文化,1940(7):4.
[10]常任俠.我對(duì)蘇聯(lián)電影的觀感[J].中蘇文化,1940(7):4.
[11]陽(yáng)翰笙.我對(duì)于蘇聯(lián)戲劇電影之觀感[J].中蘇文化,1940(7):4.
責(zé)任編輯:趙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