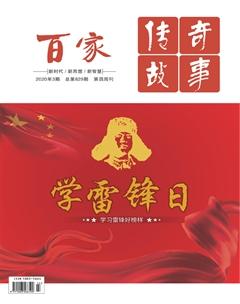論儒家生態觀的三階段
郭佳明
摘要:儒家在對天地萬物的探索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生態觀,這種生態觀是系統的且不斷發展的,起始于敬畏之心,最終發展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生態觀的發展過程是人對自身地位以及對自然萬物的認識過程,是人發揮主觀能動性將強制遵守自然規律變為自覺自律的過程,是為了將生產上升到治國層面乃至道德層面的過程。儒家的生態觀主要經歷了敬畏自然、認識利用自然規律、與自然“合一”三階段。研究儒家生態觀,對于當今儒家思想研究與生態治理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儒家;生態觀;人與自然
一、人敬畏自然階段
中國古代本無“自然生態”這一說法,但“天”“地”二字通常用來表示自然生態的含義。儒家在對天、地的討論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生態觀。
儒家對天地萬物的探索,始終是圍繞人與天的關系展開的。對于自然萬物持敬畏的態度是人探索自然的初始階段,這種敬畏之心具體表現在對天地之力的敬畏。
何為“天地之力”?天地之力是一種無形且存在的力量。“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孔子認為他一切的努力,最后的成敗都是由天所決定。天、地被看作是一種帶有決定性力量的存在,人類的活動要取得成功,必須要有這種力量的配合。認識這種力量是儒家對于自身活動規范的開始,儒家更將認識這種力量,即“知天”,視為成為君子的條件之一,并致力于自身的精神修養過程中。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他認為四十歲的時候就可以達到不惑的境界,這種境界是知識層面的不惑,而到達了五十歲之后的境界,是超越知識層面到達知天命的境界。知天命的境界是孔子對于天認識的開始,認為天是超越現有道德價值的,是超越道德價值的存在,是更高層次的智慧。對天地之力無形且存在的認識是儒家對于自然的初步認識,是敬畏之心產生的始點。
“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這是儒家對于天地之力的進一步認識,它不再是一種不可感知的存在,而是換一種方式反映在四時變化、自然萬物的生長、生成的過程中,是自然萬物得以生、得以成的依據。儒家對天地之力的探索方式,從盲目猜測轉到關注自然萬物的生長生成過程。這種轉變使得儒家更加具體地認識天地自然,同時也認識到了人在天地中的實踐活動。正如荀子所說的:“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謂之能參。”(《荀子·天論》)天、地、人成了宇宙中最為重要的存在。對天地之力認識的具體化,使得儒家對天地敬畏之心的認識從虛無縹緲的神秘想象轉化為對切實存在的自然萬物的敬畏。
二、人認識利用自然規律階段
對天地之力的敬畏之心是儒家參與天地問活動的思想準備,是人面對自然的第一步,是儒家生態觀的前提。當懷著敬畏之心探尋天地間的奧妙,自然就會衍生出對自然現象的總結,這些活動的經驗總結就是對自然規律的探索。儒家對于天是持敬畏的態度,因而對于其規律持不可違的態度,這種對自然規律的態度是不斷發展的。
人對于自然規律的認識是從天人分職開始明確規定的。荀子在闡釋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是以分工及職責來區分的。他認為天有天的職分,人有人的職責。“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荀子·天論》);“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荀子·天論》),天的運行規律是客觀且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人要做的不是去改造天地的運行規律,而是實行人道,即利用天地提供的條件創造自己的文化,這才是人的職分。這種順應自然規律的治理是對自然最基本的尊重,是人更好地生活在天地間的前提,是儒家生態觀的基礎。
儒家基于自然規律治理,將簡單地遵守自然規律上升到一國之君得以長治久安的前提。國家的長治久安需要人民的支持,“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人民得以安身立命的前提是有物質保障,這樣才能使得人民的幸福感提升,但物質保障是以遵守自然規律進行生產得來的。“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灣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只有不違時令,才能得到源源不斷的糧食、魚鱉、木材。這是一國百姓得以安邦的物質基礎,是君主更好地統治國家得到人民擁護的重要原因。儒家強調遵守自然規律進行實踐活動可以有源源不斷的資源的同時,“節用”也是儒家生態思想的重要觀念。為什么要“節用”?荀子認為:“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荀子·富國》),儒家已經認識到了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是無限的,當有限的自然資源滿足不了無限欲望的人時,就會引發爭亂。要更好地治理一個國家,需要做到節用,要對人的欲望進行限制。“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孔子認為治理好一個強大的國家不僅需要辦事認真謹慎,還要做到的就是節用,即利用好有限的資源使百姓安居樂業,從而達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國泰民安的理想狀態。
儒家對于自然規律的認識由治理國家進一步發展為道德的最高層面。仁義道德是儒學思想的核心,儒家生態觀的構建也是其“仁”學思想的體現。在儒家道德觀念中,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是諸多儒者一生所維護的,這種社會倫理秩序具體表現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認為人只有在道德與社會關系中才能更好地體現其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在對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維護中,儒家將道德的觀念與自然生態觀念相融合,賦予自然以道德的含義。孝觀念是儒家道德中一個重要觀念,對孝觀念在自然生態的解釋中,儒家認為“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將不按時節砍伐樹木、捕獵魚獸的行為視為不孝。用倫理道德秩序來規范人的行為,在生產生活中尊重自然,開采資源時要有節制按時令,否則就是在違背道德,這是需要受到譴責的,同時使人在與自然的實踐活動中形成自覺的約束力,是儒家自然生態觀的獨特之處。
三、人與自然“合一”階段
儒家所追求人與自然關系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合一并非指真正意義的合一,而是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境界。這種境界是建立在人尊重自然規律進行生產生活的前提下,將人與萬物視為一個整體的境界。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人活動于自然之中,自然也在用另一種方式給予人反饋。這是儒家對于自然的“人”性化探索。
(一)將自然賦予“人”的道德
儒家認為“宇宙在實質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則也就是宇宙的形而上學原則”,孟子所講的天,在道德上對人在與自然的實踐活動中起到的約束力,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種“同天”的境界。他認為,人如果能正確地認識理解這個道德的宇宙,即“知天”,就會成為宇宙的公民。孟子區分了“人爵”和“天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只有具備了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才能與人爵區別開來。將仁義忠信賦予自然,不斷地規范人自身的行為,將人放置在自然整體之中,才能“萬物皆備于我”,達到與天同一的境界。
(二)將自然賦予人性情的含義
董仲舒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人無論是在肉體還是在精神方面都是天的副本,因而是高于其他一切的。儒家認為,如果沒有了人,宇宙就是一個未成品,如果沒有了自然,人也就不復存在,人與自然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這就要求人與自然應處于和諧的常態,“中者,天下之始終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董仲舒認為,中和是天地萬物生成的原因,是天地的始點,只有遵循了宇宙規律的良性運行,萬物才能生生不息。
(三)將賦予自然萬物同人一樣的本質
儒家認為“人與萬物都處于氣化過程的某個環節,二者相互影響、彼此依賴、統一于一個生命共同體之中”,這是儒家對于宇宙生成的探索。張載認為,人與萬物的本質都是氣的凝聚,人與萬物的本性是一樣的,都是氣的本性,即天地之性,只是人后天所受的陰陽二氣的不同而各有差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西銘》),人生活在天地之間與自然萬物相同,天地為整體的父母孕育萬物。人與萬物都是同類,因而要愛一切人、一切物。儒家這種泛愛論的思想是將其置身于自然萬物之中,將萬物視為自己的手足,不需強制地約束保護自然,而應轉變為一種自覺行為,是人完整地與自然和諧相處而達到了“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