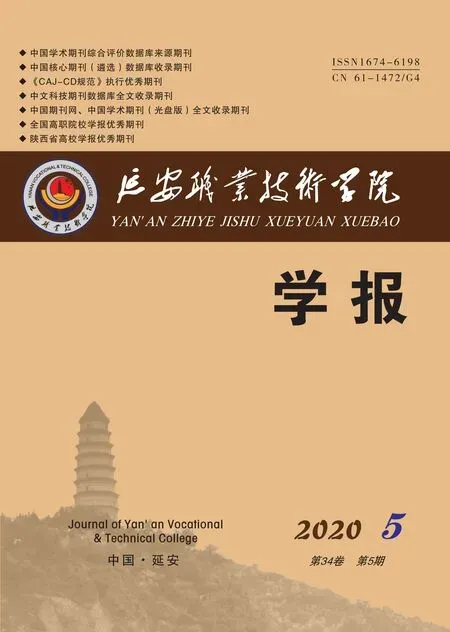徽州三雕戲曲圖像與動畫創作的跨媒介考察
陳雨微
(安徽師范大學,安徽 蕪湖241002)
回溯中國動畫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中國動畫擅長將中國傳統與場景構造結合在一起。動畫作為一種20世紀出現的新型藝術形式,已經成為新時代的一種獨具特色、極具傳染力的媒介表現形式,具有其特有的藝術特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它對其他媒介的兼容性。徽州三雕中戲曲的取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且不容忽視的表現形式。當徽州三雕、戲曲和動畫相結合時,就延伸了這三種媒介的研究領域。
一、跨媒介的學理認識
媒介是什么呢?張晶認為“藝術媒介是指藝術家在藝術創作中憑借特定的物質性材料,將內在的藝術構思外化為具有獨創性的藝術品的符號體系。”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道出了藝術媒介之間的區別:“史詩和悲劇、喜劇、酒神頌以及絕大多數雙管簫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摹仿。只是有三點差別,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用的方式不同。”龍迪勇在《空間敘事本質上是一種跨媒介敘事》中說到:“關于媒介,主要有‘管道論’和‘符號論’兩種定義,第一種定義可稱之為傳播媒介,第二種定義則可稱之為表達媒介。”這些看法表明,藝術所包含的門類采用的物質性材料都是不一樣的,但是這里的媒介并不僅僅代表物質性材料,它還代表著不同的方式,比如繪畫的圖像,文學的語言,音樂的聲音,舞蹈的形體等等。而作為“符號論”的媒介更加重要,也是我們跨媒介研究的重點。因為藝術只有創作出來才會有后續的傳播,研究。如果藝術創作一直處于構思環節,那這就不能稱作藝術,而只是大腦的幻覺。
那么何為跨媒介?萊辛的《拉奧孔》中雖然沒有提到媒介,但這是第一部對于不同媒介的藝術進行詳細論述的著作。“繪畫用空間中的形體和顏色而詩卻用在時間中發出的聲音……那么,在空間中并列的符號就只宜于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空間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時間中先后承續的符號也就只宜于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時間中先后承續的事物。”如果按照萊辛所說的來看待跨媒介,那么說明媒介之間存在著深深的隔閡。但是在20 世紀左右,隨著新的數字技術的發展,媒介的涵義變得更為廣闊,出現了廣播,電視等傳播媒介。這一趨勢催生了媒介方面的研究,麥克盧漢的《古登堡星云》:“這場革命(即信息運動的電子模式)讓我們無奈地陷入對模式和媒介的研究,視其為塑造和重塑我們感覺的各種形式。這才是我一直說的‘媒介即信息’的原意,因為媒介決定了感知模式以及確定目標的假設矩陣”。動畫就是各種媒介融合的產物,對于動畫的研究一直包含在數字媒介的研究之中,這也是媒介研究繞不開的一個領域。亨利·詹金斯的《融合文化》說:“跨媒介敘事表示這樣一個過程,即一個故事的各個有機組成部分穿越于多個媒介傳播渠道,系統構建出一種協作合一的娛樂體驗。在理想情況下,每一種媒介對于故事的展開具有自己獨特的貢獻”。
媒介研究的道路上出現了太多優秀的研究者,發展至今日,跨媒介在藝術研究中已經占據著前沿地位。對于跨媒介,周計武說:“作為一種藝術現象,它指的是某物在空間或時間上是居間的或介于兩個對象之間的。”跨媒介研究就是試圖利用媒介之間存在的可嵌入點,來打破媒介之間的固有屬性。按照傳統的觀念,藝術自身固有的媒介選擇,是它自身獨一無二的屬性,藝術自身的界定也是根據媒介的屬性來明確是何種藝術以及是不是藝術。跨媒介的產生使各種藝術突破了自身的界限,不同藝術開始跨越到別的領域用不同的媒介方式來進行展現;使觀眾開始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藝術,突破了對于藝術原有的媒介界定。拉奧孔就是一個跨媒介的作品,從文學到雕塑,突破了文學的表現形式,而以雕塑的形象存在于另一空間;觀者不僅可以想到文學中的拉奧孔,也可以看到雕塑所展現出的拉奧孔。
二、徽州三雕和動畫的跨媒介
中國動畫發展初期,就富有濃郁的民族特色,無論是萬氏兄弟所做的第一部長篇動畫電影《鐵扇公主》,還是其后的《豬八戒吃西瓜》《大鬧天宮》等。中國的傳統藝術輝煌燦爛,無論是工藝美術,壁畫,還是宗教等都是早期的動畫取材對象。《鐵扇公主》就是動起來的中國山水畫,并且結合了戲曲的特征,運用了木刻的線條刻畫,富含民族特色的人物形象。《動畫概論》說道:“《鐵扇公主》的歷史意義在于其開影院長篇之先河,非自覺地將動畫這一新穎的藝術形式與中國的民族風格相互融合,開啟了中國動畫民族化的探索之路,形成了民族化的動畫藝術語言。”而“探民族形式之風”道路指向卻是在1955年左右才確立的,當時為了貫徹這一提倡,勒夕導演了木偶片《神筆》以及特偉導演了《驕傲的將軍》,自此“中國學派”開始享譽中外。
就整個動畫史來看,徽州三雕和動畫的跨媒介一直存在,正如《鐵扇公主》使用的木刻手法。但是這種跨界大多數存在于背景,很少有專門的徽州三雕的其他方面的借鑒。徽州三雕到動畫的媒介跨界具體可以分為三種:一是靜態跨界到動態中的靜態,也就是徽州三雕成為動畫中的背景環境;二是靜態跨界為動態,也就是動畫采取徽州三雕中的故事主題,來進行擴展和延伸;三是動態轉變為靜態,也就是徽州三雕中出現的動畫作品以及技術應用。
第一種跨界,一直存在于動畫的發展歷程中。國產動畫普遍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記,構成元素中經常見到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的蹤跡,體現著中國獨有的人土風情,生活氣息。《嶗山道士》中三清觀的牌坊(圖1)。《中國唱詩班》的江南建筑等都是這種跨界的顯著代表,它們運用著中國古典建筑背景來映襯著動畫主題,描繪出一幅富含中國特色的山水畫卷。學術界對于徽州三雕和動畫場景借鑒的研究只有少量,如郜蕓的《徽派建筑元素在動畫場景設計中的運用研究》,朱米娜、吳林林的《徽雕藝術在動畫創作中的應用研究》等。但是這些先例和研究都讓動畫與徽州三雕風格建筑進行跨界添加了可能性,但是這需要兩個領域中的專業人士的共同努力和推動。最近,陜西科技大學制作的水墨動畫短片《徽州女人(圖2)》就是全篇以徽州特色為基調的動畫作品,無論是牌坊還是雕窗都呈現了徽州三雕的民居風格。
第二種跨界,一直暗藏在動畫之中。徽州三雕選材包括風俗故事,文學故事,戲曲、宗教神話等題材,這些題材一直是中國動畫創作者的最愛。如廣泛流傳的八仙故事、八仙形象、福祿壽喜、三國故事(圖3、4)等。《哪吒之魔童降世》是根據傳統神話故事進行改編的;《大圣歸來》是改編自孫悟空的神話故事。這些動畫里面出現的太乙真人、哪吒、龍王等形象是徽州三雕經常刻畫的形象。因為這些都是兩者共同采納的題材,有更廣為流傳的文學版本,所以這也就弱化了動畫中有關徽州三雕題材的借鑒,但是這也更能說明徽州三雕與動畫結合的可能性。《瓷娃娃》中就對雕塑偶進行了全新的嘗試,這也就說明動畫可以在徽州三雕方面進行大膽的嘗試,如可以創作有關徽州三雕起源的動畫。《徽州女人(圖1)》這部動畫生動描繪了一個徽州女人和徽商的愛情故事,徽州三雕題材和動畫效果相得映彰。

圖1:《嶗山道士》

圖2:《徽州女人》

圖3:三英戰盧布圖

圖4:程金達宅木雕.穆桂英掛帥
第三種跨界,是動畫與徽州三雕的物質性媒介的跨越。動畫和現實之間的跨界產生了一種動畫新模式——3D 動畫,3D 動畫使動畫形象更加立體。建筑動畫展示就是一種3D動畫衍生物。建筑動畫是指展示建筑以及建筑相關所產生的動畫影片,它通常使用電腦軟件來按照草圖進行模擬建模,所達到的效果能夠讓觀眾身臨其境,能夠在動畫影片中看到所需要的所有效果,角度,色彩以及各種變化。比如《圓明園》,這部影片用計算機技術活靈活現的展示了圓明園誕生、毀滅的過程。建筑動畫同樣可以使用到徽州三雕上面,這樣就能夠全方位看到徽州三雕的刻畫過程,成為記錄徽州三雕創作和觀看徽州三雕的一種很好的工具;同時可以作為展示資料,以做到對徽州三雕傳承的功能,使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得到更好的拓展。
3D打印是3D技術的一種展現形式。3D打印,又叫做“添加制造、積層制造”,是一種以數字模型文件為基礎,運用粉末狀金屬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過逐層打印的方式來構造物體的技術。目前我國的3D 打印技術在總體上來說還是與國外有著很大的差距,但是國內引入的較早,再加上近些年很多高校和企業開始鼓勵自主研發,這就導致3D打印技術快速發展。徽州三雕可以通過3D打印技術實現更快速的創造。如:在徽州三雕制作中總需要勾勒草圖,當這個草圖和3D打印技術結合的時候,就能夠給人更加立體的呈現,讓工匠在草圖過程就能夠看到所展現題材的動態立體效果;制作出“草圖”后,根據所需要的效果進行打光,調鏡頭;最后就可以將所需要的物體打印出來。這個技術的應用會提高徽州三雕制作的效率與效果。沈潔的《徽州古建筑復原動畫的現狀研究》中就涉及這個領域。中國動畫喜歡根據傳統故事來進行創作,但是當動畫在設計過程中的時候會對故事形象進行改設,改設過后的角色形象就產生了眾多的衍生品,比如木雕,竹雕,石雕等所形成的的動畫角色形象。徽州三雕就可以提供圖紙通過計算機技術進行建模創造,形成類似手辦的存在,或者形成樣板圖。論者就曾在黃山雕塑博物館看到過徽州三雕與動畫《哪吒之魔童降世》結合的3D打印手辦——哪吒。
總之,這三種跨界的例舉就可以說明徽州三雕與動畫之間的跨媒介還存在著很大的空間,需要后來者進行更多的大膽嘗試和創新。
三、戲曲和徽州三雕的跨媒介
徽州三雕在徽派建筑中具有豐富的圖像樣式和獨特的精神價值,徽州三雕采取的是世代相傳的方式,這使徽州文化特征、價值觀念一直延續到今天。徽州地方深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儒家的美學價值是“中和”之美,“中和”美在戲曲中處處可見,例如演員的情緒、面部妝容,服裝色彩以及戲曲中的“大團圓”結局等。工匠在進行徽州三雕戲曲制作時,就會無意識的將這些細節帶入到創作中,比如徽州三雕戲曲人物“作揖”的姿勢。在戲曲中“作揖”是要由內向外畫一圓形,然后身體要形成一定的弧度,磚雕刻畫生動的體現出了這一點。雖然徽州儒學深受追崇,甚至有“徽俗不尚佛、老之教,所謂浮屠老子之宮,絕無有焉”的言論,但是道家思想作為中國三大家學之一,是一直流淌在中國人的血脈中。道家追求的是“虛靜”,戲曲中最常見的便是“虛”的體現,比如,戲曲中的上下馬、敲門、庭院的四面透空等,這些形式都在徽州三雕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把戲曲搬上銀幕一直是中國影視領域的一大代表性題材。戲曲跨越到徽州三雕是典型的綜合型媒介跨越到視覺媒介。徽州三雕中的戲曲元素一直存在,它在形式上一定程度采納了戲曲的服飾裝扮,所以這也就造成了徽州三雕戲曲的研究一直包含在其他大類中,比如在“忠孝節義”等方面的研究。其他的研究論文多涉及服飾應用等,如王曄的《徽州三雕人物的服飾造型研究》;程小武的《論徽州建筑雕作藝術》。徽州三雕對于戲曲元素的借鑒,促成了徽州三雕風格的變化,延伸了戲曲的時空,拓展了徽州三雕的圖案形式。
戲曲中有著豐富的造型設計。戲曲題材在徽州三雕的取材中有較大的占比,徽州三雕的人物造型設計很多都有戲曲特征。徽州三雕有很多形象設計是按照戲曲的造型特征來的,工匠在創作時會進行適當的調整,以適應徽州三雕的整體風格。如:戲曲中不同的藝術形象都有著不同的臉譜形象,不同的色彩表現更是代表著不同的情緒變化。雖然徽州三雕添置顏色不是主流,但是工匠會根據故事情節的需要,對雕刻人物形象進行設計,以讓觀賞者能夠觀察到戲曲人物的形象和情緒特征。臉譜在戲劇中一直是一種象征性的符號,人物的性格、善惡、忠奸等都可以通過臉譜得到辨識,比如扮演張飛的演員在印堂上畫上一只桃,扮演魏延的演員的額頭上畫三根反骨等;除了表現性格等方面,臉譜還是徽州三雕戲曲暗示情節發展的重要手段,不同的臉譜畫法代表著不同的角色結局,比如項羽的雙眼畫成“哭相”,暗示他的悲劇性結局;包公皺眉暗示他苦思操心等;戲曲臉譜還可以使觀眾和舞臺的距離感,臉譜讓臺下的觀眾看不清演員的面貌,從而讓觀眾專注于劇情。但是當徽州三雕和戲曲的結合就突破了這種局限,工匠讓生活中的故事與戲曲形象相結合,使得觀賞者可以在心理和生理上進行近距離欣賞,突破了戲曲臺上臺下的限制。
戲曲服飾的特點(圖6、圖7)也是重要的標志,戲服上有著大量精致的紋樣,不同紋樣代表著地位、官職不同的人,這些紋樣在徽州三雕上面會進行適當的簡化,但是服飾的大體特征還是會保留的。如戲服上的龍虎豹等動物紋樣以及梅蘭竹菊等花草紋樣;還有一種紋樣就是象征圖案,如蝙蝠,福祿壽,蘭花等,都蘊含著豐富的寓意;線條組成的紋樣也是必不可少的,如云紋,幾何紋等。唐肅宗宴宮圖(圖5)中,工匠就采用了戲曲的衣帽造型,這些元素在徽州三雕創作中比比皆是,戲曲中人物造型的多樣變化,相應的在徽州三雕戲曲中得到體現。
戲曲中的動作是一種特色的表現,戲曲人物的動作設計表現著角色的心理變化,具有強烈的符號意義。戲曲人物動作跨越到徽州三雕中得到了適當的變化,更加能夠體現出戲曲故事的瞬間高潮,具有明顯的象征意義。戲曲中的“唱念做打”并不是復制到徽州三雕中,徽州三雕會根據處理手法對戲劇內容進行改造,然后得到徽州三雕的完成品。糅合兩者的優長,呈現出徽州三雕獨有的圖案造型。
徽州三雕的圖像媒介代替了戲曲的舞臺效果成為主要表現形式之后,這并非是簡單的媒介轉換。作為圖像媒介,徽州三雕并不能展現戲曲的整個時空過程,他需要從戲曲的情節發展中選取某一節點進行刻畫,也就是從動態轉向靜態,而這就需要徽州三雕來采取戲曲情境中的高潮點,就是萊辛所說的“賦予孕育性的頃刻”。徽州三雕刻所刻畫的是充滿著暗示意味,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激發觀者想象的戲曲頃刻,并不是隨機選取戲曲節點來刻畫。戲曲和徽州三雕的跨媒介研究對于雙方都是一個恒久不變的課題。

圖5:黟縣承志堂宣統(1909年).唐肅宗宴宮圖局部

圖6:黟縣承志堂宣統(1909年).寧波華少考證.鄧艾 鐘會 二士爭功

圖7:黟縣承志堂宣統(1909年).寧波華少考證.華容道 關羽放曹
四、徽州三雕、戲曲和動畫跨媒介的學術探討和價值
徽州三雕、戲曲和動畫具有很多的共通性,這是形成跨界的契機。首先,都具有強烈的民族傳統精神。儒道佛思想根植在中國人的血脈中,這三種思想深深的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舉止,以至動畫創作者和徽州三雕工匠無意識的將思想帶到作品中。其次,都是娛樂手段。對徽州三雕的鑒賞、對戲曲、動畫的觀賞都是一種娛樂身心的模式,工匠從徽州三雕創作中感到滿足感,鑒賞者從徽州三雕中得到樂趣。戲曲、動畫的娛樂功能是毋庸置疑的,戲曲、動畫作品的故事情節就能讓觀眾感到愉悅。最后,都具有展示性。徽州三雕在現實生活中作為一種裝飾媒介,他根據場景的需求來改變自身的創作模式,如牌坊,支柱,門窗,庭樓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戲曲、動畫是一種另類的展示性媒介,如幕前的妝容、服飾、布景等。
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之間的共通性也代表他們有極大的跨越空間,由此產生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跨界的可行性研究。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作為文化載體,具有豐富的題材。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的跨媒介能夠給予彼此很大的創新啟發,成功的動畫需要深入人心的故事情節,徽州三雕、戲曲中存在著大量的故事,比如《蘇武牧羊》、《桃園三結義》、《平升三級》等。徽州三雕戲曲不僅使動畫的創作題材更加豐富,而且能將動畫中的環境渲染得更加完善。同時,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的跨媒介讓彼此獲得更廣更新的發展。徽州三雕戲曲中的角色形象能夠成為動畫角色設計的靈感來源。徽州三雕戲曲集結了眾多的民間藝術的特點,具有的藝術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徽州三雕戲曲中的人物造型,服裝特點,臉譜等各不相同,動畫角色設計可以從徽州三雕戲曲中借鑒一些符合劇情需要的角色來加以渲染,增添動畫整體的效果呈現。最后,徽州三雕戲曲具有強烈的地域特征。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的跨媒介使動畫體現出徽州的文化特征,免除了額外的大片敘述。這時,徽州三雕戲曲在動畫場景中就是象征符號,觀者可以通過這些象征符號了解故事深處的內涵與文化。
宮崎駿:“動畫是一個如此純粹、樸素,可以讓我們貫穿想象力來表現的藝術……它的力量不會輸給詩,小說或戲劇等其他藝術形式”那么當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進行跨媒介又會產生什么效應呢?
當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進行跨媒介的時候,那么就形成了一種傳統媒介走向了新型的數字媒介的轉化渠道,成為傳統文化的一種延續、傳承。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之間的異同導致了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的跨媒介能夠產生多種結合方式。動畫所具有的數字技術推動了徽州三雕戲曲的發展空間和敘事形式,讓徽州三雕戲曲能夠跨越時空的限制,在數字媒介中開辟新的展示舞臺。徽州三雕戲曲的物質性材料隨著時間的延伸會產生磨損,但是當這些材料以數字的形式存在于媒介中的時候,那么他存在的時空就會變得無限廣闊。徽州三雕戲曲所具有的精神、故事等也不會隨著傳播越加艱難而消失,他們和動畫之間的跨媒介使動畫承載了這種精神和故事。那么就形成了一種傳統媒介和新型的數字媒介的融合,成為新型數字媒介表現形式和精神價值的一種擴展、延伸。這種融合,也就是亨利·詹金斯所說的——“一個新媒介和舊媒介碰撞,草根媒介和公司媒介交會,媒介生產者的權利和媒介消費者的權利以不可預測的方式進行互動的場域”。徽州三雕戲曲中所具有的豐富故事資源、服飾形象等增加了動畫的表現形式;徽州三雕戲曲中所包含的道德精神、審美特征等美學價值都給予了動畫深刻的啟發內涵,讓動畫形成更豐富的價值背景。
同時,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在跨界的時候也不能忽視各自所具有的特色,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的跨媒介足以看到各自的優缺點,在進行跨界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時刻思考著動畫過程中遇到的波折,要汲取波折中的教訓,思考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跨越的得失問題。在跨越的過程中要時刻警惕瑪麗·勞爾·瑞安在《跨媒介敘事》中所提到的三個危險:“第一是有這個誘惑,將個體文本的特質視為媒介特征……第二個危險是麗芙·豪斯肯在本文結尾文章中所描述的媒介失明:為特定媒介(通常是小說)敘事研究而設計的概念,不分青紅皂白地遷移到另一個媒介的敘事中……第三個警戒是我所謂的‘激進相對主義’它存在于這一信念中,即因為媒介是獨特的,所以敘事學的工具箱必須為每一個新媒介從零開始重建……”雖然這三個危險是瑪麗·勞爾·瑞安在討論敘事的跨媒介中提出的,但是這也適用于徽州三雕戲曲與動畫的跨媒介研究。
總體而言,在兩個領域中的專業人士的積極推動下,徽州三雕戲曲和動畫的跨媒介導向是一種良性方向,這種融合是互益的。
結束語
動畫這種新型媒介手段,使群眾不斷以新的感官體驗來看待世界,重視動畫與徽州三雕戲曲之間的跨界是一種互益的模式。徽州三雕作為中國一種雕刻形式,發展到近代研究和創作已經趨于完善,具有自身發展的獨特性和規律。徽州三雕對于戲曲的圖像呈現,并不是簡單地圖式繪刻,而是民間文化精神、社會變遷等的體現。在數字媒體時代,社會、市場對徽州三雕行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徽州三雕戲曲的這一角度必須用創新的觀念和審美來看待,將傳統與新形式相結合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所以,從動畫角度來研究徽州三雕戲曲,不失為一種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