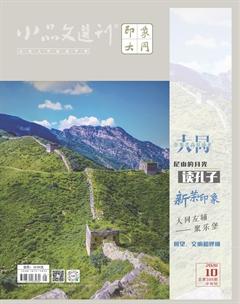活著的長城和文明的烈火
秦嶺


日月映血的長城時(shí)代早已遁入不遠(yuǎn)的昨天,如今以廢墟的形式融入大同人常態(tài)的日子和炊煙里,呈現(xiàn)出歲月原本的樣子。
我像一個(gè)天真的孩子,無邪地走進(jìn)長城的生命譜系,流連忘返于一個(gè)個(gè)城垛的傷口上、一處處撕裂的土堡里、一片片倒伏的殘?jiān)啊D且豢蹋杏X時(shí)間倒流,從今至明,從明至秦,及至更遠(yuǎn)……
綠,像這個(gè)時(shí)代從天而降的容顏,它不光挑戰(zhàn)著我對火山群的判斷,而且分明在提醒我:其實(shí),你已經(jīng)進(jìn)入大同火山群的核心地帶了。
長城的樣子
假如我畫出某個(gè)耳熟能詳?shù)闹黝},你卻辨不出畫了什么,那一刻,尷尬的你我該如何各自收場?比如,畫面上分明是長城的樣子。
我立即會(huì)看透你心目中的長城底片,那一定是“修舊如舊”之后重現(xiàn)江湖的完美高大和流光溢彩,這樣的慣性思維,豈能容得我畫筆下原汁原味、飽經(jīng)滄桑的容顏—我指山西大同的明長城,它的確是長城的另一種樣子,不!長城沒有第二種樣子,它就是它的樣子。作為明代九邊重鎮(zhèn),大同雄踞在渤海灣和西域之間,東眺山海關(guān),西望嘉峪關(guān),像一個(gè)誠實(shí)、堅(jiān)韌的挑夫,用長達(dá)數(shù)千里的扁擔(dān)戰(zhàn)略性地挑起朝代更替、御敵守邦的歷史輜重和戰(zhàn)事循環(huán)。我以當(dāng)代人的角色靠近天鎮(zhèn)、陽高、左云一帶時(shí),這才發(fā)現(xiàn)明長城分明就是一件未曾雕飾、裝扮的老物件,除了勉強(qiáng)可辨的各類圍堡,多為夯土、磚石的龐大廢墟,高高矮矮,凹凹凸凸,或突兀于平川梁峁,或湮沒與村舍阡陌,像一截截?cái)嗔训鸟R鞭,一個(gè)個(gè)倒下的烈士,一只只失群的信鴿,而總體觀察,像極了一個(gè)未經(jīng)打掃的古戰(zhàn)場,刀光劍影的留痕隨處可見,流彈箭矢的呼嘯似有可聞,千軍萬馬的逐鹿恍若眼前。“這才是長城的樣子”。我脫口而出。
陪同的大同人如數(shù)家珍:“大同明長城總長800多華里,配以內(nèi)堡,外墩,烽堠,轍道,全國罕見。”他同時(shí)不無遺憾地喟嘆:“可惜!更早的趙、秦、漢、北魏、隋、金長城,都已……”但在我看來,大同有了明長城,早先所有長城的投影、氣息便都在這里了。我必須相信,當(dāng)年秦始皇舉全國之力修筑長城重器,絕對不是為了打造工藝品。他老人家甚至一定想過,長城的終極美麗,就是殘缺,甚至消失。但他一定沒想到,就在幾十年前,中國的熱血兒郎們還堅(jiān)守在長城內(nèi)外,唱著這樣的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日月映血的長城時(shí)代早已遁入不遠(yuǎn)的昨天,如今以廢墟的形式融入大同人常態(tài)的日子和炊煙里,呈現(xiàn)出歲月原本的樣子。恰是在這種樣子里,歷史有的基因,長城有;歷史有的氣息,長城有;歷史有的訴說,長城有;歷史有的記憶,長城有。而廢墟,唯獨(dú)在這里浴火重生成生命的極致,它生機(jī)勃勃,血脈賁張,儀態(tài)萬方。我像一個(gè)天真的孩子,無邪地走進(jìn)長城的生命譜系,流連忘返于一個(gè)個(gè)城垛的傷口上、一處處撕裂的土堡里、一片片倒伏的殘?jiān)啊D且豢蹋杏X時(shí)間倒流,從今至明,從明至秦,及至更遠(yuǎn)……
這是長城活著的樣子,可它真的不像現(xiàn)代意義的所謂旅游景點(diǎn)。有游客沮喪地說:“這是長城嗎?感覺白來了啊!”這話,一時(shí)讓我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實(shí)際上有自我追問意味的:我為什么才來?“天下雄關(guān)”嘉峪關(guān)在我的老家甘肅,“天下第一關(guān)”山海關(guān)毗鄰我的第二故鄉(xiāng)天津,自然都是去過的,我甚至去過長城沿線更多的省市,多是聽說那里的長城被修葺一新,于是也難以免俗地成為趨之若鶩中的一員。直觀印象中同質(zhì)化、模式化的眾多長城,很難辨清跨越時(shí)空的歷史斷章和戰(zhàn)爭分解,以至于對家門口的八達(dá)嶺長城,我至今懶得涉足。我在某大學(xué)的一次文化講座中感慨:“要讓長城活著,必須要留住它傷殘、流血乃至死去的樣子。”我順手牽羊舉了圓明園的例子。大概是五年前吧,京津政協(xié)系統(tǒng)搞文化交流,北京某政協(xié)的一位委員眉飛色舞地告訴我:“我已提交了重建圓明園的提案,讓圓明園死而復(fù)生。”我笑問之:“仁兄到底是要讓圓明園死而復(fù)生?還是活而復(fù)死。”委員初愣,繼而頓悟,邃成至交。
大同的長城為嘛活著?也許是因?yàn)榇笸蟛煌拾伞D翘欤疑窠?jīng)質(zhì)地做了兩件事兒:先是吼了一曲古老的山西民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繼而在古堡內(nèi)打了一趟劈掛拳。同行的《香港商報(bào)》記者把我的洋相錄了下來,而某著名編輯家則給我封了個(gè)壯士的“美譽(yù)”。——壯士,約等于“不到長城非好漢”那種吧。是不是壯士,我當(dāng)然心明如鏡。但真正的壯士應(yīng)該選擇什么樣子的長城,好像還不光是個(gè)審美問題。
只是偶爾打開視頻,重溫那個(gè)手眼身法步早已不如少年的自己,吸引我的依然是大同明長城的悲壯背景。恍惚間,我不知道“壯士”到底是從歷史來到當(dāng)下還是從當(dāng)下去了歷史。這般的判斷,沒意思也難。
和朋友聊起大同之行,他說:“我心中長城的樣子,有了。”
走進(jìn)火山群
走進(jìn)火山群,卻疑似漫步綠島鏈。我脫口而出:“森林障目,不見火山。”當(dāng)然是對成語“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接龍。
綠,像這個(gè)時(shí)代從天而降的容顏,它不光挑戰(zhàn)著我對火山群的判斷,而且分明在提醒我:其實(shí),你已經(jīng)進(jìn)入大同火山群的核心地帶了。一瞬間,我仿佛在懵懂中穿越這樣一個(gè)現(xiàn)場:“轟隆隆——”在一陣緊似一陣的巨大轟鳴聲中,三十多個(gè)幻滅般的龐大液態(tài)火柱掙脫地表,刺破長空,大地劇烈顫抖,蒼天遮云蔽日,排山倒海的巖漿烈焰像洪峰一樣張開血盆大口,席卷方圓900平方公里的一切生命,最終在如今的大同盆地和桑干河流域宣示般地隆起了神秘而莊嚴(yán)的金山、黑山、狼窩山、馬蹄山、老虎山……
“火山爆發(fā),讓所有的綠色都沒了啊!”我身邊的一位大同人喟嘆。
這種喟嘆的神奇在于,它不光用綠色代替了所有的生命,而且似乎是,災(zāi)難仿佛發(fā)生在昨天。昨天是哪一天?是二十四小時(shí)前,還是幾萬年十幾萬年前?據(jù)載,作為中國六大火山群之一的大同火山群,大概從74萬年前開始,經(jīng)過三期反復(fù)多次噴發(fā),距今40萬年前進(jìn)入活動(dòng)高潮,大約在10萬年前才漸漸停止噴發(fā)。而74萬年前更為遠(yuǎn)古的時(shí)代到底噴發(fā)過多少次,人類的智慧鞭長莫及,因?yàn)椋祟愔徊贿^僅僅是人類。腳下,這些被學(xué)術(shù)界稱作火山渣錐、混合火山錐、熔巖錐的生命禁區(qū),古人曾痛心疾呼,興嘆疊加:“青山安在?安在青山?”。如此喟嘆,一今一古,如出一腔,像極了一次洞穿歲月的電話連線。
我必須相信,這絕不僅僅是作為靈長類動(dòng)物的人對綠色的呼喚。
視野里,除了樹,就是像繡花一樣小心翼翼栽樹的大同人和一臉好奇的觀光者。一位正在移栽幼樹的農(nóng)民告訴我:“過去,咱這雁北一帶山山‘和尚頭,處處‘雞爪溝,栽一棵樹比養(yǎng)一個(gè)娃還難。”這是大同人的幽默,但我沒笑出聲來。面對廢墟的微笑,一定比廢墟更要難看。現(xiàn)場聽到一個(gè)故事:有位負(fù)責(zé)林木管護(hù)的趙姓老兄,長年累月在艱苦的實(shí)驗(yàn)中育苗植樹,像大禹治水一樣三過家門而不入。有一次,他的一個(gè)朋友上墳時(shí)不慎引燃了25棵羸弱的幼樹,他一氣之下扣了朋友的車,還罰了款,監(jiān)督朋友補(bǔ)栽了樹苗,一棵,一棵,一棵……如今的火山群早已實(shí)現(xiàn)了種種的可能性,不僅披上了30萬畝的綠裝,還被國土資源部命名為國家地質(zhì)公園。有游客感慨:“綠水青山,讓火山群有了氣質(zhì)和尊嚴(yán)。”
一個(gè)比火山群更要古老的事實(shí)是:兩億年前的中生代時(shí)期,這里還是降雨充沛、江河縱橫的熱帶雨林氣候,在如海如瀑、如云似霧的萬頃綠色中,各類恐龍以主人翁的姿態(tài),自由、驕傲地繁衍生息了一億多年。如今,恐龍滅亡的原因早已不是什么迷局,可是,那些神奇的綠色去了哪里?我們叩問大地,可是,大地沉默如大地。要問與沉默對應(yīng)的詞是什么,你會(huì)想到爆發(fā)嗎?
但有一種東西,它是有聲音的,這是燃燒的聲音,它燃燒時(shí)與火山一樣通紅如霞,有形狀,還有溫度和光芒。它在如今千萬家現(xiàn)代企業(yè)的爐膛和老百姓的廚房里安詳?shù)厝紵拿纸忻骸K删G色變來,又化作灰燼而去。關(guān)于煤的成因,說法很多,其中的一種解釋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時(shí)期伴隨火山爆發(fā)造成的地質(zhì)變化,致使周邊植物被顛覆性地深度掩埋,從而演變?yōu)槊骸N抑幌胝f,那些消失殆盡的綠色生命,大多數(shù)最終還是以不可再生資源的形式饋贈(zèng)給了人類,其中的大部分,留給了工業(yè)化時(shí)代的我們。如若說,火山群是一堆堆生命的灰燼,那么,當(dāng)所有的煤化為灰燼呢?專家告訴我:“對煤炭的掠奪性開采早已讓大地和生態(tài)不堪重負(fù),大同人正在嘗試開發(fā)光伏發(fā)電資源,但是,煤,依然是人類的重要生命線。”
火山的光焰早已不在,但我們從煤的燃燒中,分明看到了與火山一樣的表情和模樣。而眼前的火山群,你能認(rèn)準(zhǔn)它到底是生命的樂章?還是墓碑。
一片樹葉,在地球上只有一次綠色的機(jī)會(huì)。那天,我曾小心翼翼地鉆進(jìn)一個(gè)深達(dá)150米的現(xiàn)代化煤井,輕輕的、輕輕的撫摸原煤的肌膚,一遍又一遍。在一些煤層的剖面,古代植物的葉脈清晰可見,我不認(rèn)為那是眾多綠色的集體死亡,它們更像萬古歲月里火山群一樣悲壯的睡眠,脈搏跳動(dòng),呼吸可聞。煤井只有150米,假如它是無底洞,我情愿走到底。它的出口,永遠(yuǎn)在地球上。
“咱栽活一棵樹,就是給前世還賬哩。”說這話的還是那位農(nóng)民。
已是午后,長空如洗,這是聞名遐邇的“大同藍(lán)”。馬蹄山那邊的樹林里傳來著名的山西民歌《圪梁梁》,深情而悠揚(yáng):
“對面山的圪梁梁上那是一個(gè)誰?
那就是要命的二妹妹……”
我納悶:“火山群里哪有要命的二妹妹呢?”
大同人笑了:“多啦。”
“何以見得?”
“一棵,一棵,一棵……”
一塊美麗絕倫的火山石就在我腳下,我沒好意思帶走它。它到底多少年沒享受這樣的綠了,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