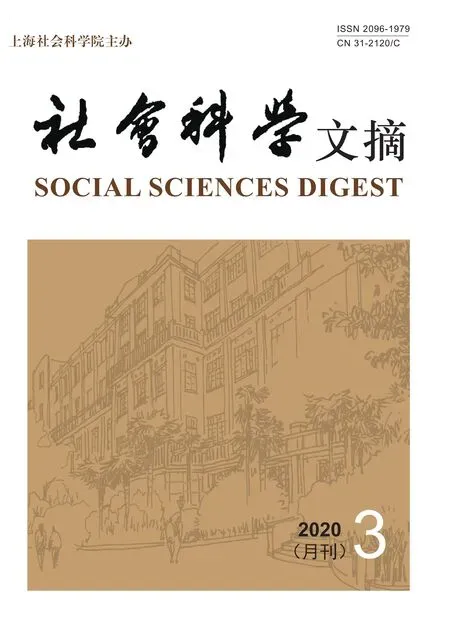浮動抵押逸出民法典擔保物權體系的理論證成
反躬自問:浮動抵押的獨特品格
概念的清晰與明確,體系的嚴格與嚴密,是現代理論科學發展的一大趨勢。只有概念清晰與明確,體系才能合理與嚴密。因此,欲討論浮動抵押與擔保物權的體系,首先需要對“浮動抵押”這一法律概念的基本特征進行科學界定。所謂特征(個性),指一事物之所以區別于他事物而獨有的特殊性質。因此,討論浮動抵押的特征,須滿足以下標準:該特征必須能夠使浮動抵押區別于其他事物且該特征為浮動抵押所獨有。就浮動抵押的特征,學界觀點莫衷一是,筆者擬從證偽與證立兩個維度來明晰浮動抵押的特征。
(一)對浮動抵押偽特征的駁斥
1.標的物僅限于動產非浮動抵押的特征
《物權法》第181條規定浮動抵押的標的物為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產品。但浮動抵押的標的物為動產僅是現象描述,并非區別于其他擔保類型的本質特征。若將標的物僅限于動產定為浮動抵押的特征,勢必將與浮動抵押制度的現實構造不符。英國法律中浮動抵押的標的物也可以是不動產。美國法律中浮動抵押的財產亦不限于動產,還包括知識產權、商譽等無形財產。
2.抵押人限于特定主體非浮動抵押的特征
浮動抵押人的主體受限制,為域外國家或地區立法上的通常做法。但從歷史維度觀察,浮動抵押人的范圍呈現出擴大的趨勢,故不能說抵押人限于特定主體為浮動抵押的特征。特定主體不能為某種擔保類型的義務主體并非僅限于浮動抵押制度具備的法政策傾向,某種擔保類型的擔保人限于特定主體亦非浮動抵押所特有,如見索即付擔保。
3.抵押物的集合性非浮動抵押的特征
浮動抵押物為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產品的全部或某類集合。但財團抵押也是以企業的特定財團為抵押物的抵押,即財團抵押的標的物亦具有集合性。故抵押標的物的集合性既非財團抵押的特征,亦非浮動抵押的特征。
(二)對浮動抵押真品性的揭示
1.浮動抵押標的物具有浮動性
在浮動抵押“結晶”前,浮動抵押并非固定在特定動產之上,而是存續于抵押標的物范圍內的整個財產之上。浮動抵押最本質的特征就在于抵押物的流動性。浮動抵押的標的物在形態上亦可發生變化,且浮動抵押當事人不需辦理任何變更手續而自動成為抵押的客體,如生產資本與貨幣資本的來回轉化。故浮動抵押的標的物具有可變性與浮動性。
2.抵押人對抵押標的物具有自由處分權
浮動抵押的最大優勢是在特別事由成就之前,抵押人可以在正常經營活動中占有、使用、處分其名下財產,浮動抵押權利人無權對抵押人的正常經營管理活動進行干預。立法者正是基于該制度之優勢,實現企業資金融通與生產流通并舉的立法目的,從而在《物權法》中對浮動抵押予以肯認。抵押期間轉讓抵押財產,《物權法》第191條并不適用于浮動抵押,債權人對抵押財產亦無追及權。究其法理,浮動抵押在固定化之前,其并非指向特定的財產,此時浮動抵押屬“休眠的擔保”(Dormant Security)。正因如此,債務人能夠靈活地運用資產,使得財產處于流動狀態,從而增加融資渠道和融資便利。
3.特定事由的出現使浮動抵押轉化為固定抵押
債務人為債權人設定浮動抵押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債權人債權的實現,因之,在法定或約定的事由出現之際,債權人即可行使權利,將浮動抵押轉化為固定抵押。因此,將浮動抵押轉化為固定抵押的確定通知乃浮動抵押權利人實現權利的必經程序。此時,浮動抵押人對抵押物不再具有自由處分的權利,即使為正常經營活動需要也不可。
綜上,浮動抵押的特征使得浮動抵押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物權法的“一物一權原則”和“物權特定原則”。
貌合神離:浮動抵押與擔保物權之悖離
(一)浮動抵押與擔保物權立法目的相錯
我國設立浮動抵押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和農民融資難問題。我國《物權法》視域下的浮動抵押制度主要著眼點為債務人利益,功能在于融資。但將浮動抵押置于我國《物權法》擔保物權體系之下,根據當然解釋的方法,浮動抵押制度的立法著眼點應為債權人利益,功能在于債的保障。不難發現,浮動抵押的法律制度與立法目的實際發生了錯位。擔保物權是以確保債權的實現而設定的權利,其目的在于降低授信風險。擔保物權的目的性決定了具體擔保類型應將債權人利益置于首位。回到《物權法》浮動抵押條款可以發現,該制度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和農民貸款難問題。浮動抵押的立法目的并非與擔保物權一致,立法者將其置于擔保物權之下,實為“合而不一”。
(二)浮動抵押與物權特定原則相異
物權特定原則亦稱物權確定性原則,是指物權僅能成立于特定的物上,即物權的標的物必須是特定的、獨立的物。作為貫穿法律始終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物權特定原則理應適用于擔保物權。但浮動抵押標的物具有浮動性,且抵押人對抵押物有自由處分的權利,因此,浮動抵押與物權特定原則相異,非擔保物權之屬。
(三)浮動抵押與公示公信原則相悖
物權公示的旨趣在于為世人知道某物有沒有權利主體、主體是誰和權利狀態如何。為實現“靜態秩序,動態安全”的法律價值,物權變動須經登記或交付,否則不生物權效力,亦無對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端視我國浮動抵押,其并無任何物權行為。《物權法》第189條提及的浮動抵押登記實為對債務人就某物(或將來取得的某物)向債權人設定浮動抵押這一事實進行登記。浮動抵押登記的對象、內容實與擔保物權中的登記發生了偏離,前者更多是對抵押人的登記,而后者是對擔保物的登記。即使浮動抵押登記,亦不能使第三人知曉與之交易的標的物已負有“擔保物權”。因此,善意取得制度在浮動抵押場域下亦無“用武之地”。
綜上所述,浮動抵押與物權法基本原則、物權法律效力、擔保物權特點格格不入。因此,具有擔保功能的權利,并非等同于擔保物權。
端本正源:浮動抵押法律效力的理論突圍
(一)對浮動抵押財產部分繼受人享有對抗權
債務人責任財產為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若債務人消極使財產流失或積極與第三人耗損財產,債權人債權自有不獲清償之虞。故法律賦予債權人代位權與撤銷權,以保全其債權之實現。債權人撤銷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阻卻債務人不正當地減少積極財產或增加消極財產,以保障債權得以完滿實現。但為避免過分地干擾債務人的行為自由,債權人撤銷權的成立在構成要件上較為嚴苛。相反,對浮動抵押權利人并不需要滿足嚴苛的構成要件而達至債權人撤銷權之法效。
申言之,浮動抵押雖未限制債務人對浮動抵押財產的處分行為,但其自由處分以“正常經營活動”為限,由是,當出現債務人放棄浮動抵押財產合同價款、無償轉讓浮動抵押財產、以明顯不合理低價轉讓浮動抵押財產等情事時,浮動抵押財產繼受人并不能對抗浮動抵押權利人就該財產主張優先受償權。與債權人撤銷權相較,浮動抵押權利人并不需要舉證證明債務人之處分行為客觀上詐害債權并致債務人陷于無資力,同時無需證明債務人與受讓人行為在主觀上具有惡意。不僅于此,即便是債務人處分浮動抵押財產乃“正常經營活動”范疇,若繼受人未支付合理價款或未取得(通過交付)浮動抵押財產,在浮動抵押“結晶”時,浮動抵押權利人仍可對抗繼受人,而就浮動抵押財產優先受償。在已有保證制度存續的法律體系下,即便證成浮動抵押非擔保物權之屬,但債權人對浮動抵押財產部分繼受人享有的對抗權,亦足以證明浮動抵押獨具的優勢。
(二)對債務人之浮動抵押財產享有優先受償權
非因債務人正常經營交易行為而繼受浮動抵押財產之繼受人,受浮動抵押權利人之對抗。此際,債權人有權就浮動抵押財產優先受償,其法理根據有二。一方面,優先受償效力并非擔保物權獨具之法效。優先受償效力并非擔保物權區別于其他民事權利之核心標準,如破產費用并非具擔保物權之債權,然其與公益債務一道居于第一清償順位。另一方面,法律賦予某項權利優先效力并非完全基于法律邏輯,某些時候乃出于立法政策考量。股東優先購買權、承租人優先購買權以及建設工程價款優先權,其并非物權之屬,但法律仍賦予相應的優先權效力,莫不因為制度背后承載的特別立法政策。同樣,浮動抵押優先受償效力也是出于特別立法政策考量之結果。
浮動抵押是為實現資金融通與生產流通并舉之目的,從而解決中小企業和農民融資難、融資貴之現實需要。賦予浮動抵押權利人優先受償權,正是考量這一立法政策之結果。基于一般法理,利益的法律表達方式并非僅限于權利路徑。表面上看是對債務人苛以更重的法律義務,實則是從義務層面進一步賦予中小企業和農民更多權益,以促成其進一步發展。如果債權人不能就浮動抵押財產優先受償,資金又怎會流向中小企業和農民手中,資金融通與生產流通并舉之目的又如何實現?
此外,需要廓清的是浮動抵押與抵押權、質權等擔保物權發生沖突時的清償順位問題。根據《物權法》第189條第1款之規定,未登記之浮動抵押權利人僅能在第三人具有惡意時,就浮動抵押財產享有優先受償權。此時,浮動抵押權利人的受償順位滯后于抵押權、質權等擔保物權。問題的關鍵在于,經登記的浮動抵押與抵押權、質權等擔保物權發生沖突時,何者優先受到清償?對此,根據“舉重以明輕”的當然解釋原理,即便浮動抵押已經登記,尚不可對抗正常經營活動中的第三人,那么因正常經營活動而創設的抵押權、質權等擔保物權,效力上顯然優先于浮動抵押權利,設定時間在此不問。與之相伴,若非因正常經營活動而在浮動抵押期間創設的抵押權、質權等擔保物權,同樣根據“舉重以明輕”的當然解釋原理,非因正常經營活動而繼受浮動抵押財產的繼受人尚且受到浮動抵押權利人的對抗,非因正常經營活動而在浮動抵押期間創設的抵押權、質權等擔保物權當然滯后于浮動抵押權利人受到清償。
綜上所述,浮動抵押雖非擔保物權,但并不代表浮動抵押之于債權人與一般債權無異。肯認浮動抵押的優先受償權,并非擔保物權法律效力使然,而系解決中小企業和農民融資難、融資貴之現實需要的立法政策考量。故,浮動抵押并非擔保物權之屬,相對合理的方案是將其“驅逐”出擔保物權體系。
棄舊圖新:浮動抵押逸出擔保物權的立法思路
(一)將浮動抵押置于擔保物權有悖民法典形式理性
良法善治之首要前提是構建形式科學、結構嚴謹、內部和諧的良法。對待我國民法典編纂,立法者應做到科學立法,遵循提取“公因式”的立法體例,構建符合形式邏輯理性的私法規則體系。反觀浮動抵押,若在明知其并非擔保物權的情況下,仍將其嵌入擔保物權體系,實為張冠李戴。在立法體例上,將破壞潘德克頓體系的邏輯嚴密性;在立法原則上,將與我國科學立法原則相抵牾;在實施效果上,將傳遞一個錯誤信息,即浮動抵押為擔保物權。因此,浮動抵押逸出擔保物權既具備合理性亦合乎必要性。
(二)浮動抵押宜嵌入合同編
在民法典分編未獨立設置擔保編的背景下,浮動抵押納入民法典合同編具有相對合理性。
首先,將浮動抵押置于合同編合乎法律邏輯。浮動抵押與債權具有天然的聯系,擔保債權實現系其制度功能之一。債之擔保類型具有開放性,言明浮動抵押債之擔保功能,并非一定需要將其與人的擔保抑或物的擔保相映射。浮動抵押既非指以第三人信用以及全部財產作為債權實現的人的擔保,也非指在特定財產上依法設定的物的擔保,而是獨立的擔保類型。
其次,將浮動抵押置于合同編合乎科學立法精神。從承租人優先購買權以及建設工程價款優先權等特別優先權制度可以看出,合同編規定優先權已非新創。某種程度上,將具有優先權的浮動抵押置于合同編,合乎立法先例。況且,浮動抵押涉及的第三人多為債務人之交易相對人,故將浮動抵押置于合同編更能兼顧債之相關制度,由此可以有效地避免法律體系邏輯的紊亂。
最后,將浮動抵押置于合同編更有助于司法適用。將浮動抵押置于合同編,對于法官將往往涉及大量債之交易關系的案件事實與相關法律規范準確涵射(Subsumtion)更有助益。浮動抵押置于合同編在立法指向上更為明確,還使民眾能夠更為清晰地認識到浮動抵押并非擔保物權。因此,將浮動抵押置于合同編具有正當性。債之擔保乃債的關系中重要一環,為豐潤債權制度的體系性與邏輯性,民法典合同編宜在第一分編(通則)第四章(合同的履行)之后增設一章(合同的擔保):一方面,可以很好地為浮動抵押找到安身之處,將浮動抵押規定在“合同的擔保”章節之下;另一方面,可以為新型擔保騰出一定的規范與解釋空間。
(三)浮動抵押宜更名為浮動擔保
浮動抵押宜嵌入民法典合同編,然浮動抵押基于其“抵押”字樣,將其一成不變地嵌入至債權體系又顯得多少有些不倫不類。因此,為避免滋生“合同編規定抵押”之虞,建議將浮動抵押更名為“浮動擔保”,以避免給人們產生錯誤導向。就浮動式財團抵押究竟稱為“浮動抵押抑”或“浮動擔保”,在該制度制定之初就存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英國Floating Charge制度既可譯成“浮動抵押”,也可稱為“企業擔保”“浮動擔保”“浮動債務負擔”或“浮動財產負擔”。第二種觀點認為,Floating Charge制度宜譯為“浮動擔保”“流動擔保”或“企業浮動資產擔保權”,持該觀點的主要為我國臺灣地區部分學者,從我國臺灣地區“企業擔保法(草案)”第3條第4項即可窺見一斑。第三種觀點即通說認為,Floating Charge制度系“抵押”的屬概念,而“擔保”乃抵押的種概念,基于種屬關系,稱之為“浮動抵押”更顯科學。
從詞源角度出發,高圣平教授認為英國法上“Charge”一詞與大陸法系的“抵押(權)”相似,意指既不移轉擔保物的占有,也不轉移擔保物的所有權的物上擔保,故將之稱為“抵押”最佳。查法律詞典,“Charge”并無“抵押”之意,與之意思相近的為“擔保、負擔”;再查“Floating Charge”,其譯文為“浮動擔保”。此外,考察比較法資料,Floating Charge制度在英國法上有另外兩種用法:Floating Security、Floating Mortgage,只是以Floating Charge最為常見;美國法以Floating Lien稱之,不難發現,Floating Security、Floating Mortgage、Floating Lien的用法更能印證Floating Charge稱為“浮動擔保”的準確性。根據翻譯的忠實嚴謹原則,Floating Charge制度在我國宜稱為“浮動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