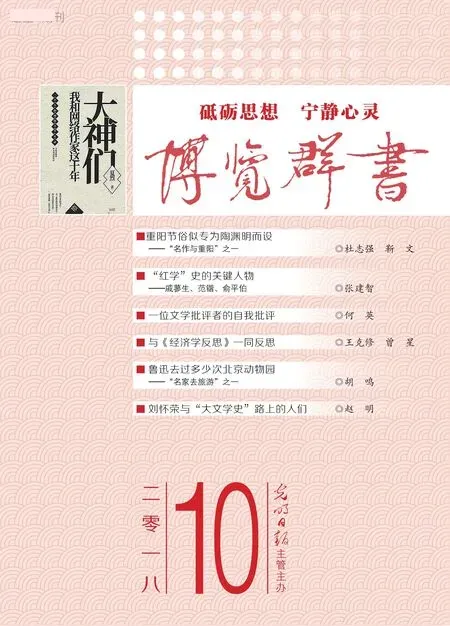檔案中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這三件事

《博覽群書》編輯部:
2020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著名教育家、病理學家徐誦明曾擔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西北聯大,其舊址被國務院列入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2020年,恰逢徐誦明誕辰130周年。筆者通過查閱歷史檔案又發現徐誦明先生不少歷史資料,對于我們了解70年前的中國高校及學人史頗有幫助,對于廣大青年了解他們所不熟悉的一代教育大家也很有裨益。
提到徐誦明,人們首先想到他從1928年到1948年歷任五所國立大學的校長(院長)以及擁有“大學校長典范”的美譽。他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和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是西北高等教育奠基人,也是中國病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從東渡學醫、參加同盟會、馳援辛亥革命、參加北伐,到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國之后選擇留在大陸領導規劃全國醫藥院校體系的建設發展;百歲人生,徐誦明教育報國的信念矢志不渝,影響深遠。1992年,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大學醫學部前身)塑徐誦明銅像于校園。2019年,西北大學復辦醫學院,首屆本科生班級被命名為“徐誦明醫學卓越班”。
本文從早年夏社故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畢業紀念冊、致函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等三件事情的有關資料談起。
夏社與三代人的故事
對于北京郭沫若紀念館一張照片的追根溯源,撥開了歷史上的一段迷霧。這張照片,正是有關于中國留日學生愛國社團夏社的影像與佐證。在時隔90年之后,這張照片還讓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徐誦明的外孫徐冬冬、陳中的女兒陳遜明相識相聚,寫就三家三代人的交往佳話。
巴黎和會的屈辱,五四運動的波瀾,讓身處日本、心系祖國的留學生群情激昂。其中,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院學生徐誦明、劉先登、陳中、夏禹鼎、余霖、郭開貞、藕炳靈等8人,志同道合,發起夏社。當時正值六月初夏,又是在夏禹鼎家中聚會,更因他們自詡為華夏人士,故而結社名夏。
日本外務省史料館的《青島民政部政況報告并雜纂》(1卷)當中,關于夏社的記錄提及上述8人名單以及行動綱領。其中,行動綱領包括:發行刻寫油印印刷品,每月發行一兩次印刷品分別寄送國內各省主要新聞社、各界;告知“倭人研究之內容”;負責接待同仁來九州帝國大學所在福岡市考察等。郭平英女士給徐冬冬先生也曾提到,當時日本駐旅順情報機關發現夏社成員往中國國內寄送宣傳抗日的印刷品,要求外務省將名單上的學生驅逐出境。
在上述名單可以看出,徐誦明排序最前。這并非偶然。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寫自己是1918年夏天升入九州帝國大學。就在這一年,徐誦明從該校畢業,繼續從事病理學研究;此時,他已接受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的聘任。比起夏社另外幾位尚在求學,徐誦明是有薪水的;“這從照片當中各人服飾也能看出這點”,徐冬冬介紹說,“外公出資買了油印機等物品”。
徐誦明資歷深厚。早在1908年即已加入同盟會;在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之后,歸國馳援革命黨人。他與郭沫若等人志趣相投,成立夏社可謂惺惺相惜,成為其中核心人物也在情理之中。1919年10月,署名郭開貞的《同種同源辨》、署名夏社的《抵制日貨之究竟》相繼在國內知名雜志《黑潮》發表,發揮了重要的宣傳作用。
醫學部學生大多更善于做病理、做診斷。翻譯和撰文,主要由郭沫若承擔。對于夏社活動經費,徐誦明慷慨相助,直至1919年秋天回國任教北京醫學專門學校。
徐誦明、陳中一直交往甚密。徐冬冬回憶道:徐誦明跟陳中是浙江同鄉,關系很好;徐誦明擔任北平大學校長期間,陳中推薦了同鄉范文瀾;徐校長舉賢不避親,聘用范文瀾擔任該校女子文理學院院長。
2009年,徐冬冬參觀郭沫若紀念館,向郭平英提到了照片當中的陳中,還提到陳中的女兒陳遜明。郭平英聽后非常激動,委托尋找。徐冬冬找到天壇醫院,單位一下子就提供了號碼。陳遜明其時90多歲,思路清晰,優雅美麗依稀可見。她知道來意后,緊緊握住徐冬冬的手不放,一說起徐誦明徐伯父,滿是崇敬之情;還提道:“您家舅舅(徐誦明之子徐一郎)在昆明的時候跟我說,他畢業之后要為我蓋一個診所。”這句表白是徐一郎在西南聯大清華建筑系學習期間,陳遜明則在昆明大學學習婦產科。有情之人卻未成眷屬,中間曲折又是另外一個故事。夏社,讓其成員后人,陳遜明、郭平英、徐冬冬在兜兜轉轉之后,相逢相聚、共話情誼。

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第八屆畢業同學紀念冊的故事
“人生到處何所似,應似飛鴻踏雪泥。”1934年夏天,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在該校文理學院的畢業紀念冊扉頁上寫下: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留此雪鴻相期進德。既是留戀眷顧,也是殷切期許。隔了八十多年的歲月,這本紀念冊翩若飛鴻歸來。后來者驚鴻一瞥,也能領略其時北平大學師生的卓然風采。
這本畢業紀念冊,是臨行臨別的點滴記憶,更是一本民國教育界名人題詞集。在校長徐誦明贈言之后,一系列名字如雷貫耳的人物依次登場,逐一寫出對莘莘學子的期望與鞭策。胡適贈曰:“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中國地質事業奠基人丁文江題寫:“畢業是做人的開始。”
“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周作人借陶淵明之句,寄語年輕人積硅步而至千里。該校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范文瀾則是給出一個“誠”字,指出內涵智、仁、勇。“言忠信,行篤敬”,物理學家夏元瑮曾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翻譯介紹到中國,他的贈言滿是修齊之道。
化學家楊光弼、哲學家張心沛、歷史學家兼鋼琴教育家李季谷、篆刻方面與齊白石齊名的音樂系主任楊仲子、年少即獲“桂冠詩人”美譽的英文系主任陳逵,都赫然在列。培養了得意門生周汝昌、葉嘉瑩的顧隨先生,其時在該院主講中國古代文學。朱光潛、吳宓、林徽因,則在該院英文系的教員名單當中。
綜上所述,上世紀30年初期的北平大學,來往皆鴻儒。但是,毋庸諱言,當年北平大學的人與事,如今卻被有意無意移植給北京大學。以訛傳訛,一是隨著時局變化,城市名稱在北京、北平之間輪換;二是北平大學抗戰勝利之后未能東遷復校,扎根西北。
如果要梳理這兩所大學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還得從1926年奉系入關談起。奉系在北京將9所國立大學合并組建“京師大學校”,北伐勝利之后國民政府通過“北平大學區大綱”,計劃將北平、天津、河北、熱河的高校合并為北平大學;因北京大學學生游行請愿,北大得以保留原有的三院組織,更名為“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北平大學不再具有行政職能之后,仍有五個學院,為京華院系設置最為齊備的院校。
1932年,徐誦明擔任北平大學第三任校長。他健全規章制度,實行人事聘任。在上述紀念冊題詞的著名教育家,不少是在北平多家高校兼職。
抗戰爆發之后,北平大學與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西遷,從西安到漢中,組成西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之后,時任同濟大學校長的徐誦明公示了陳立夫1939年承諾北平大學復校的電文;但是北平大學的五個學院,被國民政府要求留在西北服務當地,未能復校。北平大學在北京的房產校舍,多由北京大學接收。北大校長胡適以一句“我們的學堂”,算是化解了北平大學師生的心結。
北京大學,不是北平大學。北京大學,在大學區制時期,一度隸屬于北平大學,是北平大學的學院之一;在大學區制破產之后,它們是北平兩所國立名校。抗戰勝利之后,西北聯大當中的北平大學卻從此成為歷史名詞。
北平大學農學院大禮堂的貸款故事
在上海市檔案館,可以查到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在1937年年初寫給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的請求銀行貸款之信。北平大學為了紀念該校農學院已故教授許璇(字叔璣)教授,打算建設大禮堂兼圖書館。因經費不足,徐校長特向金城銀行求助,擬借三萬元。
感念許璇為中國農業教育事業所作卓越貢獻,北平大學曾于1934年12月16日為其舉辦公祭和校葬。由校長徐誦明主祭,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許壽裳、法商學院院長白鵬飛等陪祭。墓志銘由馬敘倫撰寫。

徐誦明給周作民寄送親筆函件,除了跟周作民請求貸款,還請后者代為聯系大陸銀行總經理許漢卿。徐誦明表示愿以農學院二十六(1937年)、二十七(1938年)兩年度學費收入、部分日常費用以及農場、林場的進賬,作為借款擔保;同時不忘請求利息優惠。
徐誦明意欲借款的金城銀行、大陸銀行,是上世紀年代商業銀行“北四行”當中的兩家。金城銀行、大陸銀行最初總部設在天津;此后雖把總行遷至金融中心上海,平津仍然為其業務重鎮。北平大學就近請求貸款,此為天時與地利。更主要的,還有人和。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大陸銀行故總經理談丹崖,皆是留日學人,與許璇情誼深厚。
徐誦明在請周作民代轉大陸銀行信函中還提到,北平大學農學院創建者前農科大學監督羅叔蘊(即羅振玉)與談丹崖(即談荔孫)為舊交。該校農學院與談荔孫交誼深厚的,還有前農科學長吳季青(吳宗栻)、前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校長路壬甫(路孝植)。
徐誦明在請周作民代為轉告大陸銀行的借款函中,所提人物不是教育家,就是銀行家。金城銀行周作民,大陸銀行談荔孫以及在1933年談先生病逝之后繼任該行總經理的許福眪(字漢卿),祖籍都是江蘇淮安。信中所提羅振玉祖籍浙江,生于江蘇淮安。淮安人周作民以及浙江人王國維,都曾在羅振玉1898年在上海創辦的東文學堂(教授日文為主)就讀。談荔孫和周作民在日所學都為商科,都是民國著名銀行家。
提到羅振玉,人們或許首先想到他在考古、金石方面的卓越貢獻。其實,他首先是一位農學家,1906年擔任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至于徐誦明提到的路孝植、吳宗栻,都是留日農學家,與北平大學農學院都有淵源。總之,信中所提諸位先生,皆有在日本留學或者學習的背景,或是同鄉,或是師生,或是同事,為親密朋友圈。徐誦明信函里提到諸位同仁,皆是稱呼其字以示敬重,頗有古風。這座承載故事的大禮堂,不知如今是否別來無恙。

徐誦明、郭沫若、陳中等人的一張黑白照片合影,記錄了上世紀初內憂外患之際一群中國青年的滿腔熱血、澎湃激情,也理應照亮當下青年。查閱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的一本紀念冊,雖是吉光片羽、雪鴻泥爪,依然讓人懷想北平大學的樹影夏日、名家光華。至于徐誦明致函金城銀行,記述修建禮堂的緣起、擔保貸款的常規做法,也反映了徐誦明經營管理學校的殫精竭慮。
楊蘇紅(九三學社上海文化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上海市金融委員會社員,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