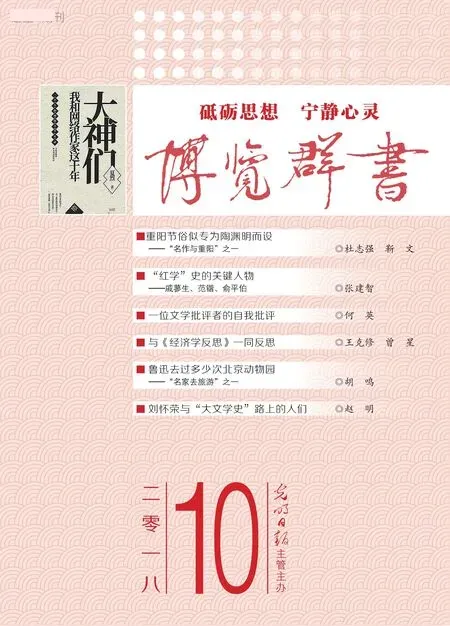激怒下作之人,慰藉體面之人
縱觀勞倫斯短短20多年坎坷而勤奮的文學創作生涯,竟然出版了11部長篇小說、60多篇中短篇小說、7部話劇劇本、12本詩集、十幾本散文隨筆集,還有幾本翻譯作品,這已經算得上十分高產,謂之汗牛充棟也不為過。但是等到劍橋出版社在本世紀初推出了長達八卷的《勞倫斯書信集》時,人們不得不對勞倫斯再次刮目相看,發現從體量上說,這八卷書信集(5400封長短不一的信件和明信片等)快與他的全部長篇小說或全部中短篇小說加散文隨筆持平了。勞倫斯在那個以書信為基本通訊交流手段的時代幾乎是天天都在寫信,甚至有時一天寫幾封信,在繁忙的創作和顛沛流離的天涯浪跡中,就是這樣保持著與親朋好友和文學出版界人士的溝通,為此大家都會情不自禁說勞倫斯是一個“了不起的書信作家”。
勞倫斯逝世的第三年,他的好友奧爾德斯·赫胥黎就迅速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厚本勞倫斯書信集并為此寫了很長的序言。一直到1979年,這部書信集幾乎是最權威的一部勞倫斯書信集了,其篇幅已經大約是兩本長篇小說的長度了。后來還有美國專家莫爾選編的勞倫斯書信集和幾本單薄的勞倫斯與某個人的專門通信集。赫胥黎曾感慨說,勞倫斯在書信里書寫了自己的一生,繪出了自己完整的畫像,沒有幾個人像勞倫斯這樣在書信里如此完整地展示其自我。
之后又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很多收到勞倫斯書信的人都紛紛為此作出自己的貢獻,比如我記得世紀初我在諾丁漢大學學習時,我的導師沃森就時不時高興地宣布他又從什么人手里買到了一封勞倫斯給誰誰的信件,感覺如獲至寶,就像古董商淘到了千年的真品一樣。他甚至告訴我發現了幾封勞倫斯用德文寫的信,他都翻譯成了英文準備出版。這些都是英國勞倫斯研究界真正的專業行為,他們不放棄任何可能搜集到的一封信,甚至勞倫斯寫下的只有寥寥數語的明信片都要不遠萬里地求索到手。
就是在眾多勞倫斯作品愛好者和專業研究人員的努力下,以劍橋大學伯頓教授為總主編的這套勞倫斯書信集第一卷于1979年出版,之后歷經23年歷程,終于在2002年出齊了八卷。所有書信都按照時間順序編了號、編了關鍵字索引并做了詳盡的注解,從1901年勞倫斯16歲上寫給工廠的第一封求職信開始到1930年逝世前幾天在病榻上寫的最后一封信,時間跨度近30年。
伯頓主編在序言中強調說,勞倫斯的收信人中除了他的舊雨新知,還有很多文化名人如作家福斯特、哲學家羅素、文學家加尼特,出版家若干,還有不少社會名流,勞倫斯走入了他們的生活,與他們有深度的交往,因此在書信中有過對社會問題的深度討論和爭論,這些書信客觀上透露了那20多年英國社會文化的多個側面,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但我個人更傾向于認為,這樣一套洋洋大觀的書信集無疑是寫在勞倫斯作品邊上的一部巨大的“注解”,是他生命的線索和藝術注解,對研究他的每一個創作階段甚至每一篇作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前我曾提出這樣的假說,即勞倫斯的作品分為虛構與非虛構兩個半壁江山,雙峰并置,我們經常可以將他同時期的虛構作品與非虛構作品進行對比研究,從中發現他小說里人物思想與現實中勞倫斯散文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思想傾向之間的關聯性,從而可以看到某些主要小說人物的價值觀與勞倫斯本人價值觀的同一性,從而在兩個領域看到勞倫斯思想的表達方式:小說里是藝術性的,通過小說人物的塑造進行表達,非虛構作品里則是直抒胸臆的散文式表達。而現在,毫無疑問,他豐富的書信集更直觀地呈現出他的日常表達,成為他兩個半壁江山的堅實腳注,這是貫穿他大半生和整個創作生涯的一條清晰的線索,是生命的自傳和藝術的自傳,其價值之重無論怎樣估計也不過分。
于是對于勞倫斯研究來說,虛構、非虛構和書信集就構成了勞倫斯世界的三分天下(當然還有他的繪畫作品,但其體量尚不足以構成第四座山峰,不妨暫時將他的繪畫與書信放在一起一并看作是勞倫斯文學創作的重要注解,勞倫斯的書信中多次談到他的繪畫理念和技巧),將這三部分有機地結合起來就使得勞倫斯作品的發生學研究更有立體感,更加活色生香,這棵勞倫斯文學之樹就更是長青的生命之樹。沃森教授曾評論說,勞倫斯的訃告多年來一直在改寫中,難有定稿,這與其作品與新時代層出不窮的新話題深度相契合有關,也與不斷挖掘出來的新的“出土文物”有關,書信集的不斷發現過程即是人們對勞倫斯不斷更新認識的過程。相信隨著對勞倫斯書信的持續研究,會有更多新的發現和命題涌現,這正是保持勞倫斯文學生命之樹常青的又一新的養分之源。
因此,從勞倫斯作品發生學的角度說,大量的談作品構思和出版的信件無疑是最有參考價值的。作為一個職業作家,勞倫斯的日常生活無非就是構思、寫作、與出版社或代理人談論稿件的發表與出版過程、出版后的推廣和遭到非議后奮起為自己辯護,這個過程中的各種遭遇都在書信中不斷提及,各種人情世故都在通信中有所觸及,自然會有充滿情感色彩的褒貶諷刺甚至詛咒。從早期的小說到最后壓軸大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寫作與出版過程中的信件幾乎令一個“工作中的勞倫斯”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信件的語言都是家常話,時不時憤怒情緒爆發還會有詛咒,高度的口語化表達恰似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日常的勞倫斯的言談舉止,嬉笑怒罵皆在信中。在沒有錄音和錄像的條件下,還有什么比得上這樣脫口而出的信件更真實地讓我們看到為作品殫精竭慮和為出版發行奔走忙碌的鮮活的作家勞倫斯呢?我想至少我是“看到聽到”了勞倫斯的音容笑貌和怒發沖冠。
作為對勞倫斯書信研讀的初步成果,我選擇了他晚期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寫作和出版過程中所寫的一些信件進行了翻譯,嘗鼎一臠,集中展現這段時間里勞倫斯的面貌,借此管窺“工作中的勞倫斯”。在雜志上發表時為了更為集中一些,除第一封信展現全貌之外,其余每封信都進行了段落的刪節,刪去了日常的寒暄和與作品無關的一些議論,只保留勞倫斯談藝和為出版而策劃征訂的部分。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是勞倫斯晚期最為看中的重磅作品,但因為語涉俚俗,不為彼時的社會道德理念所容,也成了最難出版的作品。勞倫斯為了保全作品的全貌,堅持一字不刪,完整出版,最終不得不自己找印刷廠設計印刷,出版私人征訂版。整個過程都活靈活現地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為保全作家的藝術人格而傾盡心血,為作品的出版發行而奔走呼號的勞倫斯。
為了說服朋友們為他散發征訂單,勞倫斯不斷地在苦口婆心說明自己的小說理念和小說的性質,他最為反感的就是有人將小說稱為性小說,勞倫斯不得不癡人說夢一般一再強調,這不是什么性小說。“陽物的思維比我們稱之為性的東西要深刻的多。我不管我的小說叫性小說,它是陽物小說。” “當然了,它確實是十分‘心地純潔之作。可是那些字詞都用上了!讓它們見鬼去吧。”“它是一本坦誠而忠誠的陽物小說,溫柔而細膩,我相信是的,而且我相信我們都要變得溫柔細膩。它會激怒那些下作之人,但肯定能慰藉體面的人們。無論如何請幫幫忙。”
除了苦口婆心之外,有時會發現勞倫斯幾乎是在懇求這些朋友幫忙散發征訂單,為了自己的作品完整地奉獻給世人,他也是拉的下臉懇求的。要知道這個時候他已經病入膏肓,只有兩年的存活時間了,經常咳血,經常感冒發燒病倒在床。這樣的拼搏,除了為自己的藝術,還能為什么呢?他甚至不乏高亢的理性主義宣言:
我必須賣掉它。這是一場遠征,咱倆都得上路,你幫我,我幫你。我知道你會盡力幫我的。我這是直接投向理性主義的財神頭顱的炸彈。當然,它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更加讓我靠邊,比我現在還要靠邊站。這是命運使然。你是跟我一起的,我知道。
讀這批信件,讓我們目睹了勞倫斯的“進行時”癡迷狀態,感覺真像在看直播一樣。而更多的信件都是如此這般地為我們“直播”勞倫斯工作、創作、交友、爭論、忙碌的現在時。讀這樣的信件是讀者的福分,讓我們回到了百年前,讓勞倫斯與我們同在,時空交錯,過去與現在交織在閱讀中,一時間忘卻了自己身處何方,只覺得就是與勞倫斯談笑風生、起坐交游,對他的境遇感同身受,甚至就是他的活動中的成員,在幫他發訂單,在聽著他的話發出會心的微笑,甚至隨時在回應他的精彩言論,這就是勞倫斯的書信帶給我的真實感受,我愿意將它分享給讀者。
(黑馬,本名畢冰賓,譯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