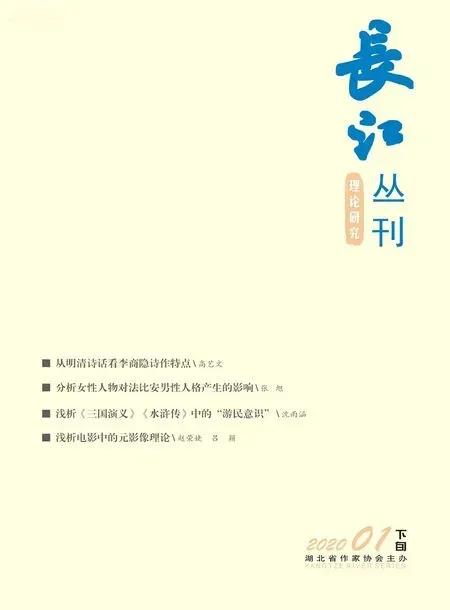田禾和新崛起的鄉(xiāng)土詩(shī)
■程光煒
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億萬(wàn)農(nóng)民離開(kāi)中國(guó)傳統(tǒng)鄉(xiāng)村奔赴城市的歷史進(jìn)程中,近年來(lái)一股新崛起的鄉(xiāng)土詩(shī)浪潮開(kāi)始受到人們的注意,雷平陽(yáng)和田禾是其中的兩個(gè)代表詩(shī)人。與雷平陽(yáng)對(duì)故鄉(xiāng)云南昭通的固執(zhí)的愛(ài)相比,田禾對(duì)湖北大冶和江漢平原的愛(ài)也是細(xì)致感人的。丹納在《藝術(shù)哲學(xué)》中令人啟發(fā)地談到歷史地理對(duì)作家性格和創(chuàng)作的影響,實(shí)際上,湖北的文學(xué)地理也有鮮明的特點(diǎn)。從黃岡丘陵山區(qū)到一馬平川的江漢平原,基本能囊括這個(gè)省份的地理特征。而孝感、咸寧的山區(qū)和恩施的崇山峻嶺,不過(guò)是對(duì)黃岡山川地貌的補(bǔ)充或伸縮修復(fù)罷了。我曾在湖北長(zhǎng)江邊上生活十年,那個(gè)千湖之省,無(wú)論山川地貌、風(fēng)土人情還是飲食習(xí)慣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gè)典型的江南。不過(guò),縱橫它的大地一路奔襲向東的浩瀚的長(zhǎng)江,又增加了這個(gè)省份人民性格的豪邁與倔強(qiáng),它的激烈的革命性格,這又是吳地軟語(yǔ)的江浙意義上的江南,以及我的故鄉(xiāng)徽州婺源意義上的江南,所不具備的。
田禾近年有一首令人難忘的詩(shī),名字就叫《江漢平原》,他寫(xiě)道:
往前走,江漢平原在我眼里不斷拓寬、放大/過(guò)了漢陽(yáng),前面是仙桃、潛江,平原就更大了/那些升起在平原上空的炊煙多么高,多么美/炊煙的下面埋著足夠的火焰/火光照亮燒飯的母親,也照亮勞作的父親/八月,風(fēng)吹平原闊。平原上一望無(wú)涯的棉花地/白茫茫一片,像某年的一場(chǎng)大雪。棉花稈/挺立了一個(gè)夏天,葉片經(jīng)太陽(yáng)暴曬有些卷曲/我順著一條小河來(lái),手指輕輕撫摸河流的速度/上下游的水都以一種相同的姿勢(shì)流淌/摘棉花的農(nóng)民把竹筐放在河灘,走近一座石橋/河里的魚(yú)翩然躍起,但河水還是來(lái)不及停頓/繼續(xù)向前流淌,水中的落日可能被絆了/一下,沒(méi)到黃昏就落了下去。這時(shí)候/遠(yuǎn)處村莊里,點(diǎn)起了豆油燈,大平原變得/越來(lái)越小,小到只有一盞豆油燈那么大/豆油燈的火苗在微風(fēng)中輕輕搖晃/我感覺(jué)黑夜里的江漢平原也在輕輕搖晃
“往前走”,這是詩(shī)人的視覺(jué)印象,“過(guò)了漢陽(yáng),前面是仙桃、潛江,平原就更大了/那些升起在平原上空的炊煙多么高,多么美/炊煙的下面埋著足夠的火焰/火光照亮燒飯的母親,也照亮勞作的父親”。我們假如有從武漢乘長(zhǎng)途大巴到荊州,路過(guò)這些縣治的旅游經(jīng)驗(yàn),是不難看到這一帶醇厚最美的鄉(xiāng)村景色,以及原野上近于油畫(huà)的人物形象的。小說(shuō)家池莉就是這一帶的人,可惜她很少用這種詩(shī)意濃厚的筆調(diào)寫(xiě)到這些風(fēng)物。就我而言,即使經(jīng)過(guò)千百次,也不會(huì)有這么動(dòng)情的感受。我雖然做過(guò)兩年知青,但缺少田禾這種出身鄉(xiāng)下的詩(shī)人那種切身的生命體驗(yàn)。想到這只是十幾年前、或許二十幾年的舊日景象,今天的鄉(xiāng)村已人走樓空,只剩下老弱病殘還在那里無(wú)望的癡守著中國(guó)文明的最后一塊凈土的事實(shí),恐怕不僅是我,還有許多善感的人,都會(huì)為被全球化和城市化所抽空的古老的鄉(xiāng)土而黯然落淚罷。
這種深摯的感情,在田禾近年發(fā)表的短詩(shī)中隨處可見(jiàn),例如《葡萄架下》《流水》《我的乳娘》《避雨記》《回家》《今夜的月亮》等等。上世紀(jì)80年代以饒慶年、張中海和龐壯國(guó)為代表的鄉(xiāng)土詩(shī),多少還夾雜著傷痕文學(xué)的某種痕跡,到了雷平陽(yáng)和田禾這里,則基本是以對(duì)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guó)鄉(xiāng)村問(wèn)題的思考為軸心的。最近二十年的當(dāng)代詩(shī)壇,一直是被先鋒詩(shī)統(tǒng)治著的,而且似乎給人越走越偏的印象。這就是寫(xiě)小人物小情調(diào)多了,寫(xiě)樸素人間的情感反倒顯得格外的離奇,田禾的詩(shī),正是在這里打動(dòng)讀者的。例如,看他的《葡萄架下》,表面上沒(méi)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滿(mǎn)院子都是葡萄的味道/葡萄架懸在頭頂,細(xì)密而/嫩綠的藤葉爬在木頭上”。聞捷和張志民50年代的《天山牧歌》《西部剪影》,在這方面都曾有精彩生動(dòng)的描寫(xiě),饒慶年的《山雀子銜來(lái)的江南》中,也有非常細(xì)致的記述。它之所以能打動(dòng)人,是因?yàn)檫@是詩(shī)人記憶中的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景象,它們?cè)?0年代后已不復(fù)存在。詩(shī)人依然那么固執(zhí)的堅(jiān)持著這種古舊的記憶,在我看來(lái)這就是打動(dòng)人的地方所在。詩(shī)歌除表達(dá)詩(shī)人自己的感情,另外一個(gè)功能就是以詩(shī)意的方式為我們留住逝去的歷史生活。田禾寫(xiě)詩(shī),靠的是樸實(shí)的情感,是對(duì)鄉(xiāng)村鄉(xiāng)土的固執(zhí)的熱愛(ài),是字里行間所透露出的對(duì)城市化進(jìn)程中鄉(xiāng)村文明衰落的感嘆。他對(duì)鄉(xiāng)土,有一種赤子般的忠誠(chéng)。從這個(gè)意義上,他是一個(gè)鄉(xiāng)村文明的堅(jiān)守者,就像60年代臺(tái)灣的鄉(xiāng)土詩(shī),30年代沈從文的小說(shuō)一樣,雖然歷史的發(fā)展遠(yuǎn)遠(yuǎn)把這些東西摔到了身后,但它們作為文學(xué)作品的魅力卻是越來(lái)越醇厚感人的。
田禾自然也知道,對(duì)鄉(xiāng)村文明的挽留,在現(xiàn)實(shí)層面上完全是徒勞無(wú)用的。他知道在感傷之余,還應(yīng)該用現(xiàn)代眼光對(duì)之加以理性的審視,在一個(gè)更高的思想臺(tái)階上來(lái)思考這些過(guò)去的東西。他的《夜宿高坪鎮(zhèn)》試圖表達(dá)的就是這種有距離的思緒。詩(shī)人嘗試著以游客的身份,來(lái)一個(gè)叫高坪鎮(zhèn)的地方旅游,參觀了農(nóng)家餐館和各種旅游景點(diǎn)后,因?yàn)樘焐淹恚淠_在某家旅店了。作品細(xì)致地寫(xiě)到了這個(gè)小鎮(zhèn)的風(fēng)物人情、一點(diǎn)一滴,不動(dòng)聲色地用攝影機(jī)式的筆調(diào),為我們復(fù)原出一個(gè)正在經(jīng)受現(xiàn)代文明洗禮的小山鎮(zhèn)的變化。
街道兩旁的農(nóng)家菜館一個(gè)挨著一個(gè)/為尋找那家八角村農(nóng)家樂(lè)/我誤入了一條老街。一個(gè)賣(mài)桃子的婦女/指給我,走過(guò)前面的那家老張肉鋪/再穿過(guò)一條小巷,拐彎就是/晚餐是清江魚(yú)、苞谷酒
這是典型的湖北小鎮(zhèn)景色,帶著南方意味的生活習(xí)俗和狀物特點(diǎn),就這樣一一進(jìn)入讀者的眼簾。如果每天路過(guò)此地,大概不會(huì)生出陌生化的幻想,但對(duì)于從未到此的游客而言,卻是無(wú)比新鮮的。最富詩(shī)意的是下面的句子:
今夜我要在這張吱嘎響的床上安睡/現(xiàn)在,清江在低處,高坪鎮(zhèn)在高處/我像一只半懸的吊鍋,煮著心事/窗外偶爾一道農(nóng)用車(chē)的遠(yuǎn)光燈/在我掛著藍(lán)布簾的窗口上一閃/算是小鎮(zhèn)一日里投給我的最后一瞥
作者在這里暗藏了他的“本地人”角色,似乎是以游客的感受寫(xiě)出了一種十分客觀的身居異地的感覺(jué)。不過(guò)仔細(xì)一看,最后這幾句,恰恰暴露了一個(gè)經(jīng)過(guò)修飾隱藏的已赴外地工作多年的本地人的濃重的鄉(xiāng)愁。這種鄉(xiāng)愁之所以綿長(zhǎng)無(wú)期,是因?yàn)樗鼘?shí)際超出了一個(gè)具體人的生活感受,是因?yàn)檫@是所有中國(guó)人的鄉(xiāng)愁——在全球化城市化歷史進(jìn)程中——每個(gè)人都在失去、或說(shuō)永遠(yuǎn)地失去自己的故土。這個(gè)進(jìn)程也許是緩慢的,不易覺(jué)察的,但是它被詩(shī)人敏銳的詩(shī)筆捕捉到了。與此我想說(shuō)的是,田禾還有一些表達(dá)苦難的作品,這種過(guò)于實(shí)在的詩(shī)作反而不如像《夜宿高坪鎮(zhèn)》更具藝術(shù)魅力。因?yàn)樗a(chǎn)生了一種必要的距離感。有距離感的事物對(duì)讀者的影響,可能要遠(yuǎn)遠(yuǎn)大于那些非常寫(xiě)實(shí)的東西。像朱自清的《背影》、魯迅的《朝華夕拾》、周作人的《烏蓬船》、沈從文的《湘西散記》,它們由于有了距離感,反而使人對(duì)那些逝去的東西更為懷念,生出更大的想象的空間。我理解田禾作為農(nóng)家子弟的感情,但是作為作家更重要的則是要經(jīng)常克服這種感情,將所要表現(xiàn)的東西加以升華。他的《夜宿高坪鎮(zhèn)》《江漢平原》都是這方面的佳作。它們的動(dòng)人之處就在于作者有意識(shí)地拉開(kāi)了與它們的審美距離,感情的距離,由于拉開(kāi)了距離,這些東西就變成了不止是他一個(gè)人的,同時(shí)也包括了所有人的感受。
另外,我想說(shuō)的是,從事新鄉(xiāng)土詩(shī)創(chuàng)作的詩(shī)人,在忠實(shí)自己過(guò)去生活感受的前提下,應(yīng)該把眼光放得更遠(yuǎn)大一些。例如放到那些到城里打工的群體的身上,增加一些他們生活的元素,超出一種懷舊式的藝術(shù)視角,把這些年輕人刻骨銘心的新東西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我記得田禾寫(xiě)過(guò)一首打工者如何從廣州千里迢迢輾轉(zhuǎn)回鄉(xiāng)的詩(shī)作,我對(duì)它印象很深。但我覺(jué)得這類(lèi)詩(shī)作還應(yīng)該寫(xiě)得更多一些,把藝術(shù)觸須深入到他們今天的生活當(dāng)中。這樣一來(lái),所謂新鄉(xiāng)土詩(shī)的崛起就會(huì)更令人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