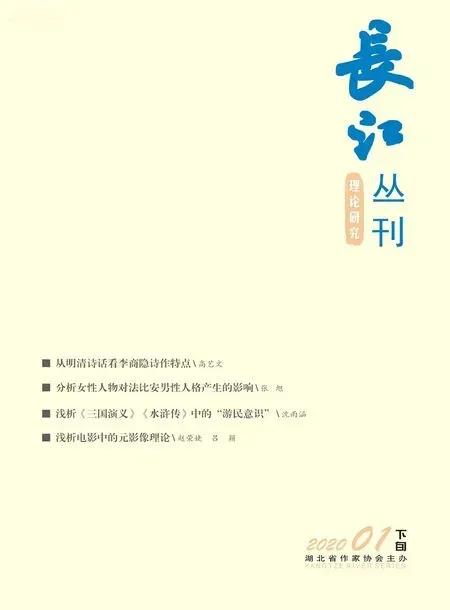分析女性人物對法比安男性人格產生的影響
■張 旭/西安外國語大學德語學院
新客觀主義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在魏瑪共和國動蕩的土地上。新客觀性是可見世界的回歸,同時也是魏瑪共和國的領先藝術運動。時間范圍通常與魏瑪共和國存在時間相同。在社會劇變、納粹力量上臺以及烏托邦夢想破滅后之后,藝術家開始轉回到日常對象,用客觀的呈現方式來表達現實,引發人們對現狀的思考。在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魏瑪共和國經歷了短暫的黃金發展時期轉而進入經濟蕭條時期,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原有價值觀的崩潰,使得魏瑪共和國搖搖欲墜。深處動蕩社會中的人受到消極的影響,而作為作家,他們有義務去描寫當時的社會現狀,表現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存危機,真實地還原當時的歷史現實。凱斯特納就是其中之一。
埃里希·凱斯特納(1899年2月23日—1974年7月29日),新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國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擅長對兒童心理進行描寫,描寫細致入微,故事情節生動,在吸引讀者閱讀的同時,會教給他們生活的道理,從而引領他們成長。由于凱斯特納對兒童文學的卓越貢獻,1957年,他被授予德國文學最高獎——畢希納獎,1960年,他被授予國際兒童文學最高獎——安徒生獎。
但是,除了兒童文學作品,凱斯特納也寫過為數不多的主人公是成人的作品,比如《法比安》。在本文中,我以《法比安》這部作品為例,試圖分析作品中女性人物對男主走向沒落產生的影響。
一開始,我介紹了新實用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比如經濟危機,失業,這些主題都無疑出現在新實用主義作家的作品中。但在閱讀時,我發現男公法比安除了承受經濟危機、失業等外部壓力,他在文中與女性的關系也同樣值得關注。另外新實用主義中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就是“新女性形象”。而文中的這些女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新女性。新女性起源于歐美,她們一反常態,不再終日待在家中,而是走上街頭,找尋工作,自食其力。除了經濟危機和失業現象,性別因素可以說是這部小說中的第二大主題。
新女性地位的不斷上升使得原有的男權主義社會受到沖擊,她們挑戰著原有的男權社會,身處這個社會中的“弱勢”男性必然影響,比如我們的男公。那么我這里提到的“弱勢”是什么意思呢?這里我主要是指男性人格的不完整,從而造成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障礙,比如文中法比安喜歡夜間活動,以及他最終選擇自殺。
弗洛伊德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了三重人格結構。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格是由三個部分構成的: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完全是無意識的,基本上由性本能組成,按“快樂原則”活動,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響,滿足本能要求,按“現實原則”活動,超我代表社會道德準則,壓抑本能沖動,按“至善原則”活動。本我和超我經常處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自我是試圖調和這對相互沖突的力量。在正常情況下,這三個部分是統一的,相互協調,當三者失去平衡時,即導致人格異常。文中,法比安受到新女性的沖擊,加上命運的打擊,最終他不堪重負,甚至最后選擇自殺。我認為,男主最后選擇自殺是他人格不完整的一個體現。
接下來,我將借助文本分析的方法,從文中找尋男主不完整男性人格的證據,并把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分成了三類。
第一類:母親。母親對法比安十分關愛,法比安在母親面前始終像是一個孩子。母親從老家德累斯頓來柏林看望自己的兒子,并給法比安帶來了錢,這時法比安說:“你不應該再為我花這么多錢。”母親卻淡淡的回了一句:“不給你花給誰花。”法比安于是也就沒有再堅持。從母親和法比安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母親賺錢的目的就是為了法比安,她始終覺得不管兒子多大,她都應該去照顧兒子,在看望兒子的幾天里,她為法比安安排好一切,給兒子打掃衛生,洗衣服。甚至在最后一天要離開柏林時提出要去接法比安下班,從這一情節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母親對兒子濃濃的愛意。而這種愛意往往太過強大,會影響法比安的男性人格成熟。
現在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法比安對母親的感情。深夜,法比安下班回到家中看到母親的信件,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一個人在柏林舉目無親,飽受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在這時,他心中突然萌生出一個念頭:為什么不回家,不回到母親身邊。在法比安充滿消極情緒的時候,母親是唯一能給他力量的人。在母親接兒子下班時,法比安走出公司大門,自然地把手給母親,母親也自然的抓住兒子的衣袖,這一動作宛如母親接幼兒放學的場景一般,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母子之間的濃濃的親情。
在經歷了與女朋友分手、好友自殺之后,法比安不堪重負,在他最無助的時候,他第一個想到的還是母親,于是他選擇回到老家。法比安進了家門,一看到母親,就哭著對母親說拉布達死了,這里法比安的哭我們可以看做是他情緒的一個爆發點,而他選擇在母親面前爆發,同樣也可以說明,法比安對他母親深厚的感情和信任。
作品中,法比安與父親的關系也同樣引起了我的關注。在法比安回到家中之后,甚至沒有跟父親說一句話,而且法比安的父親自己也說自己不了解兒子,“我根本不知道他還有朋友?”甚至父親會問母親“他要在這待多久”這種話,父子之間的關系完全是陌生人。
從文中的種種表述,我們可以看到法比安疏遠父親,親近母親,這會讓我們自然地聯想到俄狄浦斯情節,我們也可以說,法比安有一種戀母傾向。弗洛伊德曾經表示:俄狄浦斯情節在人格的建設過程中起到了一個決定性的作用。法比安的這種戀愛傾向說明他的人格中本我的在起主導作用,那么這個時候,根據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我們可以認為法比安的戀母情結導致他人格不完整。
在閱讀過程中,我注意到,盡管法比安有一種戀母情節,對母親有很強的依賴,但是他有時卻在壓抑對母親的感情。例如在他收到母親的信件后,內心中產生了想要回家的想法,但是法比安并沒有真正的回家。還有,在法比安失業后,母親來柏林看望他,但是法比安卻并沒有向母親吐露真相,而是選擇瞞著母親。
法比安所做的這一切可以說,他在進入男權社會中以后壓抑了對母親的依賴,由于受到過高等教育,法比安在這個社會中表現得像是一個道德家,法比安在進入社會之后,本我的力量被壓抑,自我和超我的力量得到了釋放,這時,法比安的人格得到進一步發展,但是三者的力量依然不均衡。這一不均衡還體現在法比安與其他女性的關系上。
第二類中包括兩個點。第一點:摩爾。摩爾在文章中是一個過度解放了的大女人的形象。她輕視男女關系,過分看重性在兩性關系中的作用,甚至開起了男性妓院。摩爾這個女性人物也同樣屬于新女性。一開始法比安對摩爾感到好奇,被摩爾所吸引,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說法比安是被本我驅使的一個過程,但是隨著慢慢接觸摩爾, 法比安又會對她產生厭惡情緒,對摩爾產生厭惡情緒的過程可以看做是超我力量激增的一個過程。摩爾對法比安的狂熱給他造成了一種心理上的壓抑,所以法比安在超我的驅使下不斷地拒絕摩爾,摩爾的出現并沒有促進法比安男性人格的發展。
第二點:畫室中出現的那些女性人物畸形的形象。對這些女性人物,法比安同樣是表現出厭惡,這不僅僅體現在現實生活中,而且體現在他的噩夢中。夢中這些女性畸形且丑陋的形象也同樣印證了法比安作為一個道德家高高在上的姿態,這也說明在法比安的人格中,超我的力量占據上風。
第三類是柯妮麗婭,法比安的女朋友。第一次在畫室見到柯妮麗婭,法比安便對其產生好感。在這場戀愛關系中,法比安一開始表現地很積極,這時本我的力量得到了釋放,柯妮麗婭的出現促進了法比安人格的進一步成熟發展。三者的力量處在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之后兩人確定了戀愛關系。但是好景不長,這一平衡很快被柯妮麗婭打破,柯妮麗婭一直夢想當一名電影演員,在欲望的驅使下,柯妮麗婭與電影導演發生了不正常的男女關系,而這是恰恰正值法比安失業和好朋友自殺。柯妮麗婭的這一決定斷送了法比安對她的愛,例如法比安與柯妮麗婭見面,往日的溫情不再,有得只是法比安對柯妮麗婭的冷嘲熱諷。他的冷嘲熱諷讓柯妮麗婭感覺陌生,甚至在柯妮麗婭吻別法比安的時候,法比安都覺得柯妮麗婭惡心。柯妮麗婭與法比安戀愛關系的一結束,意味著法比安男性人格的進一步成熟發展得到中斷。
最后法比安甚至對這段戀愛關系產生了雙重的道德標準。一方面,他指責柯妮麗婭的不忠,并且對柯妮麗婭感到惡心。另一方面他又與不同的女性發生性關系,以求得以慰藉。這些都足以說明,法比安的人格處在一個不成熟的狀態。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法比安依戀母親,遠離父親,有戀母傾向,在他進入男權社會中,他的這一戀母傾向得到了壓制,人格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但此時他的人格并不完整,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男權社會中,他遇到了許多的新女性,這些新女性的人物形象并沒有促進法比安男性身份認同的成熟發展,而是朝著一個更加畸形的方向發展。加上失去工作,女友的背叛,好友的自殺,親人的不理解,法比安最終不堪重負,選擇了自殺。
法比安最后選擇自殺可以看做是作家的巧妙安排,法比安這個人物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他是當時社會條件下眾多法比安中的一個縮影,在畸形的社會中,人格得不到完善,飽受社會和心靈的雙重壓迫,所以他最后的自殺也是他必然的選擇。正是這個縮影的出現,凱斯特納使得人們看到了當時知識份子、道德家在一個破舊不堪的社會的艱難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