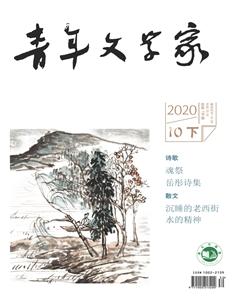林語堂譯蘇軾詞意境的變譯研究
崔小歡
摘? 要:本文從變譯理論出發,分析林語堂譯蘇軾詞的意境之變,開啟研究蘇軾詩詞的新視域,促進蘇軾詩詞在不同文化模子的碰撞中發展研究,更好地闡發中國故事,加快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關鍵詞:蘇軾;林語堂;變譯;意境之變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0-0-01
一、引言
1937年,林語堂英文撰寫了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快樂的天才》,從多個角度刻畫了蘇軾的形象,可以算是西方漢學界影響最大的蘇軾傳記,文中指出,蘇軾是個“秉性難得的樂天派……,是散文作家,是士大夫,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1]可見林語堂對文學天才蘇軾的欣賞仰慕之情。此外,林語堂先生的《東坡詩文選》中囊括了其翻譯蘇軾的詩詞文。對于古典詩詞而言,“翻譯承擔著中國古典詩歌在世界范圍內再造新生的職責。面對這個職責,我們需要更新觀念,不能一味以‘忠實為標準,把譯作和譯者貶為原作的奴仆”[2]。本文從變譯學理論出發,分析林語堂在翻譯蘇軾詞過程中,采用多種變譯手段,對蘇軾詞意境重構,再現詞之神韻。
二、變譯理論
變譯理論是黃忠廉教授提出的翻譯理論,他指出:“變譯是指譯者根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變譯是相對于全譯而言的,變譯與全譯是互輔相承的,變譯的存在不是與全譯對立,而只體現為派生、轉化和差異,它們并行不悖,共執譯事,相映生輝。”“變譯的核心就是變”,“變譯是對原作價值的凸顯,突出原作的價值是變譯的一大特征。”“發揮譯者的創造性是變譯理論的主要任務之一。”[3]在不同文化模子里,意識形態,詩學,讀者文化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譯者需通過對原文本進行變譯,再現本國文學的英姿,保留原語之神韻。
三、蘇軾詞意境的變譯研究
中國古詩詞文字凝練、意象疊加、意境優美,在他國化之旅中,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進行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通手段,再現原文本的價值,使譯作在譯入語文化中達到神似,甚至超過原文本的意境。蘇軾詞《行香子 述懷》: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
林譯:
O the clear moon's speckless, silvery light!? O what is knowledge, fine and superfine?
When filling thy cup be sure to fill it quite!? To innocent and simple joys resign!
Strive not for frothy fame or bubble wealth!? To be myself and in contentment face
A passing dream—? ? ? ? A valley of clouds—
A flashing flint—? ? ? ? ? A sweet-toned ch'in—
A shadow's flight!? ? ? ? ?A jug of wine!
原詩以景入情,意象疊加,夜色清新,月色如銀。對著這皎潔的月色,把酒述懷,抒發心中之情,名利乃浮云,只會徒勞傷神,嘆人生如夢,如白駒過隙,擊石之花,下片詞人轉入議論,表達出世之感,滿腹經綸,不被重用,何不歸隱田居賞溪云,彈古琴,飲美酒,豈不逍遙自在。開篇林語堂先生增譯了感嘆詞“O”,將第一句變譯成感嘆句,將詞人情之意抒發地惟妙惟肖,變譯后賦予了詞以嶄新的面貌。其次,在下片第一句,譯者同樣也采用增譯法,添加了感嘆詞“O”,進行變通,形式對等,意境優美,賦予了原詞以第二生命,將詞人對月述懷之意吟誦地淋漓盡致。
王國維將詩歌意境分為“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其中后者為最高境界。中國詩歌多無人稱代詞,留給讀者無限的想象。在西方模子里,由于語言差異,應增添人稱代詞,使詩意清晰。原詞中對月飲酒,如直譯,則是“Filling my wine cup”,增添了第一人稱,表明是詞人飲酒述懷,而林譯本則將其變譯,改譯成“filling thy cup”,變成了第二人稱,似乎有人在與詞人一同飲酒,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仿佛邀請讀者一同飲酒,詞人述說心中之情有了間接的聽眾,林譯本創新了詞的意境,將原文本價值發抒到新的更高境界。
再如蘇軾詞《水調歌頭》: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林譯:She rounds the vermilion tower,
Stoops to silk-pad doors,
Shines on those who sleepless lie...
本詞中是明月“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林語堂不落俗套,將月亮意象賦予了生命,轉譯成“She rounds,stoops,shines”,創新譯成第三人稱“she”,拉近了人與月的距離,月似人有情,讀來別有風味,不僅將中國文化中月之女性化特征發抒的惟妙惟肖,而且達到了變譯后增值地效果。
蘇軾詩詞融儒、道、佛,化典故于一體,文化意象詞豐富。本首詞上片說,人生不過是“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這三個文化意象是蘇軾化用。《莊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古人將人生短暫,稍縱即逝,喻為白駒過隙。另外,白居易《對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古人視人生如石之火。《莊子·齊物論》言人"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可見人生如夢。林語堂先生在把握原文本內涵之后,既考慮到西方讀者的接受,又凸顯文本價值的基礎上,將其進行了變譯,采用名詞并置手法,調整了詞的順序,先譯“夢中身”---“A passing dream”,緊接著才是“A flashing flint”,“A shadow's flight!”,將“人生如夢”的主旨放在三個并列結構之前統領,意象清晰,意境深遠,同樣下片的歸隱田居悠然自得的畫面---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林語堂先生同樣對詞順序進行了重新編排,采用名詞并置手法,轉譯成“A valley of clouds”“A sweet-toned ch'in”“A jug of wine!”,與上片相對平行, 形式優美,節奏明快,讀來朗朗上口,在中西文化不同審美層次上,達到了神似,收到了異曲同工之美。
“梅”這一文化意象在中國古詩詞中散發著濃濃的文化芳香,象征著高潔、忠貞。蘇軾的梅花詞《西江月 梅花》更是意象超俗,意境空靈:
玉骨那愁癱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
素面常嫌粉碗。洗妝不退唇紅。高情己逐曉云空,不與梨花同夢。
林譯:Bones of jade,flesh of snow,
May thy ethereal spirit stand unafraid,
Though the dark mist and the swamp wind blow....
Flesh of snow,bones of jade,
Dream thy dreams,peerless one,
Not for this world thou art made.[4]
本詞是蘇軾悼念侍妾朝云之作,全詞詠梅喻人,梅花玉骨冰姿,超塵脫俗,以花擬人,神形兼備。林語堂在翻譯“梅花”這一文化意象時,推陳出新,創造性地將第一句,與第二句進行了重組編譯,將“玉骨冰姿”合譯,化為首句“Bones of jade,flesh of snow”,再現了梅花之風姿。為再現詞之形式美,譯者將下片中增譯了“Flesh of snow,Bones of jade”與首句相呼應,最后兩句中“高情己逐曉云空,不與梨花同夢”意境尤為絕妙,蘇軾愛梅之情已隨朝云而空無,已不再夢見梅花,似物似人,而且詞中融入了佛語“情空”,意境空靈脫俗。林語堂先生不生搬硬套,把握原詞之意境,采用變通手法,創新重構,變譯為“Dream thy dreams,peerless one,Not for this world thou art made”,將原詞意境神韻闡發地恰到好處。
四、結語
為了凸顯原文本價值,考慮讀者的需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進行增、減、編、縮、并、改等變通手段,使譯作在譯入語文化中達到神似,甚至超過原文本的意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在中西文化視域中達到了異曲同工之妙。本文以變譯學理論為基礎,分析林語堂譯蘇軾詩詞的意境之變,拓展研究蘇軾詩詞的新視角,促進蘇軾詩詞在不同文化模子的碰撞中發展研究,更好地闡發中國故事,加快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參考文獻:
[1]Lin Yu-tang.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M]. New York: John Day,1937.01.
[2]王柏華.古典詩如何走向世界[N].人民日報,2009.07.07.
[3]黃忠廉.變譯理論[M].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96,86,89,70.
[4]林語堂.東坡詩文選[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127,1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