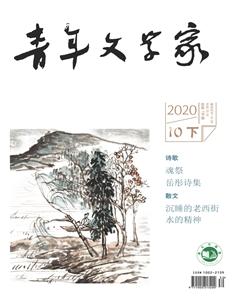用亞里士多德《詩學》淺析《暗戀桃花源》的語言藝術
摘? 要:賴聲川的經典戲劇《暗戀桃花源》運用對敘事時間和空間進行錯綜安排的藝術手法,展現了一段古今交織、悲喜疊置的奇妙故事。其中人物語言豐富多變,風格各異,尤為精彩;劇本語言簡明精煉,相映成趣,對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及體現人物性格起到了獨特的效果。本文運用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到的關于文學創作語言和言辭的理論,從語言的通俗化特點和隱喻詞的運用兩個方向來解讀、評價《暗戀桃花源》中的戲劇語言。
關鍵詞:《暗戀桃花源》;戲劇語言;亞里士多德;通俗;隱喻詞
作者簡介:謝倩(1994.11-),女,漢族,云南省楚雄市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美學。
[中圖分類號]:J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0--03
臺灣著名話劇導演賴聲川創作的現代戲劇《暗戀桃花源》講述了一個獨特的故事:“暗戀”和“桃花源”劇組因為合約問題互不相讓,同時在一個劇場進行彩排。“暗戀”講述的是青年男女江濱柳和云之凡因戰亂離散,苦戀多年未能結下良緣的愛情悲劇。而古裝喜劇“桃花源”則對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武陵漁夫的故事進行改編,講述了漁夫老陶因妻子春花與房東袁老板私通,一怒之下出走桃花源并在那里度過了一段快樂而近乎夢幻的時光,后來回家發現二人已經陷入相互糾葛與怨懟。這兩個故事從內容層面上來看似乎有著天壤之別,然而在排練過程中,兩個劇組演員嬉笑怒罵,無意中使劇情產生了相互呼應的喜劇效果。獨立于劇組之外,還穿插了一位身份不明、瘋狂尋找“劉子驥”的女子,然而劇本始終沒有揭示“劉子驥”到底是誰,由此產生了荒誕的戲劇效果。《暗戀桃花源》不僅在劇本內容上別出心裁,作為現代戲劇的經典文本,這部劇作的語言也尤為出色,劇本既有舞臺描述、人物獨白,也有群體的對話。其中的戲劇語言巧妙糅合了文言文與白話文,還在人物的話語中包含著不同的隱喻。通過對戲劇語言的設計,賴聲川在“不搭調”中展示了一種和諧之美。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西方美學史上第一部最為系統的美學和文藝理論著作,以簡短的篇幅闡述了文藝創作的本質及其與人物行動的關系,并對以悲劇為代表的藝術創作的原則進行提煉,內容極為深刻,對后世戲劇的創作及審美的方式起到了先導性作用,對西方美學及藝術理論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亞里士多德將悲劇劃分為六大要素,“把語言放置于悲劇六要素中的第三位,僅次于情節與性格”。[1]《詩學》的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與《修辭學》密切相關,亞氏在這幾個章節集中論述了語言在悲劇創作中的分類與運用,對語氣、言詞乃至字都進行了細致劃分,并與風格概念相聯系,提出了戲劇創作的語言的重要特征。整體而言,亞里士多德提倡一種相對中庸的語言創作觀念,既要求創作者遵循一定的規律,也鼓勵在適當的范圍內實現突破與創新。賴聲川秉承這種語言創作觀念進行寫作,“通中有變”的戲劇語言使得《暗戀桃花源》整體呈現出一種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明晰而不流于平淡”之美。
正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二十二章所表述的那樣,“措辭最大的美,在于清晰有條理,而又不能平淡無味。因此最清楚的言辭,是由我們日常使用的詞匯構成的”。[2]《暗戀桃花源》語言創作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明白曉暢、通俗易懂,結合人物行動與性格,使通俗的語言實現“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藝術效果。“桃花源”一劇取自古典文學,文言文作為“奇字”,無疑能夠使這個現代戲劇表現出高雅而不平凡的風格,但若采用對于大多數人而言艱澀難懂的文言文來作為對話,很容易落為“怪語”,于是,賴聲川以白話文為主,文言文為輔,巧妙地通過這種文白交織的藝術手法來展現人物性格:
老陶:嗨——嗨喲——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噯!我是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憤世嫉俗,情緒失調。我還是到上游去吧!嗨——嗨喲(老陶搖船槳而下。老陶復從左側上,浪花,漩渦布景。)
老陶:嗨——嗨喲,緣溪行,忘路之遠近。什么什么春花忘了忘了忘了!什么什么袁老板忘了忘了!哎,我記得前面不是有個急流嗎?嗨,不管了。(搖晃了幾下)啊——急流來了!(轉身,冷靜地)還有個漩渦。嗨——嗨喲(老陶下。復從左側上,桃花林布景)[3]
這一段講的是漁夫老陶因妻子春花與房東私通一事,對生活十分失望,想要在打魚途中尋求一條新出路,誤打誤撞進入了桃源圣地。創作者把古今相交的臺詞都引入到通俗易懂的日常對話中,用最通俗甚至俚俗的語言,例如語氣詞“噯”、“嗨喲”,以及口語化的表達“什么什么”等,直接作為人物臺詞運用到文學作品創作中,使得劇中人物更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主人公老陶隨性而發語,將一個失意倒霉、落魄尋路的真性情之人塑造得十分真實而親切。
除去對人物性格的塑造,通俗簡潔的語言在一些情景中蘊含著詼諧幽默的內蘊,使劇本充滿了活潑的氛圍和戲劇化的張力。在第五幕中,無法協調場地問題的兩劇同時在場上對半排練,劇中通俗的語言在作者巧妙的安排下達成了“重疊”或者說是“對照”的相互關系,頗為有趣,令人忍俊不禁:
護士:你算算看,從你登報到今天,都已經……
老陶:多久了?
護士:五天了!
春花:好久了!
護士:你還在等她,我看不必了耶!
老陶:我怕她在等我呢。
春花:她不一定想來哦。
護士:云小姐第一天沒有來,我就知道她是鐵定不會來了。
老陶:不,她會來。[4]
由此可見,《暗戀桃花源》摒棄華麗的藻飾,在創作中更注重對語言布局謀篇的策略安排。賴聲川用質樸、簡單、具有強烈生活氣息的語言,不僅極具表現力地塑造了豐富飽滿的人物形象,也完美地創造出了詼諧幽默、創新有趣的喜劇篇章,達到了亞里士多德強調的“清晰有條理,且不乏味枯燥”的效果。
此外,除卻通俗的語言,劇本對隱喻詞的使用也頗具特色。隱喻詞及《詩學》中第二十一章中的“隱喻字”,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隱喻字即是把屬于其他事物的名字,應用到眼前事物之上。“從這個種類轉移到那個屬性,從那個屬性轉移到這個種類,或者從一個屬性轉移到另一個屬性,或者也可以是類推事物”,[5]由此產生富有張力的戲劇效果,《暗戀桃花源》中的人物語言多次使用了隱喻詞這種表達方式,產生了別具一格的戲劇表現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劇本的現代性與先鋒性。
一方面,隱喻詞的使用暗示了劇中人物的宿命與故事背后的深刻內蘊。在劇本的開頭,第一幕中,江濱柳的唱詞中有一句“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6],他的戀人云之凡正如歌中唱到的這兩種事物,如流云般純潔、似流星般閃耀。但流云、流星皆是轉瞬易逝之物,似乎暗示了男女主角坎坷的命運,也不由得讓人聯想到這對苦命鴛鴦的顛沛流離,以及多年未果的愛情。與此相似的隱喻詞還有劇中“白色山茶花”的意象,“暗戀”劇組導演作為江濱柳的原型,在排戲過程中深切地注入了自己的個人思想與情感,一直在強調云之凡就像一朵純潔、美麗的白色山茶花,而山茶花開于冬季,且大多為紅粉顏色,白色山茶較為稀有。“白色山茶花”的這一特質也暗示了云之凡的命運——她是稀有而高貴的,因此她也不能如其他隨處可見的紅色山茶花一樣,獲得一份簡單、理想的愛情,便草草結束花期。
此外,“桃花源”中老陶的開場白也運用了隱喻詞,第一遍讀時覺得幽默詼諧,而對其中字詞進一步仔細揣摩,便能感受到人物深深的壓抑與委屈,從而為讀者帶來了余味無窮的藝術效果。第二幕中,老陶在家等待妻子買藥回來,使勁拔酒瓶蓋子卻怎么也擰不開,這時他便在家中自導自演、跳來跳去、牢騷滿腹:
老陶:(使勁)咿……呀!我就不信!呀我就不信我喝不著!(邊使勁邊重復)(到旁邊去拿菜刀。邊用菜刀弄酒瓶)我不喝可以了吧,吃餅!武陵這個地方,它根本不是個地方,窮山惡水,潑婦刁民,鳥不語,花還不香!我老陶打個魚,那些魚都串通好了一塊兒不上網!老婆滿街跑沒人管,這是什么地方,這根本不是個地方!(啃餅,啃不動,拿起菜刀砍,砍不動,扔刀子和餅)什么刀子,根本不是刀子!這也不是什么餅,這也不是什么餅!我踩死你,我踩死你,我踩……踩,踩![7]
這里的隱喻用得十分巧妙,事實上,酒仍舊是輕易就能夠打開的酒,武陵也只是他居住的家鄉,魚更不可能串通好一起不上鉤,刀子和餅也只是日常生活中普通、客觀的事物。但對于老陶來說,生活的郁郁不得志使他在對武陵、魚、酒、餅、刀子等物的埋怨之中寄托了無奈與失望,換言之,無論是酒是魚不過是老陶滿腔“憤懣”的別名,這些事物通過隱喻被賦予了人物的情感,使得戲劇更加豐富有趣。
除卻兩個劇組,在《暗戀桃花源》中,始終貫穿著一個瘋女人,一直苦苦追尋心中的愛人“劉子驥”,而賴聲川直到最后一幕也沒有直接點明他在劇中的身份與地位。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曾提到,“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劉子驥本身就是個不一定真實的存在,而女人卻不停追問、尋找他,這與西方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戈多”始終等待不來,正如“劉子驥”永遠無法被找到。賴聲川把陶淵明古文中的“劉子驥”轉移到現代戲劇之中,女人話語中的“劉子驥”即作為戲劇線索的隱喻詞,對他的無望找尋點明了劇本的主題與內蘊:自我主觀的美好幻想中那些永恒的美與愛也許根本就不存在,但人很有可能因為過分執著,陷入瘋狂的悲劇中。
另一方面,隱喻詞在對話中的使用有效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創造出令人意外的喜劇效果。亞里士多德認為“隱喻詞會造成謎語”[8],劇本中正是人物對話中“謎語”的重疊與強調創造出了獨特的藝術效果。例如在第二幕,老陶、袁老板與春花的一段對話中,多次用指示代詞來隱喻不同的含義,產生了詼諧幽默的喜劇效果:
袁老板:老陶你是這個這個這個那個那個說了老半天了,你直接把話說出來,不就……那個什么了嘛!
老陶:我真把話說出來不就太那個什么了嘛!
春花:你要不說出來那不是更那個什么了嗎!
袁老板:老陶!你……這個這個這個說的實在是不夠清楚!我看還是我來說吧!
春花:讓他說!
老陶:好!你說!
袁老板:我說你呀!我說呀,你那個那個那個……
老陶:我怎么怎么怎么哪個哪個哪個……[9]
在這一段戲中,老陶已經發現了春花和袁老板私通之事,但老實本分的老陶卻窩窩囊囊,拉不下臉面也不愿意把話全都挑明。而春花與袁老板都想擺脫老陶對他們二人的懷疑與束縛,礙于情面與道德也不愿直接說出心中所想。于是三人來回用“這個”和“那個”來指代彼此都知道、卻又不愿意直接在三人間說明的話。來回的語言博弈豐富地展示了三人之間微妙的關系,也使得這段戲笑料頻出。
亞里士多德指出,“對于措辭而言,掌握隱喻詞的手法尤其重要,可以說這是偉大的天才的標志,因為使用隱喻詞的能力充分地顯示出作家對事物相似點的感知”。[10]上文所引例證可見,《暗戀桃花源》一劇在人物對白中的對隱喻詞的運用不僅僅體現了亞里士多德所言的相似點,又在其中更上一層樓地把隱喻詞暗含的人物性格、情節線索交代得清楚明白,使得戲劇語言生動活潑,妙趣橫生,正如賀拉斯在《詩藝》中的強調的那樣,“如果你仔細斟酌用詞,巧妙選擇和安排,給每個普通的詞賦予新鮮的含義,你的表達就會非常精彩”。[11]
綜上,自亞里士多德時代起,語言在文學創作中就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塑造藝術形象、表達思想感情還是反映社會生活,都離不開對語言的審美把握。事實上,語言既是文學的外包裝,也是文學的內包裝,不僅是文學的“臉蛋”,也是文學的“身段”。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必然離不開精彩的語言組織與表達,現代戲劇《暗戀桃花源》的成功便離不開賴聲川獨特出彩的語言創作。王國維曾經在《人間詞話》中提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12]賴聲川選用的戲劇語言通俗而具有內涵,以言刻形,無論是現代的江濱柳、云之凡,還是古代的老陶、春花和袁老板,他們生動傳神的話語使得一個個鮮明可愛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也使劇本的主題更加明晰深刻。一顰一笑,景語與情語,都被編劇深厚的文字功力糅合在作品中,引導讀者在豐富多彩的語言中享受戲劇的藝術,實現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參考文獻:
[1][2][5][8][10][11]亞里士多德,昆圖斯·賀拉提烏斯·弗拉庫斯.詩學·詩藝[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
[3][4][6][7][9]賴聲川.暗戀桃花源[M].臺灣,1986(劇本).
[12]王國維.人間詞話[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