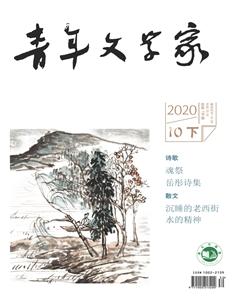南川方言關聯標記“不怕”的情理值梯級
摘? 要:文章考察南川方言中的關聯標記“不怕”。基本結論是:南川方言的“不怕”已經從否定結構詞匯化為具有“讓步-轉折”語義框架的關聯標記。“不怕”引導否定性高情理值事件和肯定性低情理值事件,并以前者為主。
關鍵詞:西南官話;詞匯化;連詞;“不怕”
作者簡介:趙青(1995-),漢族,女,重慶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現代漢語語法詞匯。
[中圖分類號]:H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0--04
一、引言
南川區隸屬重慶市,位于重慶市南部,地處渝、黔兩省交匯點。東南與貴州省遵義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正安縣、桐梓縣接壤,東北與武隆區為鄰,北接涪陵區,西連巴南區、綦江區。下轄3個街道、29個鎮、2個鄉,總人口68.65萬。南川方言屬于西南官話川黔片成渝小片。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南川方言中否定結構“不怕”的詞匯化狀態及其梯級否定功能,所據語料來源于日常口語和筆者內省。
漢語中“怕”是一個多義詞。一般辭書對“怕”的解釋是:1.害怕。(如:老鼠怕貓。);2.禁受不住。(如:這種藍布怕曬。);3.表示疑慮;擔心。(如:他怕遲到,六點就動身了。);4.表示估計(如:這么大的雨,我怕他來不了了。)(呂叔湘1980/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423)。由于“怕”本身沒有反義詞,所以它的反義為“不”字否定結構“不怕”。一般而言,“不怕”常常表示“不害怕”、“禁得住”、“不擔心”,為“怕”的辭典釋義所對應的否定義。但“不怕”在言語交際中逐漸構式化。“不怕你+V”超越了“不怕”的基本義,作為話語標記出現在口語交際中,起緩和面子威脅的作用(蘇小妹2014)。南川方言的“怕”與普通話中的“怕”基本釋義相同,構式“不怕你+V”也可以作為話語標記。并且“不怕”還走向了詞匯化的道路,似乎成為了關聯標記。例如:
(1)不怕他是我屋(家)親戚,都不幫這個忙,更不要說其他哪個外人了。
(2)不怕他是個局長,在領導面前照樣低三下四。
例(1)-(2)“不怕”已不再表示“不害怕”、“禁得住”、“不擔心”。同時也不能將其視為話語標記,因為話語標記不參與命題的表達,可刪除。例(2)中的“不怕”顯然不能刪除,并且具有邏輯語義,具有篇章連接作用。所以,我們認為南川方言中的“不怕”已經詞匯化為關聯標記。
本文要解決的問題是,詞匯化后的“不怕”在語義上有何特點。
二、“不怕”的共時詞匯化狀態
在南川方言中“不怕”的用法至少有三種:短語狀態、話語標記狀態、詞匯狀態。三種狀態有不同的句法環境。
(一)“不怕”作為短語
當不怕作謂語成分時為短語狀態,“不”否定心理動詞“怕”。例如:
(3)雖然我爸爸看起來很兇,但我一點都不怕他。
(4)這個娃娃膽子大,啥子都不怕。
(5)不怕他成績不好,就怕他品行不好。
例(3)和例(4)中“不怕”為短語狀態,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不是很怕他”。“不”具有否定義,“怕”的語義為害怕。例(5)中的“不怕”也為短語,“怕”為“擔憂”的意思。“不怕”作為短語時,往往伴有顯性的動作發出者。例(3)的動作發出者為“我”,例(4)的動作發出者為“這個娃娃”、例(5)的動作發出者為言者。當動作發出者被省略,“不怕”置于句首時,“不怕”開始向詞匯發展。例如:
(6)不怕他兇,在我面前他敢亂來試試。
(7)不怕他手上拿起(著)東西,打不過我的。
當“不怕”的動作發出者為說話人時,主語往往被省略,“不怕”置于句首。這時“不怕”可以表示“不害怕”,也有“即使”的讓步義,處于詞匯化的過渡狀態。但是這種過渡狀態僅限于言者對指稱對象在某種能力方面的比較語境。根據過渡狀態我們可以推斷,作為詞匯的“不怕”應該是由“不害怕”語義發展而來,而不是由“擔憂”語義發展而來。
(二)“不怕你+V”作為話語標記
“不怕”在“不怕你+V”話語標記中出現,該構式常常置于句首,“V”主要以心理動詞為主。“V”常常為“笑話”、“生氣”、“見怪”、“多想”、“不舒服”……以往研究認為“不怕你+V”為面子威脅緩和語(蘇小妹2014)。例如:
(8)不怕你笑話,我們結婚時,家里窮得叮當響。
(9)“老板,不怕你多心,男人怎么能理解我們女人對孩子的那片苦心呢?”
我們認為,上述用法是語用移情 。說話人移情的同時也誘導聽話人移情,聽話人識別、理解這個信號以后基于“互惠”(reciprocity)原理回贈移情。也就是說,說話人試圖通過移情獲得聽話人的反移情。例(8)和例(9)“不怕你+V”是說話人站在聽話人的角度上審視后續句,理解聽話人的情感,從而聽話人也會回贈移情,體會說話人的情感。
作為話語標記,具有可刪除性。但是在語義上“怕”仍然是“害怕”的意思,只是在使用的過程中語法化,但并未詞匯化。“不怕你+V”雖然還算不上是一個詞,但中間已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例如一般不說“我不是特別怕你笑話,我們結婚時,家里窮得叮當響”。
(三)“不怕”作為詞匯
我們認為關聯標記“不怕”屬于句法結構的詞匯化[1],是由否定結構“不怕”(語義為不害怕)演變而來。例如:
(8)不怕你是個大學生,從壹寫到拾可能都不會寫。
(9)不怕我沒去過那邊,我都曉得那地方不行。
例(8)和例(9)中的“不怕”參與命題表達,大致相當于關聯詞“雖然”。“不怕”在偏正復句中置于句首。“不怕”在句子一開始為全句設定一個讓步的語義框架,提供相關的主題背景,使聽話者對后文轉折的邏輯關系有一個良好的預期,能夠不依賴語境和上下文,有效地、獨一無二地表達整個句子的語義和邏輯關系,通過明確地、知性地引導建立小句之間的關聯,使句子有清晰的邏輯結構可循。
為什么“不怕”偏偏發展成了一個關聯標記呢?詞匯化的“不怕”與語法化的“不怕你+V”是否存在聯系? 復句是關聯標記詞匯化的句法環境。短語“不怕”常常出現在單句中,當言者將“不怕”置于轉折復句中時,“不怕”開始向關聯標記發展,由于語境吸收的作用,“不怕”逐漸吸收了“讓步”的邏輯語義。話語標記“不怕你+V”其實也隱含著“讓步-轉折”語義框架,意思是“就算你會V,但我還是要說。
三、關聯標記“不怕”與梯級模型
梯級推理是指人們以梯級中的某一參照點的情況去推導出高級的目標點的情況,從較高級的參照點的情況推導出較低級的目標點的情況(蔣勇2004)。我們認為,這個模型同樣適用于關聯標記“不怕”。由于南川方言中同時存在“不怕”、“雖然”、“即使”三個語義相近的關聯標記,但在使用頻率上“不怕”要高于另外兩個詞。所以我們利用兩兩對比的方式對“不怕”的語義特殊性進行分析。
(一)“不怕”與“雖然”的蘊涵關系
我們發現,“不怕”可以被“雖然”替換,但并非所有的“雖然”句都能被“不怕”替代。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是哪些能替代,哪些不能替代,其原因是什么。先看能替代的句子,例如:
(10)a.雖然王老師對我們這么兇,但我們還是喜歡她。
b.不怕王老師對我們這么兇,但我們還是喜歡她。
(11)a. 雖然你考了第一名,但是我還是看不起你。
b.不怕你考了第一名,但是我還是看不起你。
例(10)和(11)“不怕”和“雖然”可以互換,這說明“不怕”具有“讓步-轉折”語義。并非所有讓步語義環境都可以用“不怕”替換雖然。例如:
(11)a.雖然你考了全市第一名,但是不能驕傲。
b.*不怕你考了全市第一名,但是不能驕傲。
c.不怕你考了全市第一名,但還是上不了北大。
(12)a.雖然老師不在,但也要遵守紀律。
b.*不怕老師不在,但也要遵守紀律。
c.這個班的娃娃乖,不怕老師(都)不在,班上學生照樣遵守紀律。
(13)a.雖然今天下雨,但下得并不大。
b.*不怕今天下雨,但下得并不大。
c.不怕今天下雨,但我還是要擦防曬霜。
上述例句a式無法替換為b式,說明“不怕”與“雖然”不完全對等。“雖然”事實實說,客觀性強(邢福義1985),所以與事實言說兼容。但客觀性較強并不能解釋為什么例(11)-例(13)中的a式不能變為b式,卻可以變為c式,因為上述例句c式中“不怕”所引導的成分都為客觀事實。我們發現,“不怕p,但q”句式和“雖然p,但q”雖然都具有“讓步-轉折”語義,但轉折義的來源不同。其差異表現為,“不怕p,但q”句式轉折義的來源是對情理常態的否定,p和q存在情理聯系;“雖然p,但q”轉折義的來源既包括對情理常態的否定,也包括信息焦點強化,p和q不一定存在情理聯系。例(13)中“今天下雨”和“雨下得并不大”之間無情理聯系,也就是說“下雨”這個事件對“雨下得大”和“雨下得小”并不具有偏向性,所以不存在情理常態。因此,例(13a)不能換為例(13b)。但是“下雨”和“擦防曬霜”之間存在情理關系,即一般下雨天不擦防曬霜。由于言者對這一常態進行了否定,因此帶有轉折義。例(11a)和例(12a)為祈使句,q并非已然發生的客觀事實,“不能驕傲”和“要遵守紀律”只是言者期望達成的目標,體現其道義立場,也不存在情理常態。因此,例(11)和(12)中的a式不能替換為b式。而c式中的“考全市第一”和是否能“上北大”之間存在情理聯系,一般人們會理解為全市第一就有很大可能上北大,但事實剛好違背了這一常態,因此言者對這一情理常態進行了否定。“老師不在,紀律就不好”為情理常態,言者也對這一常態進行了否定。因此如果要讓“不怕”替換“雖然”,則必須建立情理常態。
“不怕”的主觀性較強是因為“不怕”在否定情理常態時,言者對p進行了梯級判斷。例(10)“王老師對我們這么兇”本身是一個事實,但在“不怕p,但q”句式中卻被賦予了主觀量的含義。因為“王老師對我們這么兇”、“王老師對我們不兇”、“王老師對我們有點兇”形成一個程度梯級,“王老師對我們這么兇”在量級上為最高值,按照情理常態已經可以構成“我們不喜歡她”這個結果,這是隱性的主觀梯級判斷。但“雖然今天下雨,但下得不大”中言者對“下雨”這個事件并不存在主觀梯級判斷。
綜上,我們發現“不怕”與“雖然”都可以置于“讓步-轉折”的語義框架中,但“不怕”只能表達對情理常態的否定,含有隱性的主觀梯級判斷。而“雖然”在擁有“不怕”語義的同時,還能表達無情理常態聯系的客觀事實。因此,我們認為“不怕”蘊涵于“雖然”。
(二)“不怕”與“即使”的蘊涵關系
“即使”相較與“雖然”而言,其主觀情緒較強,那么“不怕”是否等同于“即使”呢?有學者認為,“不”與“怕”組配語法化為連詞,相當于“即使”、“縱然”(趙雪,2016)。我們不贊同這一觀點。“即使”實言句必須在特定的語境中才具有明晰性。如果脫離特定語境,孤零零地說“即使p,也q”,往往會被認為是假言的,或者是真假不定的。“即使p,也q”句式的基本作用是虛擬的,實指示這種句式有條件的用法(邢福義,1985)。例如:
(14)即使你是他兄弟,他也不會幫你,他這人就是不近人情。
(15)不怕你是他兄弟,他也不會幫你,他這人就是不近人情。
“你是他兄弟”置于“即使”后,表示假設,說明“你并不是他兄弟”;置于“不怕”后,表示“你是他兄弟”是個事實。所以,南川方言中的“不怕”并不等同于“即使”、“縱然”。
其次,在一定條件下表示事實的“即使”是否可以完全替換為“不怕”呢?答案是不能。例如:
(16)a.這個箱子輕,即使小孩也搬得動。(肯定的低情理值事件)
b.*這個箱子輕,不怕小孩也搬得動。
c.這個箱子輕,不怕小孩搬得動,他都搬不動。
d.不怕這個箱子重,但這個小孩也搬得動。
(17)a.這個箱子重,即使大力士也搬不動。(否定的高情理值事件)
b.這個箱子重,不怕大力士也搬不動。
c.*這個箱子重,不怕大力士也搬得動。(常態的高情理值事件)
d.*這個箱子重,不怕/即使小孩也搬不動。(常態的低情理值事件)
e.*這個箱子重,不怕/即使小孩也搬得動。
(18)a.比你輩分高,即使年齡比你小,你也得叫他舅舅。(肯定的低情理值事件)
b.比你輩分高,不怕年齡比你小,你也得叫他舅舅。
c.*比你輩分高,不怕/即使年齡比你大,你也得叫他舅舅。(常態的高情理值事件)
王瑞烽(2015)從情理值梯級角度對“即使”進行了分析。“情理值”是建立在理想化的認知模型基礎上的。“語義理解的基礎是一個涉及背景只是的復雜認知結構。這種復雜的認知結構反映著特定社會各種相關認知域里的文化環境中的說話人對某個或某些領域里的經驗具有統一的、典型化的理解”(張旺熹,2005)。這種經驗式的典型化理解被認為是一種理想化的認知模型(張敏1988)。符合理想化的認知模型的事件是自然世界中現實生活中常態的、符合一般情理的事件,這樣的事件有較高的“情理值”(張旺熹,2005)。
“大力士搬得動”為高情理值,“小孩搬得動”為低情理值。“比你年齡大,叫他舅舅”為高情理值,“比你年齡小,叫他舅舅”為低情理值。通過替換測試我們發現,“不怕”和“即使”一樣無法引導否定的低情理事件和肯定的高情理事件,即常態事件。用“即使”的情況一般為肯定的低情理值事件和否定的高情理值事件。但我們注意到,一般沒有例(16b)這種說法,聽起來會比較別扭,例(17b)卻可以說。這說明“不怕”與“即使”不完全對等。在南川方言中,“不怕”一般引導否定的高情理值事件,卻很少引導肯定的低情理值事件。我們認為,這和“不怕”詞匯化前的語義有關。“不怕+X”中X的屬性偏向于主觀大量,因為不怕常態事件認為會怕的東西才需要用“不怕”強調。例如:不怕這只狗如此兇猛,我也敢去摸它。而不會說,不怕這只狗如此溫順,我也敢去摸他。“兇猛”和“溫順”是“我是否敢去摸它”量級中的兩端,“不怕”更傾向于主觀大量。一般主觀大量對應否定的高情理值。也就是說“兇猛”本來應該對應“不敢去摸”,但說話人為了強調“不怕”而否定了這一高情理值事件。因此,南川方言中的“不怕”往往引導否定性高情理值事件,而很少引導肯定性低情理值事件。
綜上,“不怕”在用法上蘊涵于“即使”。“即使”一般表假設,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表事實,“不怕”一般表示事實。“即使”可引導肯定性低情理值事件和否定性高情理值事件,而“不怕”更偏向于否定性高情理值事件。
四、結論
本文從共時的詞匯化狀態、真值語義、語用功能角度考察了南川方言中的“不怕”,得出以下結論:南川方言的“不怕”已經從否定結構詞匯化為具有“讓步-轉折”語義的關聯標記。“不怕”引導否定性高情理值事件和肯定性低情理值事件,并以前者為主。
注釋
[1]“語用移情”指交際過程中,說話人站在他人的立場,以他人的立場、態度來進行語言編碼。(方梅、樂耀2017).
參考文獻:
[1]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蘇小妹.面子威脅緩和語“不怕你+V”[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4(6).
[3]徐式婧.漢語偏正復句關聯標記的功能連續統[J].漢語學習,2020(1).
[4]趙? 雪.由“不X”式虛詞結構初透語法化理論[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
[5]董秀芳.詞匯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6]邢福義.現代漢語的“即使”實言句[J].語言教學與研究,1985(4).
[7]張旺熹.連字句的序位框架及其對條件成分的映現[J].漢語學報,2005(2).
[8]張? 敏.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9]王瑞烽.從梯級的角度闡釋“即使”句式及教學建議[J].漢語應用語言學研究,2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