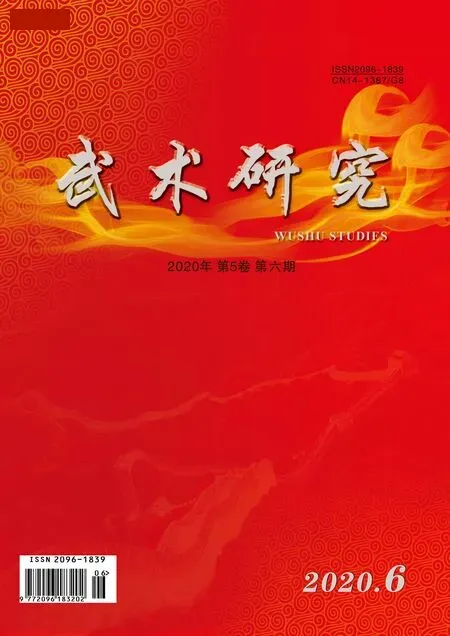儒家身體觀對武術精神文化的影響研究
馮仁嬌
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四川 遂寧 629000
古代人在沒有體育意識的情況下,身體觀就是從事體育活動的理論依據。身體是人類存在的物質基礎,儒家對身體的認識首先是承認身體的重要性,所以才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論斷。但儒家對于身體的認識不僅停留在生理上的軀體,更看中身體在心靈的主導下所表現出的社會化的德性,儒家對身體的認識表現出強烈的哲學性。武術作為中國傳統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一項技擊技術和健身方法,還是一種身體藝術,是中國文化的“全息影像”。本研究關注的是這種身體藝術在儒家身體觀的影像下表現出怎樣的精神文化特點,以窺探古代人們看待武術活動的文化心態。
1 儒家身體觀——“踐行”的身體哲學
儒家對身體的重要性、完整性的重視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受不同歷史時期權力和文化的影響,儒家身體觀并非是一以貫之的,如:先秦時期,在“六藝”教育體系中,孔子提倡通過禮、樂、射、御等身體活動達到教育目的,側重于通過身體的形態、身體的思維、身體與環境的關系表現道德秩序、倫理綱常和政治傾向;晉至唐時期,儒家思想在與佛、釋、道的沖擊與融合中,更加注重身體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禮儀對于身體的束縛有所減輕,追求精、氣、神健全的身體,身體被看做一種隱喻,是社會道德規范、政治權利的載體;唐以后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仍然強調通過身體活動實現“修身”的自我完善的目的。通過禪定、坐忘、靜坐等活動形式,達到豁然貫通的精神境界,追求身體從生理意義上的存在實體達到無身的理想生命狀態。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儒家與其他文化學說、宗教流派沖擊與融合中,對身體的認識也不斷的變化,但其內核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儒家的身體觀可概括為主張身心相合的“踐行”身體哲學,形成了作為政治權利展現場所的身體,作為社會規范展現場所的身體,作為精神修養展現場所的身體以及作為隱喻的身體。[1]身體作為一種社會化的工具,被權力和知識賦予各自時代的“目的”和“意義”,[2]但無論如何都沒有超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齊治平之論,表現出積極的入世精神。
2 儒家身體觀對武術精神文化的影響
體育文化可以分為三個維度:物質文化維度、制度文化維度和精神文化維度,其中精神文化是內核。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家文化影響和支配著任何一個文化領域,儒家身體觀也影響著習武者對武術的價值觀念、心理傾向和通過武術運動表現出的藝術文化。
2.1 躬身踐履的德藝修為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重行”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對于道理、知識的體驗與把握在于實踐,而實踐的基礎在于身體。武術非常重視習武者的“悟性”,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靠個人”,講的就是以口傳心授的傳統武術對精思篤行的重視,是對儒家“踐行”身體哲學的具體表現。師父的個人經驗體會來自于“時時操練、朝朝運化”的結果,手把手的教導遠甚于經驗之談,拆招、喂招都是在模擬實踐中提高技擊技術。拳諺“拳練千遍,其義自見”,是達到著熟、懂勁、階及神明的必經之路,要掌握嫻熟的技藝必須將師父的經驗教導經過身體的反復習練,才能轉化成自己的功夫。作為一種身體藝術,最真切、最可靠的個人技藝是在實踐中體驗得來的,需要個體經年累月的躬身踐履。通過實踐塑造出的不僅是嫻熟的技藝,還有習武者的道德人格,從紛繁復雜的拜師禮、象征著五湖四海為一家的抱拳禮開始,到習武鍛煉中磨礪出的意志品質,形成了一整套武德修養的行為實踐程序。尊師重道、門規戒律都在習武者日習而不察的日常行為中內化為習武者的價值認同和生命態度,最終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目標。
2.2 承擔社會責任的俠義精神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講究“克己復禮”“愛人”,遵循忠恕之道、中庸之道以修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修身,修身又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齊、治、平是修身的主體推衍,[3]也是修身的目的。武術悠久的歷史文化源于其不囿于一般意義上的身體活動,而是帶著自己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進入到更為廣闊的場域,表現出儒家傳統文化積極的入世精神。習武者忍受三膘三瘦的形體變化,經歷三伏三九的刻苦磨礪,希翼在技藝上有所建樹,不僅僅是追求一種技擊技術和養身方法,而是因為武術可以實現理想抱負、匡扶正義,是修身的方式和途徑。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當各方面矛盾平緩時,它輔助朝政,“治四海如磐石之安”;當社會矛盾激烈,則又蕩敵護國,“替天行道”。[4]“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民間武術雖然與軍事武藝有著本質的不同,但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影響著社會的安定與否。民族危難之際,習武者以“恢復中國為志”,突出民族大義,給予了無數習武者力量與責任感。
2.3 武學境界的整體意識
儒家對于身體完整性的重視也表現在武術運動的協調性上。田徑被認為是運動之母,其中各個項目也要求運動員的上肢與下肢協調配合,但主要是在于腳或手,而武術則強調牽一發而能動全身的整體協調性,其中包括內臟活動、呼吸吐納以及精神氣質。西方的拳擊、擊劍、摔跤等項目在技擊對抗中強調勇猛快捷、直拳直腳,而傳統武術則講究縱橫往來、圓轉變化,套路表演更是重視全身上下協調、龍騰虎躍、起伏跌宕的節奏變化。儒家認為“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反對“一己之力”“匹夫之勇”,不講“怪力亂神”,形成了武術倡導以“四兩撥千斤”的整勁和巧勁的技擊特點。作為承擔社會責任的外在物質力量,高超的武技需要不斷的鉆研,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內在道德修養的提高,也貫穿于整個習武生涯中。外在的物質力量和內在的俠義精神,兩者合二為一,形成了傳統武術中特有的最高武學境界,驅動著習武者窮盡畢生精力去接近、去實現,詮釋了儒家身心一體的整體身體觀。
2.4 “范我驅馳”的競爭意識
王良是春秋時期著名的善御之人,曾兩次為趙簡子的寵臣嬖奚駕車狩獵,因按規矩駕車一無所獲而遭受非議,又因不安規矩駕車收獲頗豐而獲得賞識,王良以“不貫與小人乘”為由“請辭”,后世對王良擇善而居的個人品質大加贊賞。這個記載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范我驅馳”的故事反應了儒家看待身體的“中庸之道”,教化人們身體活動應有節制,強調方法和手段的正當性。在眾多武俠文學和當代的影視作品中就能看到,競爭的雙方,一方總是占有絕對優勢,與人出手大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逼不得已。切磋時應點到為止,贏得漂亮,還要讓對方輸得體面,方能顯示出這一方德才兼備、德藝雙修的謙謙君子形象。如果在競爭中險勝了對方,自己被打得鼻青臉腫,即使贏了也不光彩。在儒家“中庸之道”的影響下,推崇“君子之爭”,體育活動、娛樂活動要符合禮制,身體活動更像是個人社會化的自我修行方式。
3 結語
儒家身體觀對于武術精神文化的影響并不都是正面的,傳統武術重視實踐使得武術技藝的深度得以挖掘,但是忽視經驗的總結與整理也使得武術缺乏理論的指導,荒誕經驗之談大行其道,以致現代武術的發展難以向科學理性邁進;中庸、禮讓的倡導下,武術作為體育項目的競爭性、娛樂性遭到了遏制,缺少“制度思維”使得武術在現代體育項目中顯得格格不入。但是傳統身體活動項目成為蘸滿禮儀的文化活動,在發揮體育的德性教化和身體訓練雙重功用方面,同樣具有著不容忽視的歷史和現實意義。[5]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國文化最積極進取,最主動作為的一部分,是激勵中華民族奮發有為的文化基因。受其影響,武術精神的博大弘深遠遠超過了武術本身。武術不僅僅是一種簡單、孤立的技擊技巧和健身活動,而且還是一種思維方式、人生態度和人格修養。[6]只有在整體上充分把握武術的特點,才能繼承和發揚武術的優良傳統,促進武術的健康發展。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