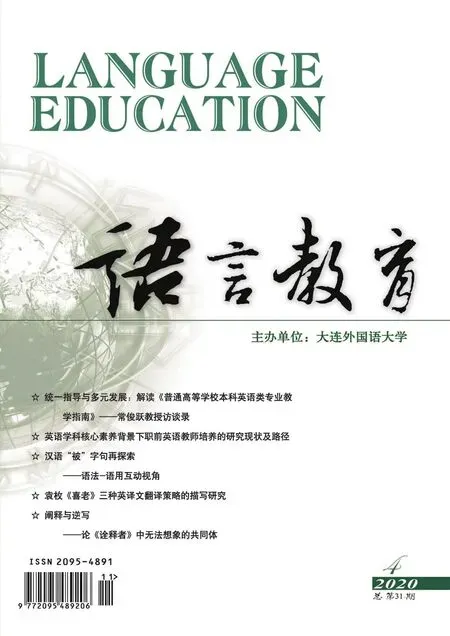教師情感研究三十年:理論視角、研究主題與發展趨勢
李小撒 王文宇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2. 南京大學大學外語部,江蘇南京)
常言道,喜怒哀樂,人之常情。《三字經》有云,“曰喜怒,曰哀懼,愛惡欲,七情具。”情感(emotions)是人生活的核心部分之一,長期以來一直是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的常見研究議題,相關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Clay-Warner& Robinson,2008)。教學過程蘊含強烈的情感體驗(Frenzel,2014),因為教學過程與學習過程一樣,都像是坐過山車,喜悅的巔峰過后就是沮喪的深谷(Scott & Sutton,2009)。情感滲透在教師工作的各個角落,發揮著核心作用(Nias,1996;Hargreaves,1998),但是教師情感研究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開始起步,發展較為緩慢。教師情感專刊《劍橋教育學報》于1996年問世,標志著情感研究正式走進教育領域(尹弘飚,2008)。進入本世紀以來,隨著人本主義思潮在全球范圍的興起,教師情感研究逐漸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并于2008年后呈現出較快的發展態勢(胡亞琳 王薔,2014)。
1. 教師情感研究的必要性
“教學是一種情感的實踐”(Hargreaves,2000),但是學界長期以來對教學情感層面的研究嚴重不足。在課堂情感研究方面,研究的焦點往往集中在學生身上(Schutz & Pekrun,2007),如學習焦慮、測試焦慮和口語焦慮等。在教學研究方面,教師一直被視作學習情境的提供者,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對教師提供的學習環境進行探討,包括課堂目標結構、學生之間的互動模式以及師生互動模式(Seidel & Shavelson,2007),但是很少有研究把教師當作有自己的動機目標、情感體驗的全人(Chang,2009;Nias,1996;Zembylas,2003),唯一的例外就是有關教師職業倦怠的研究(Hakanen等,2006)。
尹弘飚(2007)等學者認為,教師情感研究長期被學界忽視主要有以下兩種原因:(1)哲學傳統中盛行的理性和情感二元對立關系。長期以來,情感一直被視為理性的對立面,是理性的對手和威脅,研究者對“情感”一般采取“警惕”或“利用”的態度,因而教師情感通常被視作非理性的干擾因素并遭到壓制。(2)文化背景中居于主導地位的父權制意識形態。理性和情感分別被賦予截然不同的性別內涵。理性代表著男性的、積極的意象,情感則代表著女性的、消極的意象,因而情感與認知、理性和秩序等主流研究焦點無法兼容。
認知決定情感,情感反過來也會影響認知,并對人的顯性和隱性行為產生影響。教師情感對教師的決策、行為以及自我和身份的形成方面有重要的影響(Hargreaves,1998)。從保證教學質量的角度而言,教師情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教師的教學態度和師生關系發展。從提升教師“教育生命的創造性與質量”的角度而言,教師情感研究關乎“師生的個性發展和心理健康”(Pekrun & Schutz,2007:327)。從教師的職業選擇和專業發展角度而言,教師選擇從事教育行業、愛崗敬業或是放棄教師身份,普遍受到自身情感的影響。因此,教師情感研究對于教師的教學效果、專業發展和身心健康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2. 理論視角
2.1 個體心理視角
早期的教師情感研究基本上是從個體心理的視角研究教師情感的產生機制和影響,這種心理學視角至今仍是情感研究的主流。這類研究將教師情感視作教師個體的心理體驗,在研究方法上通常遵循心理動力學的方法論,使用標準化的量表來分析教師的喜悅、焦慮、憤怒、悲哀等具體的情感體驗。Sutton和Wheatly(2003)是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Frenzel(2014)所提出的“教師情感因果關系交互模型”(Reciprocal Model on Causes and Effects of Teacher Emotions)也主要是基于個體心理視角。這一類研究認為,個體通過不斷對刺激事件與自身的關系進行評價(appraisal),從而產生各種不同的情感體驗,因而評價是個體情感產生的內部心理機制;教師應該對教學相關的情感進行管控,并提升自己的情感智力。Salovey和Mayer(1990:185)提出,教師應當形成“準確感知、評價和表達情感的能力,接近并產生情感以促進思維的能力,理解情感及情感知識的能力,以及調節情感以幫助情感和智力發展的能力”。
2.2 社會文化視角
較之于將情感定位為個體心理的主流研究視角,立足于社會文化視角的教師情感研究呈現出明顯的理論視角轉向,即“把教師放置在社會互動的世界中理解其情緒表現”(尹弘飚,2007:46)。該視角認為,情感并非僅僅源于個體的生理本能或沖動,而是個體所處之社會文化作用下的產物。在社會文化視角下,教師情感研究關注社會文化、學校管理和專業規范對教師情感形成的作用,凸顯了社會規范、文化習俗等社會文化因素對教師情感的影響。Hargreaves(1998,2000)是基于社會文化視角教師情感研究的代表。這類研究借用社會學家Hochschild(1983)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情感規則”(emotional rules)、“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表層扮演”(surface acting)、“深層扮演”(deep acting),研究社會文化因素對教師情感的形成和影響。
2.3 后結構視角
這類研究認為,情感鑲嵌于文化、意識形態以及權力關系之中,在這個過程中被建構;情感的建構受情感規則的制約,被權力關系所控制和影響;教師可以通過接受或者抵制權力關系的方式對情感規則進行反思和批判,促使其發生轉變。根據后結構理論,教師情感具有變革性的特征,指向行動改進。換言之,教師情感具有能動性,不僅僅是對事件或外界刺激的簡單反應。權力關系雖然無處不在,教師也無法逃避情感規則的制約,但依然能夠利用情感“開展行動與變革”(Zembylas,2005b:21),教師情感具有反抗和變革功能(Zembylas &Barker,2007)。基于這種認識,這類研究者提出,教師不僅要做好情感調節,有效管控灰心、焦慮、憤怒等負面情緒,還應當對現有的情感規則不斷進行批判和反思,探索打破現有情感規則的方法和策略,建構情感系譜(emotional genealogy),創造更為和諧的情感環境。
2.4 生態學視角
近年來出現的生態學視角研究雖然尚未形成氣候,但是很可能會成為未來教師情感研究的重要方向。生態學視角下的相關研究綜合考量教師情感產生的個體因素與環境因素,提出個體因素與環境因素之間的互動是教師情感形成的內在機制(Cross &Hong,2012;Schutz,2014)。生態學系統視角認為,情感不是由單一因素建構而成,教師情感受其所處的種種生態環境因素制約;教師對于個體因素與生態環境因素之間交互關系不斷進行評價,教師情感是這種評價的產物。此類研究致力于從社會歷史環境層面認識情感事件(emotional episode)的成因,并在此基礎上探究教師與情感事件之間的互動關系。生態學視角具有創新意義,為教師情感的形成機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但我們還需探索該視角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有多大的適用性(古海波顧佩婭,2015)。
綜上,教師情感研究在過去30年中逐漸形成多元理論視角并存的局面。不管是個體心理視角、社會文化視角、后結構視角,還是近年來出現的生態學視角,都為認識教師情感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情感是個體的心理體驗,同時也是個體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產物,情感具有能動性和行動指向性。情感的多面性和復雜性意味著研究者需要打破不同理論視角的壁壘,綜合考慮個體、社會文化、環境等各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才能全面揭示教師情感產生的機制,充分解釋多種情感成分復雜的交互方式。
3. 研究主題
教師情感研究不僅有理論層面的探討,也積累了一定的實證基礎。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國外教師情感實證研究呈現迅猛增長的態勢,國內相關研究近年來也有顯著增加,研究內容大致涉及以下5個類別:教師情感概貌、特定類別的教師情感、教育改革中的教師情感以及教師情感智力和情感勞動。
3.1 教師情感概貌
這類研究探索教師的整體情感體驗,既包括正面情感,也包括負面情感。Cowie(2011)通過對9名經驗豐富的外語教師進行深度訪談,了解他們對教學環境和教學工作的認識,揭示其對教學、學生以及同事所持的情感。研究發現,受訪教師對學生表現出較為積極、正面的情感,而對學校和同事則表現出較多的負面情感。這一方面與社會對教師的角色期待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被研究教師對學生的關愛者和道德引領者的身份認同有關。在Waldron(2012)對科學教師Alejandra的個案研究中,研究者描述了該教師在教學工作中的各種情感體驗,并追溯這些情感體驗對該名教師職業生活的影響:學生的仰慕、家長的感激、同事的信任與情誼增強了她的信心,對新教師的同理心則推動她為對方提供指導,對應試教育的不滿激勵她向管理者提出對測試制度的意見并積極尋求改變,而對家人的愧疚感促使她試圖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到平衡點。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也開始關注教師的整體情感體驗。古海波(2016)通過對國內高校外語教師所做的敘事探究發現,這一教師群體在科研工作中體驗了正向、混合及負向情感,其中負向情感明顯多于其他兩種情感。顏奕和談佳(2018)使用多維樹形情感框架,采用質性個案研究方法探究了國內五位高校法語教師在專業生活中感受到的愛、快樂、意外、生氣、悲哀和害怕等六類情感體驗。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揭示,他們在其專業生活中的多個方面,如學生、同儕、教學、科研及職稱等,體驗了具有多樣性、復合性及變化性的情感。
3.2 特定類別的教師情感
(1)焦慮
焦慮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由對未來事件的預期、對過去事件的回憶、或者對自身行為的反思而引發(Keavney & Sinclair,1978)。焦慮分為狀態焦慮(state anxiety)和特質焦慮(trait anxiety)兩種形態。狀態焦慮是“個體處于某一具體情境時所產生的短暫、強度多變和緊張的情緒狀態,主要表現為某段時間內的不愉快情緒體驗,具有情境性、短暫性、不穩定性和多變性等特征;而特質焦慮是一種人格特質,是一種具有個體差異且相對穩定的焦慮傾向和焦慮易感性”(Spielberger,1985;王欣 王勇2015:31)。教師焦慮主要是前者,研究對象主要是職前教師和中小學教師群體(Sutton & Wheatley,2003)。
王力娟(2012)基于狀態焦慮領域的信息加工理論、行為反應模式理論編制了針對性的教師狀態焦慮結構模型,對我國中西部地區數百名中小學教師的控制感焦慮、沖突感焦慮、滿足感焦慮進行調查研究,發現狀態焦慮作為一種情緒狀態,在中小學教師中普遍存在;不同狀態焦慮水平的教師在認知編碼、判斷/解釋和再認識特點方面雖然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但過高的焦慮狀態會顯著影響教師的認知加工效率。
相對于中小學教師而言,高校教師的焦慮狀況更為普遍。王欣和王勇(2015)通過對上海地區72名學術英語教師焦慮狀態情況的調查,分析在通用英語教學向學術英語教學的過渡階段的焦慮特點。研究發現,學術英語教師在教師角色與家庭角色沖突、職業自我沖突、付出與回報滿足感、教學準備與課堂教學控制感、職業發展控制感以及教學效果控制感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無可否認,“知識爆炸”引發的“知識袪魅”增加了高校教師備課的時間和難度,“新時代的學生特征以及諸如慕課、翻轉課堂等新形式的涌現給當下的高校教師帶來了多種挑戰,而雙語、雙文化背景更是給外語教師帶來身份認同的多重焦慮”(古海波 顧佩婭,2015:54)。此外,隨著國內越來越多的高校強力推行“騰籠換鳥”的用人政策,高校教師“保住飯碗”的壓力也有增無減。無獨有偶,Lee(2014)對國外高校教師群體的研究表明,“publish or perish”的制度同樣使得高校教師焦慮程度持續走高。
(2)悲哀和憤怒
悲哀和憤怒也是教師最常感受到的兩種情緒,兩者常常難以區分。Sutton(2007)對30名中小學教師進行了深度訪談,并且對他們的相關情感日記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多數教師最常體驗到的情感是憤怒、生氣和灰心等負面情緒對教師的課堂教學行為具有顯著的消極影響。文秋芳和張虹(2017:21)的研究發現,不公正的學生評價會對高校外語教師的教學熱情產生持續而強烈的負面影響,“有些原本熱愛教學的教師而今對教學充滿負面情感,原因是不公正的學生教學評估結果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情。學生評教可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學情況,但學生的認知水平和情感因素也可能導致評教結果有失偏頗,以致極端評價打擊教師的教學熱情”。
在高等教育界,職稱評審中盛行的“科研一票否決制”也是導致眾多中青年教師灰心和憤怒的重要因素。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多個場合強調①對話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培養什么樣的人 辦什么樣的大學.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 /moe_1485/201612/t20161229_293339.html., accessed 2017-01-25.:教育要回歸初心,社會和學校必須重視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通過多種方式引導教師把主要精力用在教書育人上。遺憾的是,在國內很多高校,職稱能否評上與教學質量關系不大,只要有課題項目、有文章、有頭銜就足夠了,教學效果很好、廣受學生好評的“老講”不在少數,而教學效果一般、成果卻很豐碩的教授也不在少數。
社會認可的缺位會引發教師消極的情感體驗。Bahia等(2013)和Chen(2016)發現,當社會對教師的認可和尊崇越來越少時教師就會感到悲哀。中國是尊師重道的國家,在我們的傳統中,教師是“春蠶”,是“蠟燭”,但是近年來由于各種有違學術道德和師道尊嚴的事件頻發,公眾對高校教師的認可度持續走低,更有甚者,有批評者稱當今的高校教師沒有責任擔當,乃是“犬儒”,這些評論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都助長了高校教師群體的負面情緒。
(3)職業倦怠
Maslach和Jackson(1981)將職業倦怠定義為在以人為服務對象的職業領域中,個體的一種情感耗竭、去人性化和低成就感的癥狀,是個體長時間處于對情緒資源過度需求的環境下而產生的生理衰竭、情緒衰竭和精神衰竭狀況。教師產生職業倦怠的風險相對較高(Hakanen等,2006)。已有研究發現,教師屬于職業倦怠的高發人群(楊秀玉 孫啟林,2004),“倦怠”甚至已經成為當下教師的生存狀態(Chang,2009)。
有關教師職業倦怠的研究是教師情感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話題,國內外語界對此也較為關注,如程曉堂(2006)、張慶宗(2011)、范琳等(2017)。唐麗玲和趙永平(2013)綜合使用問卷等多種調查工具對118位西部高校外語教師的職業倦怠情況進行調查,發現這一教師群體在“情感衰竭”維度上問題嚴重,科研和晉升壓力是導致教師產生倦怠情緒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范琳等(2017)對高校英語教師進行調查,采用相關量表考察其自我概念、教學效能感、職業倦怠現狀及其相互關系,研究發現:(1)高校英語教師自我概念、教學效能感水平較高,職業倦怠水平總體不很嚴重,但其核心成分情感衰竭維度水平較高;(2)英語教師自我概念、教學效能感均與職業倦怠呈顯著負相關,其自我概念與教學效能感呈顯著正相關;(3)自我概念是解釋職業倦怠的重要變量,其教學滿意度、師生關系、自我接納、風險接受和主動性維度能夠顯著預測職業倦怠水平。
3.3 教學改革中的教師情感
情感曾一度是教育改革中最受忽視的維度之一(尹弘飚,2007)。近年來,教學改革中的教師情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如Hargreaves(1998;2000)、Schmidt和Datnow(2005)和Darby(2008)。
改革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教育中的改革可能會不斷突破原先的制度框架、組織結構、資源組合方式以及利益分配的格局,造成政策環境的動蕩”(孟憲賓 鮑傳友,2004:48),給教師帶來強烈的不確定感。教育改革從改革的動力源上可以分為內源型和外生型兩種類型:前者的改革動力源于學校內部,特別是教師群體;后者的動力主要源于政府或其他社會力量。外生型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會低估現行的做法和教育模式,將改革者自身的價值取向和觀點傾向強加于學校和教師之上,改革者與教師之間的沖突似乎不可避免。在這種情形下,許多教師從一開始就對改革方案的合理性存有質疑,隨著消極情緒的蔓延和持續,教師甚至可能有意識地采取消極的抵抗行動。Hargreaves曾于1996-2000年間主持“教學情感與教育變革”課題研究,對加拿大53名中小學教師工作相關的情感體驗進行調查研究。他的研究發現,課程變革作用于教師的情感目標,從而影響他們解讀教育改革方案的方式。
情感支持對教師理解教育改革、落實改革舉措具有重要推動作用。Schmidt和Datnow(2005)在4年之中對75名中小學教師進行了深度訪談,發現教師在宏觀層面上談論他們對教育改革的理解時,很少涉及個人的情緒感受,但一旦結合個人的課堂教學談論教學改革,他們往往會表露出明顯的情緒。改革者必須認識到,沒有足夠的情感支持,教師心甘情愿投身改革洪流的可能性很低。在外界支持缺席的情況下,教師面對教育改革容易產生多種負面情緒,導致自我效能感顯著降低,喪失職業熱情,甚至引發職業身份認同危機。Darby(2008)的研究驗證了情感支持對教師投身教改的重要性。面對改革,有些教師最初感到恐懼,但是在指導教師及高校研究者的幫助下,他們對教師角色、教師專業能力的認知和理解發生變化,積極投身改革中,有效提升了教學效果,同時也實現了個人專業發展的飛躍。
3.4 教師情感智力和情感勞動
情感勞動是社會學家Hochschild(1983)在分析服務業從業人員(比如餐館服務員、空乘人員)所從事的勞動時提出的一個概念。簡言之,情感勞動是指個體管理自身的感受以產生公共可見的表情和體態展示。教學不僅是情感實踐,更是情感勞動(Hargreaves,1998;2000),需要教師“在教堂教學及相關場合通過努力、調節和控制來表現合適的情感。而教師在進行情感勞動時必須遵循的某種特定要求、準則和規范體系,就是教師的情感規則”(尹弘飚,2009:20)。
教師普遍認同情緒管理是教師專業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合適的情感表達有利于推進教學活動,有益于在師生之間建立積極的互動關系(Liljestrom et al.,2007;Sutton,2007)。Zembylas(2005a)綜合使用課堂觀察、深度訪談以及教師情感日志等研究工具,對一位教師的教學實踐及相關情感規則進行了為期 3年的跟蹤研究。結果表明,課堂之上有不成文的情感規則,教師需要遵循這些規則,不宜在不合適的場合表達不合適的情感。Zembylas還發現,教師普遍認為在課堂上表露強烈的情緒是不專業的表現,在學生面前應當盡量表現得客觀中立。
情感具有社會文化屬性。不同的社會文化因素會衍生出不同的情感規則。Yin和Lee(2012:64)專門“探討了中國大陸環境下教師工作遵循的情感規則。他們采用半結構訪談和檔案收集的方法,獲取了29名學科不同、教齡各異、任教學校層次不一的中學教師和兼職管理者的數據,總結出以下4個情感規則:熱情投身教育、隱藏消極情感、維持積極情感以及把情感作為實現教學目標的工具”。尹弘飚(2009)提出,對教師專業實踐來說,情感勞動同時具備壓迫性和酬勞性兩個側面,理解教師的職業形象和專業規范必須將教師情感勞動的這兩個側面考慮在內。
4. 發展趨勢
縱觀過去30年的教師情感研究,理論層面上由早期的個體心理視角發展到如今的心理學視角、社會文化視角、后結構視角和生態系統視角等多元理論視角共存的局面,實證研究從探討教師整體的情感體驗到關注特定類別的情感,從闡釋宏觀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教師情感到揭示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教師的情感規則,對教師情感的理解由單一維度走向多元互動,初步構建了教師情感體驗的實然圖景。隨著學界對教師情感理解的不斷深入,研究理論基礎和視野不斷拓寬,教師情感研究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1)在研究對象上,給予中小學教師和職前教師以外的教師群體更多的關注,比如研究幼兒教師和高校教師情感體驗的特點。
(2)探討教師情感的橫向差異,比較不同教齡、學歷、職稱、性別的教師情感體驗的異同。
(3)教師情感研究的范圍不斷延伸,從關注教學過程和教育變革中的教師情感向探討教師專業發展過程中的情感體驗過渡;關注教師情感的影響和結果,尤其是科研相關負向情感與離職傾向之間的關系;如何幫助教師培養情感智力仍是教師情感研究的重要議題。
(4)辯證看待教師認知與情感的關系,探討教師情感產生的認知基礎。認知和情緒都屬于心理活動,情感是態度類活動,產生于特定的認知基礎之上。
(5)聚焦探索個體、學校以及社會、經濟、文化等宏觀環境因素如何形成“情感規則”,探討教學工作作為一種特殊的情感勞動與教師職業倦怠的關系。
(6)在研究方法方面,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相結合,群體研究和個案研究相結合,力圖在得到概括性研究結果和深入細致的研究結果之間找到平衡點。
5. 對外語研究的啟示
在過去30年中,“教師情感”已經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教師研究領域一個重要議題,但是目前針對外語教師情感的研究數量嚴重不足,國內相關實證研究尤為匱乏。教師情感研究給我國外語界的最重要的啟示是:教學是情感的實踐,研究教師情感對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教師情感應當成為外語教師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研究者需要關注不同外語教師群體的情感體驗及影響因素。目前相關研究涉及的教師群體主要是中小學教師,我國高校外語教師數量龐大,但對他們情感體驗的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女性外語教師群體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國內外語教師以女性為主,而家庭和職業中傳統的性別期望意味著女教師的教學和科研情感體驗、課堂教學的情感規則異于男性。
在研究方法論層面,目前國內教師情感實證研究大多傾向于采用量化研究方法,通過引進國外的情感測量工具、開展問卷調查,力圖得出具有概括性的研究結果。國內研究者需要拓展研究視角,融合量化和質性研究方法,更多地開展敘事研究和個案研究,推進對教師情感微觀層面的探索,深化對不同類別教師群體情感體驗的理解和認識,推動外語教師的專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