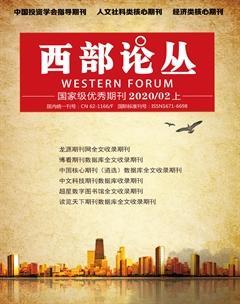意思表示解釋與審判實踐
摘 要:關于意思表示解釋的理論,一直存在著這樣的爭論:解釋應當探究表意人的內心真實意思,還是應當作出合乎理性第三人理解的解釋?而在審判實踐中,意思表示的解釋也面臨著案件事實客觀上無法還原、解釋方法紛繁復雜、當事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當事人故意隱瞞事實虛假陳述等各種情況,給審判中的意思表示解釋帶來了諸多的困難。《民法總則》第142條對意思表示的解釋作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定,雖并沒有正面回答以上問題,但強調了文義解釋的重要性,并指明了解釋的方向。
法律行為理論是現代民法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意思表示的解釋是法律行為解釋的核心。在學術界,關于意思表示解釋的爭論一直存在著,并至今沒有統一的結論。而在審判實踐中,對相關的合同條款進行解釋是每一個法官必須要做的工作。對相同的條款采取不同的方法進行解釋,甚至會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尋找一套系統的、科學的、可行的意思解釋方法對于推進審判工作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意思表示解釋的目的
目的指導著行為的最終方向,出于何種目的對意思表示進行解釋,可能最終影響意思表示的最終結果。在法學理論界一直存在著關于意思表示解釋目的的爭論,傳統觀點認為意思表示解釋的目的是為了探求當事人的內在意思,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解釋與表意人意思之探尋無關,而與表示的意義的查明有關”,“解釋的目標就是確定表示所蘊含的意義,而且在表示的眾多可能的含義之中,確定那個剛好被法律認為是具有決定性的含義”[1]。此種觀點提出解釋的結果應當是理性第三人所能理解的含義。這兩種觀點幾乎截然相反,在實踐過程中也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
其實兩種觀點都有其道理。但是若是細究,會發現其實兩方都存在著不同的缺陷。盲目追求對表意人內心真實意思的探究,則對相對人有明顯的不公,對于信賴利益將無法保護。而如果單純考慮相對人的信賴利益,盲目追求客觀地解釋,則有可能將表意人至于不利之地。那么是否存在一種合理的、折中的,更加妥帖的做法呢?這值得我們在實踐中去探索。
二、審判實踐中的意思表示解釋
除去當事人對案件事實沒有爭議的案件,大部分當事人對案件事實有爭議的案件,尤其是合同類糾紛,都可歸結為意思表示解釋的糾紛。對合同相關條款進行解釋,是每一個法官必須要做的事情。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審判過程中對意思表示解釋進行解釋,并確定其最后的內涵和外延,要比單純在學理上討論意思表示的解釋要復雜得多。
一是客觀上還原案件事實的不可能性。每一個審判案件都是對過去的事實進行探究。合同是雙方意思表示達成一致并表示共同遵守的契約,在合同成立時,雙方的意思表示應當是明確而唯一的。但是,當糾紛發生時,合同簽訂時的意思表示已經成為了“過去式”,我們只能通過現存的合同條款以及其他相關的“意思表示的遺存”來窺視當初發生的事實。這些“遺存”可能是一紙欠條,也可能是一段錄音、一張圖片、一種交易習慣,但是不管是什么,都無法完整地真實展示過去發生的事實。對于法官來說,他所能認定的事實,僅僅是法律上的事實,而不是真正的事實。
二是不同的意思表示解釋方法的適用紛繁復雜。意思表示解釋的方法有許多,包括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習慣解釋等,在審判過程中不同解釋方法的運用甚至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三是當事人的疏忽大意導致合同未能考慮周全,意思表示的解釋更多地偏向漏洞的填補。在意思表示解釋的理論上,不管是探尋內心真實意思的主觀解釋說,還是注重外在表示形式的客觀解釋說,其實都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設上。主觀解釋說認為,一個成年人有能力判斷自己的處境并做出合理的行為處分自己的權利,這也是私法自治的基礎;客觀解釋說則認為,一場交易行為中,交易人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相對人是一個能夠通過他人行為做出足夠客觀地判斷的人。可惜,在審判實踐中,在矛盾發生時,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理性人”,有無法認識到自己的行為的真實含義的人(這種錯誤認識就表意人本人而言可能存在過錯,也可能不存在過錯),也有對他人的行為做出錯誤的判斷并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的人。這就對法官的解釋工作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一個審判法官可能需要在一些本來就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的遺存”上解釋出合理的結果,并對瑕疵的后果進行公正的分配。
當事人因為內心意思與外部表示不一致,或意思表示不自由,導致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由于意思表示代表法律行為效力的核心要件,代表著公民意思自治的基本權利,因此從《民法通則》到《民法》再到《民法總則》以及業已通過等待生效的《民法典》,對于因意思表示不自由(欺詐、脅迫、重大誤解)而產生的瑕疵,法律都從法律行為的效力上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對于不涉及合同效力問題的意思表示瑕疵,一般來說可以通過漏洞的填補來實現,這也是意思表示解釋一種。
三、《民法總則》第142條的回應
在《民法總則》出臺之前,關于意思表示的解釋的內容主要規定在《合同法》內。《合同法》第125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合同文本采用兩種以上文字訂立并約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對各文本使用的詞句推定具有相同含義。各文本使用的詞句不一致的,應當根據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釋。”此為關于合同條款的解釋,但是并沒有完全覆蓋全部意思表示的解釋。
《民法總則》對意思表示解釋則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第142條規定:“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應當按照所使用的詞句,結合相關條款、行為的性質和目的、習慣以及誠信原則,確定意思表示的含義。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詞句,而應當結合相關條款、行為的性質、行為的性質和目的、習慣以及誠信原則,確定行為人的真實意思。”仔細對比理解以上兩個條文,我們不難發現以下幾個結論。
一是現行法律并沒有回答“意思表示解釋的目的是什么”,也沒有明確回答應意思表示解釋究竟應當努力探究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還是追求客觀的解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表意人內心意思表示的重要性。《民法總則》第142條對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和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進行了區分,在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中,用的是“確定意思表示的含義”的表述,而對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則采取“確定行為人的真實意思”的表述。
有觀點認為,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因為沒有相對人,所以并不存在相對人的問題,因此意思表示的解釋就是探究表意人的內心真實意思,不必考慮客觀情況。我認為,此種觀點考慮欠周。一方面,從事實上來說,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雖然沒有相對人,但是也會引起法律關系的變更,任何法律關系的變更都會引起社會利益的再分配,完全不考慮客觀情況是不合理的(比如在拋棄中存在先占的問題,在遺囑繼承中也涉及到繼承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從邏輯上來說,“確定行為人的真實意思”,并不能當然反向推出不需要考慮客觀情況和利益相關者的信賴利益。
二是現行法律對各種意思表示解釋方法并沒有作優劣之分,對適用的順序也沒有作出規定,但將可供選擇的解釋方法進行了羅列,注明解釋的注意事項,并將文義解釋放在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合同法》與《民法總則》均表述為“應當按照所使用的詞句”)。此處對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和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也進行了區分。在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中規定“應當按照所使用的詞句”,在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中則強調“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詞句”。
有觀點認為,《民法總則》對有相對人意思表示的解釋和無相對人意思表示的解釋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規定。我覺得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首先從文字邏輯的角度進行理解,規定“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詞句”并不能當然推出“按照所使用的詞句進行解釋是錯誤的”的結論,規定“應當按照所使用的詞句”也不意味著就要拘泥于文字。其次,語言文字具有多義性,按照所使用的文字進行解釋同時不拘泥于文字地進行解釋并不矛盾。再次,文字是人類使用的最基本的表達工具,在采用文字作為意思表示載體的時候,文字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最直接的表達和記錄,并且文字本身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其含義也不會在短時間內發生巨大的變化,這就是文義解釋的正當性基礎。在這點上,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和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來說并沒有太大的差別。最后,從整個民法體系來看,《民法總則》第146條規定虛假表示并不影響隱藏行為的效力,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解釋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解釋不一定要拘泥于文字。另外,在學術上也早有“誤載不害真意”的理論共識。因此,無論是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解釋還是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解釋,都應當從文字出發解釋,但不完全拘泥于文字。《民法總則》第142條在行文上作出完全不同的表述,更多地是出提示的需要,強調在具體操作上,解釋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和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整體上來說第一款和第二款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四、審判中的意思表示解釋探析
意思表示解釋在審判過程中更具有復雜性,《民法總則》第142條雖然未作出十分明確的規定,但是卻給我們指明了正確的方向。結合相關理論學說,在審判過程中的意思表示解釋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改善和突破。
一是在解釋方法的運用上,意思表示的解釋必須以文義解釋為基礎,再綜合運用其他解釋方法。在上文我們已經分析過,現行法律對于文義解釋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并且《民法總則》第142條的第一、二款在對待文義解釋上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在具體的審判實踐中,法官應當先用文義解釋的方法對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當文義解釋得出多種結果得時候,再運用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方法在文義解釋所得的結果中進行篩選。 文義解釋的結果包括文字的通常具有的一般含義和可能具有的其他含義,所謂不拘泥于文字表述,亦不能超過文字可能具有的其他含義。即,意思表示的解釋要始于文字,并終于文字。
二是在意思表示解釋的原則上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同時兼顧表意人內心真實的意思表示和相對人信賴利益及交易安全的維護。文字的多義性和現實生活的多樣性,使得在意思表示的解釋過程中,即便采取文義解釋,我們也可能獲得完全不同的結果。當文義解釋的結果出現分歧時,如果單純追求表意人的內心真實表示,則對領受人不公平;若純粹采取客觀的解釋方法,則對表意人的利益缺少合理的保護。以意思表示為核心的法律行為是實現私法自治的重要手段,人們通過觀察他人的法律行為對自己的生活、生產、交易進行預先的安排。意思表示“意思”和“表示”的雙重性質決定我們必須選擇一個能夠兼顧表意人和領受人的解釋方法。
三是在審判實踐中應當堅持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對合同條款進行解釋雖然是法官的職責,但是并不能免除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具體來說,當當事人對文義解釋的結果有異議主張超越文義的含義時,原告應舉證證明;當表意人主張自己確實屬于意思表示錯誤,不應當對自己的表意行為負責時,也應當承擔舉證責任;同理,當受領人主張自己確實已經盡到注意義務時,也應當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的分配應當堅持以誠實信用原則為引導,并綜合考量雙方的利益。
注 釋
[1] [德]卡爾·拉倫茨:《法律行為解釋之方法——兼論意思表示理論》,范雪飛、吳訓祥譯,法律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第2頁。
作者簡介:何亞江(1989一),男,臨海市人民法院,浙江臨海,漢族,浙江臨海人,學士,法官助理,研究方向: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