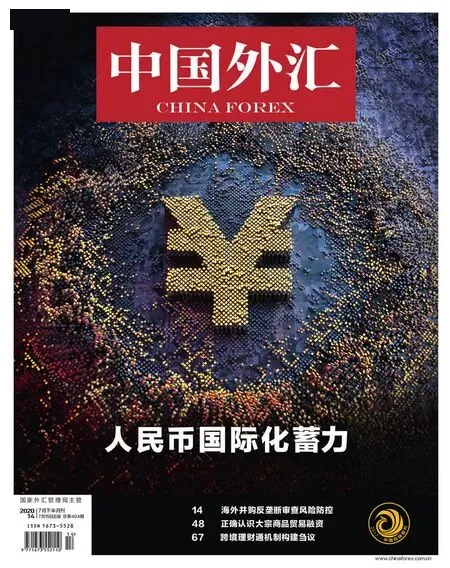應進一步注重匯率政策協調
近一段時間以來,在世界經濟前景并不樂觀的背景下,市場對于應采取何種貨幣政策進行應對的討論持續引發關注。對此,筆者認為,面對當前形勢,還有一個因素十分重要,應予以重視,即匯率政策協調。當前經濟增速回落和價格水平承壓是一個全球現象,背后的共因是2013年以來的強美元。面對這種局面,如果僅是采取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則可能事倍功半,且副作用巨大,這也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的深刻教訓;而如果各國能采取匯率政策協調,則可能事半功倍,帶動全球經濟走出停滯狀態。
首先,新冠疫情沖擊只是加劇了全球深陷長期停滯狀態的風險,強美元才是導致全球經濟前景萎靡的根本原因。2013年以來,美元實際有效匯率較此前上升了11%,從以下六個方面導致全球陷入低增長和低通脹的長期停滯狀態:一是強美元對美國經濟產生收縮效應,壓低美國的增長速度和通脹水平。根據美聯儲的估算,美元有效匯率上升10%,會導致美國GDP增速每年平均少增長0.5個百分點。二是強美元壓低了大宗商品價格水平,對全球低通脹有直接作用。三是強美元導致國際貿易融資積極性下降,全球產業鏈貿易由盛轉衰,拖累多國的貿易和經濟增長。四是美元走強使得新興經濟體貨幣匯率下跌的壓力增大,陷入貨幣危機的風險上升,投資受到抑制。五是強美元使得土耳其等商品國家的經濟基礎動搖,國家風險上升,增長前景惡化。六是強美元加大了國際資本流動的波動性,抑制國際資本在各國之間的流動。
其次,面對強美元對世界經濟產生的負面效應,加強國際間的匯率政策協調具有重要作用。1985年的廣場協議是匯率政策國際協調的經典案例,可以從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為中國當前的政策選擇提供借鑒。
從經驗的角度看,美國的實踐表明,國際匯率政策協調的政策效果明顯且副作用小。通過廣場協議的匯率政策協調作用,美元有效匯率從高點回落了30%左右。約兩年時滯后,美國的貿易失衡情況好轉:1987年美國的貿易赤字達到峰值的1520億美元,1991年這一數字回落到300億美元。貿易狀況改善后,美國退出了貿易保護主義,結束了與日本等國的貿易爭端。而伴隨美元的轉弱,不僅美國進入“新經濟”狀態,世界經濟增長也從1985年低點的3.6%連續三年反彈至4.6%。這意味著弱美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增長。
從教訓的角度看,日本的失誤在于,沒有通過匯率政策協調來應對廣場協議之后日元過度升值產生的收縮效應,而是采用了副作用過大的寬松貨幣政策。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危機從表面看是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升值過快導致的,但事實上則是由于日元過度升值抑制了通脹上升,而日本對于資產價格泡沫與宏觀杠桿率之間的關系缺乏認識,采取了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日本企業部門杠桿率從1985年至1990年提升了30個百分點,居民杠桿率從1985年至1990年上行了16個百分點。換言之,日本的教訓恰恰是只注重國內貨幣政策寬松,忽視了通過國際匯率政策協調改變上世紀80年代末日元過度升值的狀況(1987年的盧浮宮協議執行效果不佳,由此可見匯率政策協調這個“靈丹妙藥”由于種種非經濟原因非常難以獲得)。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曾在2004年《日本匯率政策失敗所帶來的教訓》一文中強調,“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當時政府的經濟政策失誤。”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經濟增速和通脹水平的下行,不僅僅是國內因素所致,強美元產生的收縮效應亦具有重要影響。應對當前形勢,通過國際間的匯率協調可能事半功倍;而如果僅采取國內的寬松貨幣甚至赤字貨幣化,則難免推高資產價格,甚至有可能重蹈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泡沫危機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