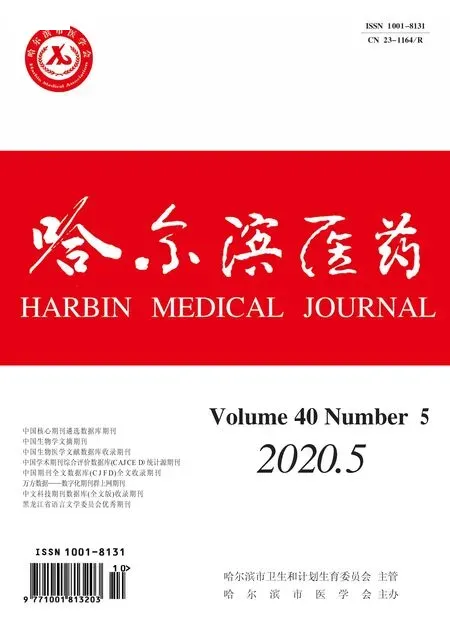髓源性抑制細胞在胃癌發生發展中的作用與應用
屠妍霞 陳 光
(臺州學院醫學院,浙江臺州,318000)
胃癌是全球發病率第五的惡性腫瘤,為第三大常見死因。研究表明,地域差異對胃癌發病率有較大影響,發展中國家約占70%,東亞約占50%,中國的發病率尤其高,且性別差異導致男性發病率約為女性的2倍[1]。胃癌的分子分型,目前按照“癌癥基因組圖譜(TCGA)”項目(2014)將胃癌分為四種基因組亞型:染色體不穩定型(CIN);微衛星不穩定型(MSI);基因組穩定型(GS);Epstein Barr病毒相關型(EBVaGC)。繼手術、化療、放療和分子靶向治療后,療效顯著持久且副作用較小的免疫治療成為胃癌最有前景的治療策略之一。
腫瘤微環境由癌細胞和基質/免疫細胞組成,如癌相關成纖維細胞(CAFs)、內皮細胞、M2型腫瘤相關巨噬細胞(M2-TAMs)、髓源性抑制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和調節性T 細胞(Regulatory cells,Treg),是妨礙常規治療的因素之一[2]。由此對MDSCs在胃癌發生發展中的相關作用研究作一綜述。
1 MDSCs
髓源性抑制細胞(MDSCs)是由未成熟的、無法分化為粒細胞、巨噬細胞和樹突狀細胞的髓系祖細胞組成的異質性群體,是一種免疫抑制性先天細胞群[3]。MDSCs通過多種機制抑制腫瘤微環境中的先天免疫和適應性免疫,包括高表達的精氨酸酶1(Arg1)、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NADPH氧化酶2產生的活性氧和氮物種,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的表達以及半胱氨酸的消耗等[3]。
MDSCs激活Treg和M2-TAM并促進其增殖,通過抑制效應性T細胞的增值和功能因子的釋放等機制削弱T細胞的抗腫瘤效應和NK細胞的活性[3],介導腫瘤微環境中免疫逃避。
2 MDSCs阻斷胃癌腫瘤免疫的機制
2.1 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家族:與胃癌相關的基因FGFR2、CSF1R、EVGFR2等參與組成FGFR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