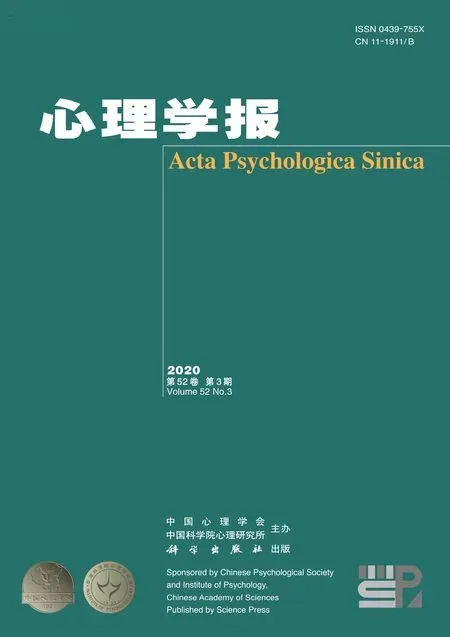中國神話中的具身心理學思想探索*
蘇佳佳 葉浩生,2
(1廣州大學教育學院; 2廣州大學心理與腦科學研究中心, 廣州 510006)
1 引言
心理學發展至今, “具身認知”的出現終于可以讓心理學者們預見中西方心理學對話和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心理學的最大可能。隨著強調人類認識世界中“計算”與“表征”作用的“第一代認知科學”的日漸式微, 以關注身體在認識世界過程中作用的“第二代認知科學”逐漸崛起(李其維, 2008), “具身認知”學術研究之風日益強勁(Shapiro, 2019)。縱向推演, 具身認知理論建構路徑之節點有三:自重申身體于認知歷程乃不可化約的本原角色, 到身體于認知之作用不僅僅是因果角色更是構成角色, 再到認知是大腦嵌入身體、身體嵌入環境的動力系統的角色(葉浩生, 2019)。簡言之, 具身認知強調身體對心智的塑造, 認為心智并非一種可以“離身” (disembodied)的符號加工; 而是身心一體、互為因果和相互糾纏(Wilson & Foglia, 2015)。西方“具身認知”思潮涌入中國以后, 中國的具身認知研究如火如荼(何靜,2014; 李海峰, 王煒, 2015; 魏華, 段海岑, 周宗奎,2018; 楊雅琳, 楊偉星, 張明亮, 司繼偉, 2018; 張帆, 袁芯, 盧葦, 2019), 且國內很多學者在致力于將西方“具身認知”思想本土化方面進行了多維的寶貴探索(張兵, 2016; 黎曉丹, 杜建政, 葉浩生,2016; 苗小燕, 張沖, 2018), 但在西方話語權力和敘述文本的宰制下也暴露出諸多“思想轉嫁”的文化背景問題。
西方“具身認知”心理學思想與賦存在中國文化里的以“天人合一”為核心的“體知” (杜維明,2002, p.343; 黎曉丹, 葉浩生, 2015, p.707)心理學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然則中國古代文化又有著獨有于西方文化的“身體”元素。依文化之視角, 我們可以預見中西方心理學對話的最大可能。“倘欲究西國人文, 治此則其首事, 蓋不知神話, 既莫由解其藝文, 暗藝文者于內部文明何獲焉” (魯迅, 1981,p.30)。文化的源頭就是神話, 欲真正追溯中西文化相通相異的釋源性之因, 神話當屬首位。其中創世神話實為神話之主體(謝·亞·托卡列夫, 葉·莫·梅列金斯基, 1993, p.3)。美國學者杰克·波德曾言道“中國沒有創世神話”, 此言激起千層浪, 經由眾位中國神話學者搶救性保存、挖掘和整理神話史料, 中國神話匱乏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鐘敬文, 1992,p.2), 而今已然形成了“創世神話大發現”的繁榮之象(烏丙安, 2009, p.9)。現重新梳理尚存在世的上古創世神話, 當我們在慨嘆何以古人能想象出如此波瀾壯闊的神話畫卷時, 一個不可回避的神話母題矗然立于我們面前, 即, 為什么上古創世神話幾乎都與“身體”緊密相聯, 尤其是中國以取諸自身為特點的身體創世神話(章立明, 2013, p.30)。中西創世神話中“身體”的“同”在哪里?中國神話中“身體”可貴在哪里?中國神話中的“身體”之于中國心理學又有何種意義?
本文希望藉由中國神話之身實現三個目的:一是希望能為心理學的“綜合科學取向”發聲; 二是希望能為心理學的“整合之路”貢獻中國具身心理學思想的力量; 三是希望能為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科學的具身心理學提供理論建構與研究范式的啟示。
2 神話的身體生成觀:本體論維度
魯迅(1973, p.8)將神話界說為, 天地變化多端、萬物難以恒常, 因人力難以解釋此玄妙世界, 太古初民故將“神思”進行“人化”而創造了神話。那人化是如何表現神思的呢?欲說明這一點, 便不能不提及梅洛·龐蒂的“意向性”概念(梅洛·龐蒂, 2001,p.13), 此概念是西方具身認知思想的哲學基礎之一。費多益(2010, p.15)將西方“embodied cognition”譯為“寓身認知”, 有“心寓于身”的“身心一元”之義。換言之, 所謂“意向性”的根本寓意就是“身體意向性” (梅洛·龐蒂, 2001, p.138), 即“身體”是本體,身體能動地進行思維, 身心是一元的。李恒威和盛曉明(2006, p.184)以生成論視角闡述, 認為“知”必以寓于環境中的“身”為根基, 故而認知起源于身體(身體結構、身體活動、身體圖式等)。另一層涵義是“運動意向性” (梅洛·龐蒂, 2001, p.150), 即“身體”是運動的, 身體能動地進行行動, 身體具有多種可能性。認知的意義一定是跟身體的行動相聯系的, “知覺存在于知覺引導的行動” (F.瓦雷拉, E.湯普森, E.羅施, 2010, p.139)。言簡意賅, 人的本體論意義是在身體的行動中存在, 沒有脫離身體的認知,更沒有脫離身體行動的認知。因此, 人以“體認”的方式認識世界, 更以“體認”的方式創造神話, 身體是神話形成的唯一母體。
國內神話研究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茅盾(1981,p.163)曾言道, 遠古人雖思想原樸, 卻偏偏有勇氣去攻擊那些直指人生終極意義的巨大問題, 譬如,天地、萬物與人類究竟緣何而來又將往何處。自人類誕生伊始, 這些人生終極問題就一直縈繞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對于這些問題的答案便是我們的原始神話。如在美洲文明中, 北美印第安人神話記載,宇宙萬物的產生是源于造世大神 Belmaruduk斬妖怪 Omoroca為兩段, 并以尸身創造(茅盾, 1981, p.37)。在歐洲文明中, 北歐神話中的世界巨人 Ymir是被冰巨人三子神所殺, 其中奧定(Odin)將伊密爾尸身造為天, 其肉為大地……腦為云(茅盾, 1981,pp.39?40)。而在亞洲文明中, 日本《古事記》記載,伊邪那岐命拔劍斬其子迦具土神的首級, 死后的血迸濺巖石而生諸神, 其母伊邪那美命身體各部分也化為雷神八尊等(安萬侶, 1990, pp.9?10)。印度《摩登伽經》相傳:“自在梵天以頭為天, 足為地……大小便瀝為海”。若將世界各民族上古創世神話進行比較, 可發現創世之始, 未有一切之先, 神創世的材料只能是神的身體, 世界問題肇始于身體問題。其中, 最具中國特色的是, 在創世神話中, 華夏原始初民是以自身獨有的“近取諸身” (《周易》)的思維方式去認識天地開辟、萬物肇始和人類起源的。
舉天地開辟神話為例, 華夏身體創世大神與承襲于希伯來神話的“上帝創世”之別是眾所周知的、顯而易見的。于人類對天地起源的發問, 《圣經》舊約開篇即言道:天地乃神創。一開始就界定了神的存在, 神是不可追問的終極存在。且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神說:“要有天地”, 于是就有了天地。這樣神就造出了世界。可見, 《圣經》“創世說”中所有動詞都忽略過程而只強調結果, 即西方創世神話中的宇宙并不是發端于上帝的“身體”, 世界的形成只是源于上帝的意志而已, 上帝、天地、萬物、人類不具備一體的可能性。這種明顯的神人分際觀念可以看作是希臘文化主客二元思想發微的由來。自此開始, 西方心理學也一直秉承希臘文化的“主客二元論”思維模式, 由假設概念出發, 重視明確的認識論(馮友蘭, 2004, p.21)。與西方迥然相異的是, 中國的開天辟地神話強調“身體”作為本體論的特色。如華夏宇宙開創是以盤古“身軀”變化而成,《繹史》卷一引《五運歷年紀》載曰“首生盤古, 垂死化身……齒骨為金玉, 精髓為珠石, 汗流為雨澤”。盤古開天辟地神話展現了原始初民已然意識到人身難得, 并且可將身體的力量用于改造自然之理。由此可見, 中國的“心的活動”寓于“身的基礎”,“身心一體”, 而且以“生”為訓, 即中國的“身體”是活的, 身體的真正蘊義是存在于主體之于客體的動態生成過程之中的(張再林, 2006, p.11)。值得考究的是, 補天神話在世界創世神話之林中獨樹一幟,為世所罕見(陶陽, 鐘秀, 1989, p.42)。《淮南子·覽冥訓》記載女媧是如何煉石補天的, “往古之時, 四極廢, 九州裂……鷙鳥攫老弱”。民間相傳, 補天的石頭缺了關鍵的一塊, 這時, 女媧竟以自己的身體變化之, 并最終化為無實體的神靈與天同壽。以今人視野解釋之, 由“以身化石”可推知“心”納于“身”,以“身”馭“心”, “身”“心”一元, 此外, 更可推出華夏兒女獨有的“以身殉天下道” (《孟子·盡心章句上》)的大無畏精神。西方現象學家梅洛·龐蒂之于身體的理解與中國幾千年前對身體的理解幾乎如出一轍,在西方身心二元論的危機下, 他也試圖將身體擢升至本體論的位置上, 即將西方的“靈”與“肉”重組為“身心合一”的“身體”, 主張“靈魂和身體的結合每時每刻在存在的運動中實現” (梅洛·龐蒂, 2001,p.125)。而濫觴于神話, 中國文化一直沿循著獨有的“身心一元”哲學理念, 誠如郭沫若《爾雅·釋言》所言“身, 我也”, “我”字既包含“身”也包含“心”, 同時, “身”具有“心”的力量。一言以蔽之, 中國的“身體”具有主體的力量。
舉人類起源神話為例, 中西方神話都盛傳人是由神用泥土所造, 但中國的造人神話卻有著獨有的中國“身體”的繁衍特色。因循時間線索, 西方人類起源神話中, 希臘神話在前, 圣經神話隨后。希臘神話記載, 普羅米修斯依神之模樣以濕土塑人形, 并于動物靈魂中攝善惡二性, 并加以女神雅典娜所吹取的神氣, 使人終獲生命(陶陽, 鐘秀, 1989, p.225)。大同小異, 《圣經》上亦說, 上帝用大地之土造人形, 亦吹取神氣, 使亞當獲生, 而夏娃則生于亞當的肋骨, 人類祖先乃從此二人出。兩者相互對觀,西方的造人神話中有其通性, 即神只是負責創造人的身體和靈魂, 神人并不同形, 神的身體與人的身體并不發生任何“身體”的聯系。而中國人類起源神話則介紹了鴻蒙之初, 人由神的身體所出。“俗說天地開辟, 未有人民, 女媧摶黃土作人, 劇務, 力不暇供, 乃引繩于絙泥中, 舉以為人” (《太平御覽》),并且女媧大母神本身也生于黃土, 屈原《天問》曾疑:“女媧有體, 孰制匠之?”, 后人解釋女蝸實乃地母, “女媧地出” (《抱樸子·釋滯》)。典有明征, 因此女媧是用造自己的材料來造人的, 人與神在“身體”上是同質的。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 在經歷了大洪水之后, 圣經神話是正常人類再傳, 只有中國神話是伏羲女媧“兄妹婚配”來延續后代的(陶陽, 鐘秀, 1989, p.232)。圣經載曰, 神見世人行惡于大地之上, 于是欲以洪水毀滅人間另造新世。當時之世界, 只有諾亞行義人之事, 蒙恩于神前。故神命諾亞一家人進方舟避洪水, 再度繁衍如常。而中國神話典籍《獨異志》云:“昔宇宙開初之時, 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昆侖山, 而天下未有人民……天若遣我二人為夫妻……于煙即合”。以哲思辨之, 伏羲女媧兄妹婚神話中的男女并非是兩種獨立的元素以兩種獨立的性質相結合, 乃是作為一種“關系”的喻指,來表達男女作為本體結合使生命得以產生的一種純粹性關系, 即生命生發于關系之中, 而非元素使然。這種關系即為中國傳統文化里的“感”。《易經》中, “感”為其不二法門。古文中“感”字與“咸”字是互通有無的, 且為人倫之始。《序卦傳》曰:“男女之道, 不能無感也, 故受之以咸。咸者, 感也。相感則為夫婦”。如是之故, 易經的“感”不僅為我們推出了“男女感應之道”的“身本位”的本體論, 而且還為我們端直推出了“造端乎夫婦”的“家本位”的倫理觀(張再林, 2007, p.53), 即身體?兩性?家國的“差序格局”的中國社會觀(費孝通, 2008, p.25), 從而使萬事萬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成為可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系辭上傳》)。從中國身體本體出發, 身體可延伸至男女, “身體發膚, 受之父母”中“父母”即為“男女”的別稱; 而“陰陽”又是“男女”所衍生之物,因“至陰生牝, 至陽生牡” (《淮南子·墜形訓》)中祖、妣二字與“男女”亦為異名同義(《釋祖妣》); 老子言:“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故陰陽與道又乃是不二之物; 終, 道與身體又合流于同一, “即身而道在” (王夫之語)。此種解讀文本蘊涵了一條中國式哲學的閉環路徑, 身體?男女?陰陽?道?身體。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里明明白白只存在一個身體。中國的“身體”就是道。
舉萬物肇始創世神話為例, 中西方神話都認為神創造萬物, 但中國創造萬物神話又有著自己獨有的“身體”的能動特色。希臘神話中, 起初天地混沌未分, 皆因愛神將利箭射入大地, 花草鳥獸等萬物才得以在大地上衍生; 圣經載曰, 上帝在第三天到第六天讓萬物生長, 并讓日月星辰、魚鳥蟲獸也各司其職。如此這般, 上帝以“命令”的口吻即完成了“創造萬物”這一巨大工程。而中國古籍多載創世大父神盤古和創世大母神女媧是萬物之主。如“盤古氏, 天地萬物之祖也” (《述異記》), 許慎《說文》亦言:“媧, 古之神圣女, 化育萬物者也”。另有漢文古籍中的日月起源神話亦可證明神與物的親緣關系, 如《山海經·大荒南經》:“羲和者, 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經·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 生月十有二”。盤古、女媧以身化萬物以及神生日月等神話, 都表現了華夏初民認為萬物也是經由神的身體生發的, 與西方以“神物分野”為特征的上帝意志造物大相徑庭, 中國的神并不是像西方圣經中的上帝那樣是絕對至上的形而上的存在, 因此, 神、人與萬物實為同宗同源, 而“身體”則為本源。在自然這個巨大的生命社會里, 人并非萬物之靈長, 人、動物與植物等萬物實處于同一維度, 并無高下左右之別(恩斯特·卡西爾, 2013, p.106)。值得深究的是,上古民族中, 射日神話也是具有中國元素的獨特神話(陶陽, 鐘秀, 1989, p.199)。勘察史料, “堯之時,十日并出, 焦禾稼……” (《淮南子·本經訓》), “羿射九日, 落為沃焦” (《山海經·秋水》)。大羿不忍十日破環人間生息, 故射殺九日。此中可得, 中國太陽起源神話中, 神與太陽是同一的, 神的身體即太陽的身體, 同時, 人的身體亦來源于神的身體。而“后羿射日”, 人的身體可以射殺神的身體, 故而“身體”可以具有兩種不同的身體意向與行動指向。中國傳統文化里, “身”為第一人稱, 與西方哲學把“身”當做第三人稱不同。《說文》:“身, 躳也”。躳躬同義, 強調躬身踐行, 體驗為重。造字之時, 古人就把“活”義寄寓于“身”字當中, 身體具有主觀能動性, 此中可管窺一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論語·學而》), 即通過反思身體來認識自身, 身體在這里俱生有“忠”、“信”和“恒”之主觀意志。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 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孟子·盡心上》), 即通過窮究自身以臻體義明理, 身體在這里具有了“格知”之蘊義。荀子曰:“篤志而體, 君子也”《荀子·修身》, 即通過事必躬身以踐行胸中大志向, 身體在這里也有了“圣人之風”、“君子之骨”。故《存人編》也謂:“吾身之百體, 吾性之作用也”。概而言之, 中國的“身體”具有意志。
以上, “神話”實為“人話” (金城, 1986, p.76)。正如袁珂先生(1998, p.6)所說, 神話并非來自于形而上的“玄思”, 而是源于形而下的“體悟”, 遠古初民是憑借根植于勞動過程中的具體的身體經驗來創造神話的。用具身認知的術語來講, 就是從身體感覺——運動體驗出發來闡述思維過程。所謂“創世神話”亦可稱之為“身體神話”, 且張開焱(2014, p.6)稱中國創世神話的特色為世界祖宗型神話, 取創世神與祖宗神合一之義。與西方相比, 中國神話中的“身體”是真正“天人合一”的本自具足的身體, 與西方在上帝視角下重新回歸身體的“身體創世神話”有著不同的獨立生存空間。以中國獨有的補天神話、洪水婚配神話與射日神話為例, 可見中國的“身體”即是“道”, 身體具有“力量”, 同時身體也具有“意志”。簡言之, 西方的本體論哲學注重靜態的體用關系, 認為現象與實體是“自然二分”的兩個概念,而中國哲學向來只關注動態的“本末關系”, 即中國哲學的本體是萬物存在的根本并通過行動而顯示其存在的意義, 如樹根與樹干是一個非二元對立的生命整體。大道至簡, 一元論即中國的“身體”確有“身心共存”之蘊義, 身心互倚, 相待以生又俱生俱滅, 身與心合而為一, 并最終上升到永恒的本體論維度。
3 神話的身體現象觀:空間維度
先前, 神話研究一直是神話解釋學的天下, 但在現象學運動日漸深入的今天, “神話現象學”開始掌握了話語權。神話解釋學其思想基礎是孔德的實證主義, 即解釋不是自下而上從事實本身歸納得出的, 而是自上而下從現成的解釋演繹而來的(列維·布留爾, 1981, p.9), 而神話現象學其思想基礎是胡塞爾的“現象學”, 現象學者期望的“解釋”是“在事實本身中”獲得的(王懷義, 2015, p.43)。“現象學”式的創世神話解讀與西方那種宏大敘事的“羅格斯式解讀”實為南轅北轍, 在現象學里, 能指和所指的聯系絕不是固定的, 大腦、身體、環境是“三位一體”的活態系統。神話“遠取諸物”的身體現象學觀可參考“概念隱喻理論”, 人類最初認識世界之時,就是從自身的身體結構、空間位置和運動圖式開始的, 即通過自身和外物方位的上下左右、前后遠近、中心邊緣的關系來表達對事物的認識(Lakoff &Johnson, 1980)。瓦雷拉(2010, p.139)等人認為, 具身認知有一種含義是認知根生于身體的感覺運動系統, 身體的感覺運動系統本身又嵌入于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場域中, 被生物環境、心理環境和文化環境所形塑。在這里, 身體作為一種“可能活動的系統”, 即身體不止是單維的物理層面的肉體, 更是與周圍多維世界發生關系的媒介。在中國神話的語境中, 始終把人與自然、萬物、神這四者看作是一個有生命的活的“精神統一體”。
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即是以“身體本體論哲學”為源頭, 并以“依形軀起念” (唐力權, 1990, p.81)的思維方式來認識這個世界, 即“喻指”是人所賴以生存并認識本體的重要發明(Mark, 1980, pp.3?6)。且更為重要的是, 東方思想所獨有的一大特色即是隱喻思維的發達, 尤以中國傳統思想為巨擘(黃俊杰,2006, p.31)。《易·系辭傳》中說:“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 中國哲學家常“以身為喻”對事物展開各種論述。如“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易傳》), 在“身體”的視閾下, “太極”即本體乃以人身為原點, “兩儀”即空間乃為人身俯仰觀察之場域, “四象”即方向乃為身體可能朝向的“東西南北”方向, “八卦”即圖式是“身體意向性”的多種“可能性”的圖像顯示(張再林, 2005, p.29)。易經思想傳承至儒家遂以“圣人踐形” (《孟子·盡心上》)的古訓作為中國人獨有的世界圖式, 實際上就是一種從人的行為中展開的“身體圖式”。正如梅洛·龐蒂(2001, p.166)所說, 身體就是一種“為身體而成為身體的多種方式”, 身體可以在千變萬化的環境里應用不同的身體圖式, 身體圖式具有多種可能性, 但是身體本源卻只有一個, 人以自己的“身體”為中心,以不變應萬變。因此身體的現象學場域并不囿于固定的思維方式。
以物我同一的角度觀之, 人與萬物本為同根生,不應起分別之心。首先, “女媧造人”神話一直以“人從土出”說法傳世, “女媧摶黃土作人” (《風俗通》)。另外, 漢傳神話亦傳大禹和其子啟也都是石生之子,“禹生于石” (《淮南子·修務訓》), 《絳史》引《隋巢子》云:“涂山氏見之……石破北方而生啟”。這種認為人類生于外物的“人的擬物化”觀念表明人與外物的聯系密不可分。其次, 有“玄鳥生商”的故事, “見玄鳥墮其卵, 簡狄取吞之, 因孕生契” (《竹書紀年》)。《莊子》書中的一些圣人其實也是神鳥之化身, “鳥莫知于鷾鴯……而襲諸人間, 社稷存焉爾” (《莊子·山木》)。這種認為人類生于動物的“人的擬獸化”觀念也表明人與動物的聯系密不可分。最后, 如“黃帝母附寶……感而孕” (《初學記》引《詩含神霧》), “太昊庖犧之母……意有所動而生太昊”(《太平御覽》)。古人看來, 黃帝、太昊等圣人皆是“感生”神話, 屬于無性生殖。這種認為人類生于自然現象的“人的擬象化”觀念也表明人與自然現象的聯系密不可分。由此可見, 古人實則并不認同“人類是萬物之靈”, 而是把自然、自身看作是難舍難分的整體(鄧啟耀, 2005, p.59), 才能從自身感應萬物, 創造出種種“物我合一”神話。梅洛·龐蒂(2001,p.441)認為“身體是朝向世界的運動, 因為世界是我的身體的支撐點”, 人的身心關系依賴于身體的主體性, 身物關系則依賴于身體的廣延性, 廣延即隱喻, 以身為喻, 外物被納于己身, 人渾然與物同體。
以天人交感的角度觀之, 天人相勝亦相知, 即人與天地共呼吸同命運。首先, 古人善用自己的想象心理來指代外界自然環境。如南北朝民歌“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都是初民們憑他們住原始帳篷的生活經驗, 并加以天真的想象, 對天圓地方認識的反映。《列子·湯問篇》記載的“負地龜神話”與烏丙安先生的“地震魚”觀念也是原始人的類比思維的生動表現。古人“太陽運行”的神話也有類似特點,一說太陽駕車而行, 屈原的《九歌東君》言“暾將出兮東方……撫余馬兮安驅”; 另一說太陽載烏而行,有“羿焉日, 烏焉解羽?” (《淮南子·精神篇》), 也有《離騷》中言:“前望舒使先驅兮” (王逸注:“望舒, 月御也”)。駕車也好, 載烏也罷, 此二者都說明在原始先民看來, 太陽是需靠外力或能行動的工具才能運行, 因為原始人的想象總是以其自身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其次, 當自然環境發生變化時, 也必然伴隨著古人心理活動的變化。例如 《山海經·海外北經》記載夸父之死:“夸父與日逐走, 入日……棄其杖, 化為鄧林”。此則神話中, 古人即是用日落來隱喻夸父的命運, 或者勿寧說, 在古人看來, 外界環境與內心活動就是“一生二又復歸于道”的一個整體。而且當人的心理活動變化并借之以一定的媒介與天溝通, 外在自然環境也會相應發生變化。例如原始人通常以一種儀式化的身體活動為中介來溝通天人兩界, 如儺戲、巫術舞蹈等。正如謝六逸(1990, p.48)認為, 神話的流傳嬗變無法脫離神話所處的環境, 神話與自然人文環境是互相借用、同化和建構的。由此可見, 認知是具身的, 不僅身體活動方式決定了認知的種類和性質, 而且心智、身體、大腦和環境是一體化的系統(Kiverstein, 2018, p.19)。
以人神相通的角度觀之, 古人“天地人三通”觀與列維·布留爾(1981, p.69)的“身心互滲”觀, 其稱雖異, 其指卻一。楊堃先生譯為“渾沌律”。簡單來說, 古人就是以身體為中介溝通人神兩界, 身體是一切隱喻的母體。華夏神話多言, 古時天上的神與地下的人相交頻繁, 婚配往來者不足為奇, 如龔自珍在《壬癸之際月臺觀第一》云:“人之初, 天下通,人上通; 旦上天, 夕下天”。神下地自有法術, 而人不借助天梯就根本不能上天。古籍《淮南子·地形篇》和《淮南子·墜形篇》都記載昆侖山和建木都被視作神圣天梯, 可打通天人二界藩籬, 神人可藉之互通往返。后來, 神人頻繁亂交破壞了宇宙秩序, 故黃帝派重黎二神移去此木, 《國語·楚語》言:“古者民神不雜……九黎亂德……是謂絕地天通”。此時,人神之間的直接交往不再可能, 人上不了天, 但某種具有特殊能力、為上天先祖所鐘愛的“巫”卻仍保存了一絲“身體”的能力。《說文》釋“巫”字云:“巫,祝也, 女能事形, 以舞降神者也, 象人雨褒舞形”。他們透過身體的象征、儀式等幫助, 相信可以離體遠游, 重返神的故鄉。中國人講究修身, 自神話之后皆然, 《尚書》提及頗豐。古《尚書》明確提出了“袛厥身” (《尚書·伊訓》), “修厥身” (《尚書·太甲中》), “慎厥身” (《尚書·皋陶謨》), “慎”、“祗”與“修”的指向不過一“身”字而已。故顏習齋亦謂:“神圣之極, 皆自踐其形也” (《存學編》)。此間, 身體的媒介作用就凸顯出來了。中西方“人神溝通”的儀式涇渭分明, 西方僅通過“禱告”就能與上帝直接溝通, 而中國溝通天地神的祭祀活動不僅需要純粹“語言化”的過程, 身體在其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華夏創世神話深入溯源可推出“身體?人?萬物?神”的不斷生成變化的宇宙圖式, 而貫通于其中的應當屬中國獨異于西方的“氣論”。西方具身認知的動態生成觀認為大腦、身體和環境所層層嵌套的系統是自創生的, 認知的涌現過程是系統內元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即認知是身體與環境相耦合的, 且認知是成動力系統的(Thompson, 2001, p.3)。中國的“氣論”與耦合機制(coupling)不謀而合, 但同時中國的“氣論”又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即氣貫通于天地人三界。莊子認為“萬物皆種也, 以不同形相禪”,而遍布于萬物之間的交互感應之所以能成功, 就在乎天地一氣而已。現象學地來看, 此世中身與心不是二元分離的, 身涵納心, 心寓于身, 而在身心之間周游流轉的乃是“氣” (楊儒賓, 1996, p.49)。孟子亦提倡“養吾浩然之氣”, 認為流動性的“氣”貫通于人之“心”與“形”, 而使人的“身體”成為“人者與道為體之全也”。中國的氣論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對死亡的超越。《禮記》云:“魂氣歸于天, 形魂歸于地”。釋言之, 一切現象的“成、住、壞、空”的變化都是因為“氣”的變化, 生與死之間并不是具有嚴格界限的涇渭兩端, 生死之間是有聯結的, 關鍵就在于“氣”是大化流行, 無生無死的。所以, 老子堅持“死而不亡” (《道德經》), 莊子大呼“生死皆氣之聚散也” (《莊子·知北游》)。
以上, 中國神話中的“身體性”實則發端于中國古代哲人切身的“問題意識”——對人自身憂患處境的真切觀照, 如《易傳》言:“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于是中國衍生出了有別于西方“理”式的“自然”。中國神話的世界不是“道?萬物”的二元世界,而是萬物生成的一元世界。“自然”的本義含“自主”的力量, 絕不僅僅是“自然而然”, 即萬物憑借己身之力自發地生長、變化(池田知久, 2009, p.27)。因此, 中國神話中的“自然”被看作是一個具有生命形式的活的身體, 所以物我可以同一, 天人可以交感,人神也可以相通。同時, 身體的物理狀態引發的心理狀態是一個直接的過程, 不以任何思維或推理為中介, 而是以“氣”為媒。究一言以概之, 氣在空間屬性上, 萬事萬物萬人之別均由一氣所統屬, 可大化流行, 周游貫通, 即“存有連續性”。而氣的生成屬性屬于本末關系, 一切生命的本質在于“生成”,一切事物的意義是在“生成的運動”中凸顯出來的。以神話的現象學觀點來審視“身體”與“自然”的關系,我們會發現“自然”宏觀上可理解為一個“活的”的生態系統, “身體”只能是“現象學式”的, 而不是“實驗室式”的。
4 神話的身體當下觀:時間維度
如上文所述, 創世神話中的“身體”涵義包括了身體生成狀態(本體)和身體現象學狀態(空間), 同時中國的“身體”也是一種歷時性哲學。海德格爾(2006, pp.474?482)在《存在與時間》中將時間分為存在時間和流俗時間。流俗時間認為, 時間就是從過去走向未來, 時間是客觀的, 在這里, 人不具有主觀能動性。而存在時間認為, 時間是主客觀一體的。以存在論視角來探究時間, 時間有多種“意向結構” (可能性)——“過去”、“現在”和“將來”, 但純粹的時間卻不是流動的線性時間樣式, 而是這三種時間樣式的共同在場。具身認知有一個概念“實時認知”, 即是認知是處于時間壓力下的(Wilson, 2002,p.626), 即必須從與環境的實時交互中來理解認知,“認知即認知發展” (李其維, 2008, p.1319)。“現在”的認知無不受過去記憶和將來期望影響, 因此“實時認知”實則包含了“過去”、“現在”和“將來”。最值得考究的是, 中國的“時間”大異于西方, 更類似于黑爾德(2003, p.244)提出來的“世代生成的時間經驗”。在中國社會里, “孝”的家庭觀至關重要, 這意味著“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有可能保存這種原始時間經驗的基礎”。在“身體”的時間維度中, 客觀的空間現象(環境)已然被轉化成主觀的時間現象(社會、文化、歷史) (李清良, 2006, p.21)。因此, 文化意象?社會思維?歷史建構三者扮演了“身體”的時間歷程的三個外顯角色, 其中“身體”則是歷時性的本質角色, 時間維度已然消解于其中。
華夏文化是帶有神話色彩的文化, 神話與生活早已熔于一爐而冶之, “神話”一詞并未被古人日常所提及, 蓋因國人自古而今就生活在神話式的文化思維之中(葉舒憲, 2010, p.2)。古今政治、文學甚至宗教系統中, 創世神話中的“身體”早已成為被賦予各種內涵的文化符號, 并流傳至今。原始文化中,神話思維的邏輯前提是一切生命之間似乎都有親緣關系, 而其中“圖騰崇拜”最具特色(恩斯特·卡西爾, 2013, p.105)。例如華夏民族崇尚“龍圖騰”, 傳說禹父鯀死后“剖之以吳刀, 化為黃龍也” (《歸藏·啟筮》)。《玄中記》云:“伏羲龍身, 女媧蛇軀”。聞一多(1997, p.35)從“二龍傳說”推源得出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的身體形象, 并推論出龍圖騰乃博采古代眾圖騰之所長而新造之物, 龍文化也是華夏真正的本位文化。原始初民虔誠地相信具有共同圖騰崇拜的每個人都與圖騰祖先密不可分, 并能夠在時間的長河中常存長青。圖騰崇拜進一步衍化就變成了神像崇拜, 各個宗教的造神運動就是擷取了“身體”的重要表意作用, 神的身體儼然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神話符號, 傳示萬世。比如, 道教諸神、佛教諸菩薩和基督教耶和華, 其身體造像有其泛指指符,又都有其特指指符, 古人與今人之所以能立即分辨開來實因“身體”所承載的神話意義。正如梅洛·龐蒂(2001, p.529)這一至理名言所揭, “最后的意識是‘無時間的’(zeitlose)”。西人文化專攻“重思”之認識論哲學, 以非歷時性顯著; 而東方古老文化以“重身”本體論哲學立論, 以歷時性為特色。古人的根身文化早已借孔子的儒學流傳至今。縱覽儒家文化, 一言以蔽之曰“反求諸其身”。由自己的身體出發可踐行文化之“仁”, “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論語·雍也》。由自己身體出發亦可踐行倫理之“孝”,“身體發膚, 受之父母……立身行道, 揚名于后世”《孝經·開宗明義》。由自己的身體可踐行宇宙之“道”,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正顏色和出辭氣” (《論語·泰伯》)。在這里, 龍圖騰、神靈指符均升華了身體圖像, 表明“身體”早已成為了中華文化的編碼邏輯, 而且早已在時間的長河中內化為中華文化的基因之一。
社會生活中所存有的神話式思維與榮格(1986,p.79)的集體潛意識概念是息息相通的。每個人都是全人類億萬斯年的意識繼承者, 每一個當下華夏初民們的身體現象學經驗都凝聚在每一個人的潛意識之中構成巨大的心理能, 謂之“集體無意識”。神話故事就是后世在思維中進行精神重構的原型, 而只要今人重新體驗到原型中蘊含的古人的碎片化生命經驗, 過去的生活世界就會重現, 未來的世界也將依此重新建構。與西方理性主義思維模式不同,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以主客體統一為首要特征的主體思維(蒙培元, 1993, p.7), 其衍生物是“天人合一思維”, 這種思維方式完全來源于中國神話思維, 即是動用各種原始思維方式對自然與人文環境作出多重交感反應, 傳達出原始初民所展示的世界相的意義。古人出于對雷電自然力的敬畏懼怕而創造了雷神形象來使心理狀態客觀化, 而創造的方式即為古人樸素的思維方式。如西漢王充《論衡·雷虛篇》說:“圖畫之工, 圖雷之狀……連鼓相扣擊之意也”。這里, 吼聲、叫聲、擂鼓聲等等, 都取其與雷聲相似之處。此外, 神話中把日月星辰、風雨雷電等神都說成是環繞在“天帝”周圍的大神, 也是原始人的空間類比思維模式使然。上述可得, 原始先民們在創造這些神話時, 他們所遵循的類比聯想的思維方式是共同的。最有中國特色的當屬“陰陽”思維模式。中國“陰陽哲學”內圣外王之表現, 一方面,社會倫理被視為基于“身體”而生發的“禮文化”的展延,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禮記·中庸》); 另一方面, 社會政治制度也被視為基于“身體”而外化的“法理”的擴張, “湯武, 身之也” (《孟子·盡心上》)。如《呂氏春秋》記載, 商王成湯用身軀在桑林中祈禱, 這里, 商王成湯之發、手以及身都成為國家思想傳統的表征, 在這個意義上, 湯的身體是“政治的身體”, 也是“禮”的身體。《論語·季氏》中有云:“君子有九思”, 更是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身體多器官都可進行思考。所以, 這種被社會價值所潛移默化的身體, 就不再是純粹生理的身體, 而是能表征道德意識的身體(黃俊杰, 2006, p.25)。古人多稱這種身體表征為“威儀”, 如子思贊孔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中庸》)。故而, 在一個主客尚未二元的神話思維世界里, 思維在空間中是流動的, 在時間上可逆的, 以身為本的神話式思維形成了政治倫理制度, 最終形成了今天中國人獨有的思維模式。
神話是人類對事物的起源和時間問題的最早思考, 是人類歷史意識萌芽的一個標志(恩斯特·卡西爾, 2013, p.219)。“神話的歷史觀”和“歷史的神話觀”之爭自聞一多始, 直到顧頡剛(1982, p.60)提出“層累地造歷史觀”, 才終使后人“廓清云霧, 斬盡葛藤, 使后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偽史所蒙” (錢玄同,1982, p.67)。天行有常, “史”行亦有常, “今史”終究難以復原“古史”之容貌。“神之選民”抑或是“泯然眾人”其形象亦均是在朝代更迭嬗變中被“層累的創造”的。五千年之后, 今人已不能完完全全把神話中的古史成分和神話成分如實區分開來, 神話就是歷史, 歷史也就是神話(趙沛霖, 1995, p.53)。神話與古史難分在我國表現尤為突出。如公元前二世紀的《說文》里, 女媧只是一個女性神坻, “媧, 古之神圣女, 化萬物者也”。漢代以降, 《淮南子》記載女媧搖身一變躍為女皇, 與伏羲一起共治天下。女媧概念范疇的變異、拓展和重組都揭示了身體創世神話在神話歷史的螺旋演變中早已“歷史化”并源遠流長。古籍記載“黃帝本為皇天上帝也” (楊寬, 1982,pp.195?199), 皆因神話歷史化, 后輾轉流傳而為華夏民族神人共同始祖, “黃帝萬諸侯,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漢書·郊祀志》)。《國語·晉語四》記載黃帝的生父被附會在古代某一位民族首領少典身上,而《水經注·滑水》和《史記·五帝本記》也記載黃帝的家鄉被后人附會于天水和壽丘兩個地方。從加達默爾(2004, p.283)“效果歷史”的觀點來看, 真正的歷史并無主觀客觀之分, 而是主客體之間的一種關系。每一代今人都在自己的視閾中解構、重構歷史使歷史更接近于真相, 但歷史真相中的主觀解釋偏見永遠不可能被消除, 只能日益檢驗、修改和完善。歷史事實雖然過去了, 但是歷史解釋還活著。在神話的意義上也是如此。雖然神話事件已經過去了, 但是它的解釋空間還在, 在此空間中, 今人視閾和古人視閾的解釋不斷碰撞融合形成新的解釋并達到視閾融合, 時間維度因此趨于消解。如西方《圣經》的意義就是一個不斷經由后人解釋的生長的有機體。因此克羅齊(1982, p.2)講“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一切神話也都是當代神話。
西方文化講究基于“意識”的“道成肉身”的外在超越, 而中國文化講究基于“身體”的“超凡入圣”的內在超越。這不僅表現為中國文化發端于“身體”的神圣性, 還表現為身體的“男女交感”機制衍生出了“時”的神圣性(張再林, 2006, p.14)。“周易”, 顧名思義即“變易”, 而“時”應當為“變易”之魂, 故中國的“易”的理論就是“時” (王新春, 2001; 黃黎星, 2004;王振復, 2007)。就如梅洛·龐蒂(2001, p.515)所講,“時間不是我把它記錄下來的一種實在過程、一種實際連續。時間產生于我與物體的關系”。關系變化, 時間也隨之而變。但關系變化與否還是取決于身體的不同指向, 而身體具有“意向性”這個變化事實是不變的, 在這個意義上, 時間也是不變的。故而東漢鄭玄曰:“易即不易” (《易贊》)。中西哲學大異其趣之基本點, 即中國哲學里, 關系的意義總要優勝于元素的意義。變化的是元素, 不變的是關系。一方面, 王弼謂:“夫卦者, 時也; 爻者, 適時之變者也” (《周易略例》), “變通者, 趣時者也” (《系辭下傳》), 所有的身體的可能性活動都隨“時”進行流轉, 時移事易。另一方面, “六爻相雜, 唯其時物也” (《系辭下傳》), 舜的“敕天之命, 惟時惟幾”(《益稷》), “時”也產生于主客雙方的關系里, 易即不易。老子的思想亦有此意味, 如“物壯則老”、“反者道之動”、“萬物并作, 吾以觀復”。凡此種種都揭示了中國所特有的時間觀, 即方以智的“輪”式的時間(《東西均·三征》)。
以上, 社會建構論告訴我們, 人類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并非是對固有經驗消極被動“發現”的, 而是處于一定關系中的人們積極主動“發明”的。換言之,主體、現象與實在都不是經驗歸納的產物, 是嵌入于文化、社會、歷史環境中的人們進行互動、溝通和協商的互動建構的結果(Gergen, 1985)。通過華夏創世神話所催生出的文化意象、社會思維、歷史感也是建構的結果, 而建構的主體就是人的身體。身體就是時間, 而時間是由現在建構而成的, 如《說文》釋詁曰:“時, 是也, 此時之本義, 言時則無有不是也”。一言以蔽之, 周易的“時”以時間統攝空間,涵具時、空、人與物四者于一體, 這里的“時”其實是一種具有主體性的現象學經驗, 所以身體具有包含有眾多時間經驗的當下性, 這就是中國獨有的身體的“時”。中國文化傳統“既是非超越性的, 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 (郝大維, 安樂哲, 1999, p.234), 這種具有鄉土氣息的宗教性絕非來自于形而上的西方上帝的意志的神啟, 而是發端于活生生的中國人的身體的體驗。
5 小結
心理學應是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于一身的統一心理學(Ardila, 2006)。所謂自然科學取向還是體現在研究方法的優越上, 即實驗設計、統計分析以及研究結論的大樣本意義。所謂人文科學還是依賴理性思辨的縝密, 即反思、觀點、論證。而具身認知沖破了第一代認知科學的知覺、認知和行為的“三分模式”壁壘, 并被寄望于成為具有整合業已二分的心理學潛力的新的研究取向(Soliman, Gibson,& Glenberg, 2013)。中西背景下, 具身認知雖已引發了一場持續已久的熱潮, 但也出現了諸多問題,例如概念如何界定問題、實驗如何操作和結論如何解釋等問題(Newen, de Bruin, & Gallagher, 2018)。
心理學的整合之路既要汲取西方的“具身認知”觀點, 也要結合中國古已有之的“具身心理學”思想, 特別是要注重從中國神話這個根源上挖掘中國“具身”的真正蘊義。吳光明(1993, p.395)認為“身體思維”有兩種區分, 一是 bodily thinking, “身體”被動地作為工具進行思維活動, 身體協助思考; 二是body thinking, “身體”主動地作為主體進行思維活動, 身體就是思考本身。不言而喻, 中國的身體思維屬于后者, 中國無認知這個概念, 卻有體知的概念。從認識論的意義上看, 沿襲希伯來神話的二元論思維模式, 西方心理學也一直是以身心二元的分類思維來認識事物的。在此基礎上, 西方具身認知雖然號稱反對離身認知, 但仍然難以徹底廓清身心二元的痕跡, 仍然是在身心二元的基礎上重新強調身體的價值, 畢竟西方的認識論早就預設了身心二元的邏輯前提。湯淺泰雄(1997, p.67)指出中國傳統哲學實為實踐哲學, 是以研究身心修行關系為基礎的哲學。若從哲學上講, 西方的“形而上學”是以“觀察知識”為立論之基, 而中國的“形而上學”是以“體驗知識”為攻訐之本, 二者不可同日而語。自古以來,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就是軒輊兩分, 各執一端的。中國人自然難能生發出西方意義上的“認識論”, 因為中國思想的土壤基礎是“本體論”。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并沒有從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明確的分化出來, 類似于胡塞爾講的“純粹心理學” (鄧曉芒, 1996, pp.66?67), 即不是考察人類心理能力的分類、運作和關聯, 而是著眼于人的心理本身是什么樣的意識結構。所以中國的“具身心理學”思想是在本體論的意義上強調“天人合一”、“身心一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 中國文本背景下的“身體”才是全然具足的“身體”。因此, 我們勢必不能再以西方心理學為圭臬來淘篩中國心理學思想(張春興, 2002,p.596), 應站在中國傳統具身心理學思想的理論高度上, 為反思西方具身認知研究已經顯現和仍然潛藏的問題帶來新的理論視角, 依此進路, 我們將看到中國心理學建立的可能。
中國一定有自己的心理學思想, 但問題是如何結合中西具身認知心理學思想的創造性轉化而建立起來中國人自己的科學的具身心理學。中國心理學若欲建為成熟科學, 必以理論、數據和闡釋三駕馬車并駕齊驅, 方才有實現之可能(崔光輝, 陳巍,2011, p.485)。依西方科學標準的定義, 中國文化并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科學共同體, 更遑論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 但以東方理路窺之, 中國文化實有自己的獨立的邏輯范疇與內在運演(汪鳳炎, 鄭紅, 2006,p.97)。從方法與實證的整合程度來說, 西方具身認知在系統化維度上更勝一籌; 但從理論與實踐的契合程度來說, 中國具身認知思想在豐富化的維度上也不遑多讓。欲建中國之具身心理學, 中西科學觀的本質差異不得不首先厘清。以研究范式選取為例,就需要注意到中國具身認知觀的具身概念與實踐概念的所指并非“一對一”的關系, 而是“少即是多”的關系, 如中國古人所講的“理一分殊”。最近MIT的幾個心理學家通過核磁掃描方法所做實驗表明,在參照左邊的小框小線之后, 亞洲人更傾向于在右邊的大框中畫出等比例的大線, 即亞洲人比美國人對背景信息更敏感, 更易依據背景信息作出相應判斷(Hedden, Ketay, Aron, Markus, & Gabrieli, 2008)。這個實驗就是中國具身文本的最好解讀, 因為中國的“身體”講究的是“天人合一狀態”。此中可得, 今后做中國的科學心理學實驗所必須考慮到中國文化背景, 絕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心理學實驗的身心二分的實驗范式和實驗解讀。于今, 遵循中國神話的思維路徑, 我們完全可以選取影響力之廣、持續時間之長的“巫術”、“氣功”和“中醫”等具有中國古老文化色彩的身體元素, 并嘗試用中國具身范式嘗試進行實證研究, 來作為中國具身心理學研究的發軔之作。
理論落地方為正途。故參照多位致力于建設中國心理學的學者們之思想, 可以嘗試總結并提出建立中國心理學的三條切實可行的具體路徑。一是心理學應堅持“學科獨特性”原則, 以研究“心理活動的過程和機制”為立身之本(李其維, 2019)。心理學人需以獨特研究對象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采自然科學取向和人文科學取向各家所長, 致力于中國人和西方人所共有的心理機制的發生發展變化之研究。二是心理學應堅持“一種心智, 多種心態”原則,以心理學本土化研究為適用之所(黃光國, 2014)。心理學人更需要置身于本國社會歷史文化中, 努力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豐富的心理學思想, 使其與西方近現代心理學連續起來以資構建起具有普遍意義的心理學體系。三是心理學應堅持“一致性”原則,以合乎人的心理實際為發展之維(潘菽, 1985, p.2)。心理學人最應致力于從中國現實情境中提煉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核心的、帶有一般心理機制意味的概念、范疇、理論, 并與時代變換有機結合以饗中國心理學不斷構建乃至終成科學之體系。
綜上所述, 中西方神話中所蘊含著的具身心理學思想同異皆有, 最難能可貴的是, 中國的“身體”在本體論維度、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都有著獨有于西方的“中國元素”。本文藉由神話之身, 以期通過“中西互釋”能為消解中西心理學思想的對立與沖突構建“對話平臺”, 進而為建立起來中國人自己的科學的具身心理學, 為本土心理學走向世界提供中國神話的“窄門”。
“我們沒有心理學, 但有心理學的思想” (高覺敷, 1985, p.76), 就是具身心理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