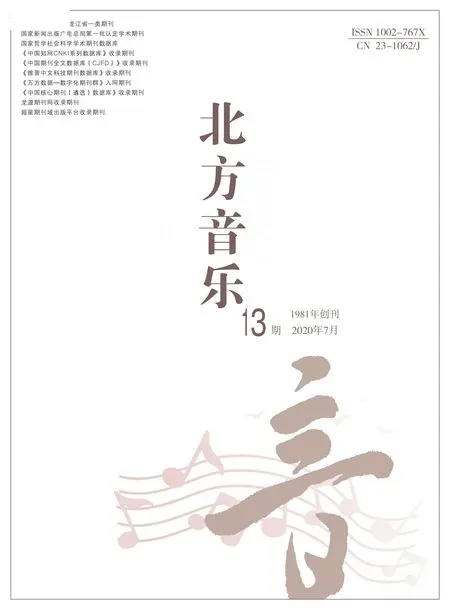淺談秦腔唱腔
郭嘉儀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北京 100872)
引言
秦腔又稱為梆子腔,是流傳于我國西北包括陜西、寧夏、青海、新疆和甘肅等地區頗具地方特色的傳統戲劇,它的歷史淵源留長,是經歷了人民世世代代的創造和演變,經過時間長河的錘煉逐漸形成的相當古老的一種劇種形式。但是距今為止,它的起源眾說紛紜,不一而論,有說秦代就有了秦腔的雛形,還有說是唐代長安是秦腔的演變之地,更有元朝,清代開始興起的學說。這些學說,都有待考證,所以秦腔的起源還不可妄言,以下筆者只述秦腔唱腔。
一、秦腔的代表性唱腔歡音和苦音
秦腔的唱腔分為歡音腔和苦音腔兩種。所謂的歡音,也叫花音、硬音,顧名思義就是表達歡快的情感,旋律線條明亮、輕快,而又不失力量,擅長表現各種歡樂、喜悅的心情。而苦音,也稱作軟音、哭音。它和歡音情緒表達截然相反,但卻最能代表秦腔的特色,它把凄凄慘慘戚戚描繪得栩栩如生,深沉的曲調在哀婉、激昂的表現手法中切換自如,把悲憤、凄涼、哀痛、懷念的感情表現的淋漓盡致。
秦腔里的歡音腔和苦音腔是根據戲劇中的場景情節和人物需要來選擇性地使用。但是它們之間卻又有嚴格的區別,兩種不同的音群組織雖然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關系,但是彼此在對方的音群區域內出現的機會比較少,或者僅僅出現在不重要的曲調里面。
秦腔里歡音和苦音的兩大調式當中,很明顯能看到,歡音是大調式清樂音階的調式特性,但是它不僅僅表現角色歡快的情緒,而是能夠表現得更加細致、和歡樂有關的情緒。而苦音的調式表現則更為明顯,與燕樂音階類同,融入了西北少數民族的音樂,增加了音樂的飽滿度。相比歡音曲調來說,苦音曲調相對表現的陰郁低沉,而且具有小調的性質特征。
秦腔的演唱方式用的是陜西關中的方言,而秦腔的基本板式有慢板、墊板、滾板、二六板、二倒板、流水板等六大主要形式。而其中除了慢板和滾板沒有歡音,只運用苦音之外,其余的各個板式中都可以區分開歡音和苦音這兩種形式。
秦腔在歡音唱腔中,旋律的進行方式為旋法的五聲音階,上行和下行級進,波浪式的進行為主,而上行和下行的跳進也會出現。調式音階和旋律的行進方式善于表達歡快熱鬧的音樂景象,在戲曲中用來刻畫出場角色英武豪邁、大義凜然、剛正不阿的正面形象。秦腔在苦音唱腔中,旋律的進行方式為下行級進,上行跳進。它的調式音階和旋律進行的方式,善于表達哀愁憂郁、悲憤凄苦的音樂場面,見者心酸,聞之落淚。如《斷橋》中的詞牌片段:“恨宮人喪良心不如禽獸,一心心聽佛法永不回頭,全不顧魚水情胡行亂走,好夫妻(耶)倒做了臨風的馬牛。”從詞牌上就能看出角色的悲苦無依和憤懣的心情,再加上演員的細膩演繹,整個鮮活、悲憤的角色躍然紙上,這就是秦腔苦音腔的魅力所在。
秦腔的藝術劇本多聚焦在歷史故事中,貼近人民群眾民風和民俗,內容題材廣泛,最為突出的是悲劇色彩為其主要核心,大悲以后迎來大喜都是秦腔劇本一貫手法,具體表現在歷史舞臺上的家國仇恨、金戈鐵馬,或者是文臣武將用正義為國為民做出重大貢獻的題材。在劇目上極盡渲染主要角色的苦難遭遇,音樂上用大篇幅的苦音唱腔來把悲劇的層次一層一層推向高潮,用苦音唱腔把劇中人物的悲劇形象烘托得無以復加。而劇情最終難免落于苦盡甘來、皆大歡喜的俗套之中,主要是因為受中國傳統戲曲的思維方式和結構模式影響,不僅是傳統戲曲的結構形式,也是人們心理的安全接受度,表現出了起筆平鋪、結尾圓滿的特點,而這一特點也受到了很多學者的詬病。但是這是因為文化背景的固有模式而造成的,需要有大膽突破的思想來進行新的創作。
二、秦腔的不同角色,所代表不同唱腔的演唱特點
秦腔逐年累月下來形成了一種極富有夸張的藝術形式,唱腔高亢質樸,高能引龍有悔,低能悲泣成聲。表演真實細膩,入木三分,最易打動人心。演員要用不同的唱腔演繹不同的角色,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唱念做打,一板一眼,扣人心弦。唱腔根據每個出場人物形象和性格不同,按照劇情的發展貫穿全劇,立求為觀眾帶來切身體會的情感氛圍,融入其中,感受劇中人物的喜怒哀樂。劇情緊張的時候,演員唱腔噴口有力,字字珠璣;劇情舒緩之時,演員唱腔又會由快變慢,一寸一寸婉轉吟唱,點點滴滴潤心沁肺。
秦腔的每一個角色出場,都是一個人物的鮮活形象表達,角色中細分有四生(花生、須生、小生和幼生),六旦(老旦、正旦、小旦、花旦、五旦和媒旦),二凈(大凈和毛凈),以及一丑,十三種角色。這些角色的逐一登場,表達的角色儼然不同,所以對演員的要求精益求精,立求將真實的情感帶入其中,要有渾然天成的氣勢,才能將不同的角色演繹好,才能打動人心。一開口,一舉手,一投足,嬉笑怒罵,哀樂愛恨,皆要聲聲入耳,扣人心弦,少不得演員的努力付出和鉆研。
秦腔中的老旦出場,演唱的角色一般是具有多種身份地位的老年婦女,有尊貴和卑賤之分。老旦所走的臺步,唱腔和道白都有自己角色的獨特之處。秦腔老旦臺步走大八字步。唱腔上用低沉的道白唱念音調起始,旋律簡潔直白。和正旦的唱念完全不同,正旦在秦腔中多具有正直無私的性格,角色是舉止端莊大氣的中年婦女,演唱唱腔穩重而又不失含蓄,將欲語還休表現得淋漓盡致。而秦腔中的其他旦角在演唱中唱腔多為年輕姑娘所具有的明朗清脆,不失活潑的聲音特點。
秦腔中的老生,一般在秦腔曲目中扮演老年人的角色,人物形象多為老年官員和社會底層人物,人生經歷豐富并飽受歲月滄桑。唱腔表現穩重、寬厚而不失質樸。而秦腔中的小生角色多表現為青年男子,演唱時要將男子的瀟灑、豪爽而又不失儒雅英俊的風度逐一表現出來。秦腔中的須生唱腔多為高昂奔放的方式,嗓音高亢嘹亮。
秦腔中的凈角,是劇目當中最具有特色的角色。演唱唱腔多粗獷、豪放不羈,是秦腔行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凈,大花臉,唱功和念功俱佳,腔腔生情,把旋律演唱放在前面,而后才是角色表演,但是表演的動作幅度很小。
秦腔中的丑角,劇情角色唱腔承擔詼諧、打趣的方式來演繹。他們出場插科打諢,幽默風趣,滑稽逗樂。他們在舞臺上展現的是和其他角色完全不同的形象,完全顛覆了其他角色獨有的特點。他們需要唱念做打全部融會貫通,并且把韻味、神情、獨有的諧謔個性和特色完全發揮到極致。
三、秦腔的另一大特點“吼”和現實社會環境緊密相連
秦腔唱腔“吼”字當頭,并被很多人認可。為何有如此一說?因為秦腔的發展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區,地理環境惡劣,造就的人物形象和其他優渥地區形成截然不同的對比。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西北地區人民擁有著豪爽耿直、勤勞淳樸、勇敢敦厚的民風。西北高原的艱苦的生存環境,造就了秦腔用“吼”的形式出現,“吼”出人們對艱苦歲月的不妥協,“吼”出人們相信只要心存希望,就一定會有幸福生活來敲門!一出戲,一出人生生存的意義,用“吼”來表達人們內心豐富的情感!
陜西著名作家陳忠實的文學作品《白鹿原》里,用大段的陜西地方方言,一方面描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環境中的各色人等的百味人生,用語言文學描寫得錯落有致,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還將地方傳統戲曲秦腔引入其中,將《白鹿原》這部小說的語言句式和秦腔板腔音樂相互結合在一起。文學中的蒼涼厚重,用秦腔中的散板——慢板——急板——結束這一過程,演唱者用這種循序漸進的節奏推進方式將故事層層展開,把語言張力和秦腔的大氣磅礴、“天地一聲吼”的氣勢互相融合交匯,成為這片佳作的一大特色。
“吼”產生的原因,回顧歷史就會發現,關中地區也就是最早的秦文化產生的地方,述說稱為八百里秦川,在這片土地上因為朝代不斷更迭,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的場景不斷上演。而秦地在歷史文獻記載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各種戰亂和天災聚集之地。可想而知,這里生活的人民是處在怎樣一種環境之中?如杜甫的《兵車行》中描寫的片段:“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劍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這種古時征收兵役和徭役的詩句中,道盡人世間的生離死別,哀嚎悲苦之音,悲吼之聲,令人心悸,悲憤的怒吼能夠插入云霄。現觀之今天的大秦之腔調,包括了秦腔、眉戶、碗碗腔等,俱是表現出了粗狂豪放、蒼涼悲壯的唱腔聲調。這些大秦之音都是秦人的歷史寫照,是用天災人禍堆砌而成的結果。
秦腔的“吼”字,這種嘶吼式的發音,并不單純是一種感情宣泄,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發音方式,它是一種長久浸淫在歷史文化中層層積淀的活化石,是鮮活文化中富有原生態表演的文化形式之一,也用“吼”字表現出秦腔的強烈濃郁的抒情特點。“吼”是秦腔的本色,不能輕易改變,因為它代表的是這種戲劇繁衍生息的、代代相承并賴以生存的根系。
四、秦腔的未來發展前景
秦腔唱腔的發展從20世紀以來,推陳出新,在保留原有的藝術基礎之上,又在調式、板式、樂隊編配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變,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而對秦腔演員的演唱更是要求精益求精,對他們演唱秦腔的氣、韻、聲、字等都需要更加精湛的表演藝術功底來作為鋪墊。秦腔不但要保留傳統,還要順應時代的變革,適應時代審美標準,貼合人民群眾,更要采取百家之長,接受不同的觀點,才能讓秦腔這一傳統戲劇經久不衰。
時代的快速發展,秦腔雖然作為古老的戲曲劇種獨樹一幟,現在也成為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但是現在的秦腔藝術保護和發展,成長的文化環境堪憂,大秦文化的支持和影響力日益減少,不復往昔。而秦腔作為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藝術,缺失了秦文化的支撐,勢必會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再加上秦腔的群眾基礎薄弱,以老年人居多,青年人卻相繼缺失傳承。秦腔的發展勢頭堪憂,筆者希望國家能夠大力提倡傳統戲劇走進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去,鼓勵普通民眾接觸中國傳統戲劇,感受中國古老戲曲的魅力,從而使這一中國傳統戲劇瑰寶薪火相傳、生生不息,這也需要我們所有人的努力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