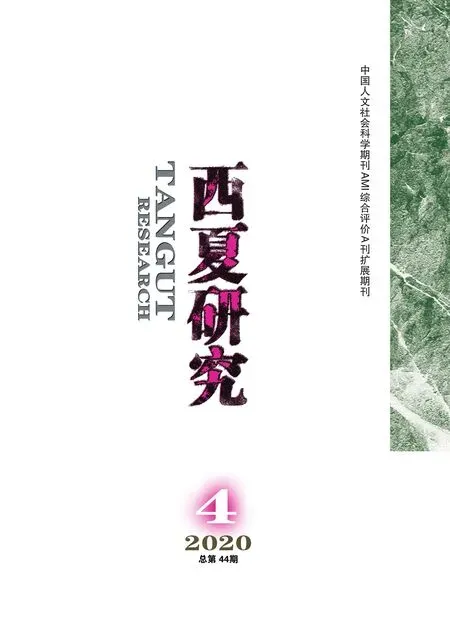論拓跋思恭勤王時(shí)的 “夷” 兵
□周永杰
晚唐黨項(xiàng)拓跋部的興起,傳世文獻(xiàn)言之甚簡(jiǎn)。最早的記載是《舊唐書》中拓跋思恭參加勤王,“太原節(jié)度使鄭從讜發(fā)本道之師,與北面行營招討副使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玫、夏州將李思恭等行營諸軍,并赴京師討賊”[1]709-710。不過,與行營諸將的明確身份相比,拓跋思恭的職務(wù)相當(dāng)模糊。《資治通鑒》(下文簡(jiǎn)稱《通鑒》)的記載稍為詳細(xì),“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黨項(xiàng)羌也,糾合夷、夏兵會(huì)鄜延節(jié)度使李孝昌于鄜州,同盟討賊”[2]8249。結(jié)合定難軍自撰文獻(xiàn)《白敬立墓志》:“大寇陷長(zhǎng)安,僖宗卜省于巴蜀。王自宥州刺使率使府將校,統(tǒng)全師問安赴難。”①可知《舊唐書》中“夏州將李思恭”即是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通鑒》的記載更為準(zhǔn)確。
對(duì)于拓跋思恭所部勤王軍,《通鑒》特意提到:“糾合夷、夏兵會(huì)鄜延節(jié)度使李孝昌于鄜州,同盟討賊。”[2]8249“夏”與“夷”連用,“夏”應(yīng)是華夏、漢之意,可知勤王部隊(duì)兼有“漢兵”與“夷兵”。當(dāng)時(shí)拓跋思恭已任宥州刺史,前引墓志中提到:“王自宥州刺使率使府將校,統(tǒng)全師問安赴難。”“漢兵”應(yīng)該是宥州戍兵。關(guān)于“夷兵”,《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指出:“拓跋思恭集結(jié)漢—黨項(xiàng)羌軍隊(duì),幫助唐朝效忠的武裝。”[3]184言下之意,“夷兵”即是“黨項(xiàng)羌兵”。這種觀點(diǎn)應(yīng)該是由拓跋思恭族源推演而來的,并未被充分論證過。由于勤王時(shí)的軍隊(duì)涉及早期拓跋部勢(shì)力的形成,是了解黨項(xiàng)崛起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仍有進(jìn)一步考察的必要。
靖邊縣出土《白敬立墓志》記錄了拓跋思恭擔(dān)任宥州刺史前后夏州政局的變動(dòng)。特別是關(guān)于拓跋思恭發(fā)動(dòng)兵變、勤王過程的記錄為了解其勢(shì)力構(gòu)成提供了線索,可補(bǔ)正以前的認(rèn)識(shí)。
一、夏州兵變中的拓跋思恭勢(shì)力
關(guān)于晚唐夏州發(fā)生的兵變,景福二年(893)定難軍節(jié)度判官李潛追述道:
王始為教練使,公常居左右前后,凡邊朔戰(zhàn)伐、軍機(jī)沉密,多與公坐謀。時(shí)有征防卒結(jié)變于外,突騎得入屠滅權(quán)位,其首亂者逼節(jié)使,請(qǐng)署為馬步都虞候。半年之□,凌慢愈甚。時(shí)朔方王集部下,伺隙盡擒誅之。公弟兄皆與其事。洎乾符年,大寇陷長(zhǎng)安,僖宗卜省于巴蜀。[4]84
拓跋思恭被封為朔方王后,定難軍自撰墓志中就以王位尊稱[5][6][7]。所記“征防卒兵變”與“拓跋思恭兵變”兩事,發(fā)生于拓跋思恭任教練使到乾符年(874—879)之間。關(guān)于拓跋思恭任教練使的時(shí)間沒有明確記載,根據(jù)宣宗大中六年(852)五月敕書:“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huì)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xí)時(shí),常令教習(xí)。仍于其時(shí)申兵部。”[1]630-631唐朝全面設(shè)置教練使始于大中六年(852)。那么,拓跋思恭任教練使的時(shí)間應(yīng)在大中六年以后。志文還記載拓跋思恭任教練使時(shí)的人事交往,“王始為教練使,公常居左右前后,凡邊朔戰(zhàn)伐、軍機(jī)沉密,多與公坐謀”,表明拓跋思恭為教練使時(shí)志主白敬立已經(jīng)成年。白敬立生于大中五年(851),咸通元年(860)方才九歲,則拓跋思恭任教練使不會(huì)早于咸通以前。因此墓志所記夏州兵變應(yīng)發(fā)生于咸通年間(860—874)。這與《新唐書》對(duì)拓跋思恭由教練使再任宥州刺史的記載吻合,“拓拔思恭,咸通末竊據(jù)宥州,稱刺史”[8]6218。
咸通年間夏州兵變前,會(huì)昌(841—846)、大中(847—860)年間對(duì)平夏、南山黨項(xiàng)的戰(zhàn)爭(zhēng)方才結(jié)束。據(jù)唐朝善后綱領(lǐng)《平黨項(xiàng)德音》記載,黨項(xiàng)之亂很大程度上是由帥臣貪尅所致。唐廷在黨項(xiàng)地區(qū)增筑堡寨、屯戍,逐界制置把捉,禁止與部落交易兵器。[9]710在此基礎(chǔ)上,調(diào)整軍政結(jié)構(gòu),“夏州節(jié)度使增領(lǐng)撫平黨項(xiàng)等使”[8]1785,意圖加強(qiáng)夏州節(jié)度使對(duì)黨項(xiàng)部落的管控。不過上述措施卻未能緩和與黨項(xiàng)的關(guān)系,史書記載:“今委李安業(yè)依朝廷制置。差兵建筑防守。尤恐部落心懷疑慮。委令李安業(yè)駐軍塞門。朕之屈法從人。斯為極矣。”[9]700唐廷增加戍守兵力,“尤恐部落心懷疑慮”,鎮(zhèn)戍軍隊(duì)只在塞門駐軍,以示彈壓。征防軍隊(duì)與黨項(xiàng)部落的關(guān)系仍相當(dāng)緊張。
夏州兵變就是在這種政治形勢(shì)中發(fā)生的。墓志云:“時(shí)有征防卒結(jié)變于外,突騎得入屠滅權(quán)位,其首亂者逼節(jié)使,請(qǐng)署為馬步都虞候。”[4]84“征防” 為唐初兵役,服役者稱“防人”或“征防人”,施行于府兵制時(shí)期,如《舊唐書》載:“凡衛(wèi)士,各立名簿。其三年已來征防差遣,仍定優(yōu)劣為三第。每年正月十日送本府印記,仍錄一道送本衛(wèi)府。”[1]1843府兵制解體后,沿用于各地屯戍部隊(duì),墓志中的征防卒即指夏州地區(qū)的戍兵。征防卒兵變后升任馬步都虞候。據(jù)嚴(yán)耕望考證,“諸府都虞候似僅一人,亦稱為馬步都虞候。但亦偶分兵種馬軍步軍各置都虞候”,德宗時(shí)代以行軍司馬為儲(chǔ)帥,“都虞候亦常得繼任府主,或?yàn)樾熊娝抉R”[10]442-443。由此可知兵變后征防卒一系已躋身夏州節(jié)度使高層,節(jié)度使府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發(fā)生巨大變化。
此后教練使拓跋思恭勢(shì)力受到壓制。志文稱:“半年之間,凌慢愈甚。時(shí)朔方王集部下,伺隙盡擒誅之。公弟兄皆與其事。”②征防卒兵變后對(duì)黨項(xiàng)部拓跋思恭等“凌慢愈甚”,極易使人想到此前平夏黨項(xiàng)與戍兵的緊張關(guān)系。可能兵變使夏州節(jié)度使內(nèi)部的勢(shì)力平衡被打破,所謂“凌慢愈甚” 應(yīng)指拓跋思恭的勢(shì)力受到了壓制。這成為拓跋思恭兵變的引子,“時(shí)朔方王集部下,伺隙盡擒誅之。公弟兄皆與其事”。
值得注意的是兵變中拓跋思恭勢(shì)力的構(gòu)成。“集部下”的概念相當(dāng)模糊,可以理解為教練使所部,也可認(rèn)為是黨項(xiàng)拓跋部,或者兼有。若要細(xì)究,“集”的字義傾向從分散到聚合的狀態(tài),這與教練使所部編制整齊的形態(tài)有些不符,認(rèn)為是教練使所部的話,文意顯然有難解之處。墓志接著說,“公弟兄皆與其事”,可知咸通年間兵變拓跋思恭“集部下”,其中就包含白氏兄弟。白氏家族在咸通年間就是拓跋思恭勢(shì)力的重要構(gòu)成,此后還參與了勤王戰(zhàn)爭(zhēng)。
二、拓跋思恭所部白敬立家族考
據(jù)《白敬立墓志》記載,白氏有兄弟五人。乾寧二年(895)任官如下:
公長(zhǎng)兄承襲,見任興寧府都督元楚。令兄忠信,檢校吏部尚書、前綏州刺史。令弟敬忠,檢校左常侍、充親從都兼營田使、洛盤鎮(zhèn)遏使、御史大夫。……其季忠禮,檢校右常侍。[4]85
白氏家族在定難軍中擔(dān)任官職,與其在拓跋思恭創(chuàng)業(yè)期間的重要貢獻(xiàn)有關(guān)。而其之所以受到拓跋思恭重視,關(guān)鍵是家族在夏州的深厚根基。墓志云:
公家自有唐洎九世,世世皆為夏州之武官。曾祖父字令光,年一百二十四歲,充興寧府都督,娶高氏,生祖父,字奉林,充興寧府都督,娶婆高氏。祖父字文亮,充興寧府都督,娶婆王氏,生公。③
白氏“世世為夏州武官”,確切而言是世襲“興寧府都督”[11]69。唐朝“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nèi)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lǐng)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8]1119。羈縻府州長(zhǎng)官世襲統(tǒng)領(lǐng)部落,享有相對(duì)獨(dú)立的權(quán)力。由此看來,咸通年間拓跋思恭“集部下”兵變所依托的武力中除了白氏兄弟,還有其興寧都督府部落兵。
關(guān)于興寧都督府,有兩種推理。一是黨項(xiàng)說,周偉洲認(rèn)為“興寧府都督”即是黨項(xiàng)“清寧都督府”[12]79,但并未給出推論的依據(jù),很可能是由于白氏為黨項(xiàng)拓跋思恭所部,且兩者都有寧字,有誤寫可能。但是《新唐書》記載“清寧都督府” 隸靈州都督府,與白氏“世世皆為夏州之武官”并不符合;且墓志中四次出現(xiàn)“興寧府都督”,撰志時(shí)白元楚“見任興寧府都督”,官職因襲有印信依憑,似乎不應(yīng)該出現(xiàn)誤寫。二是興寧府都督白氏為漢人。這種說法源于白氏墓志中南陽郡望的記載[5][6]。不過依據(jù)郡望判別族屬的前提是排除攀附的可能,從后晉吐谷渾《白萬金墓志》中自稱南陽郡望看,[13]160[14]636-637時(shí)至五代邊疆少數(shù)民族攀附南陽白姓的情況仍然存在。況且認(rèn)為夏州興寧都督由漢人世襲,與我們對(duì)羈縻府州制度的常識(shí)也有很大出入。這兩點(diǎn)是夏州白氏漢人說成立的關(guān)鍵,卻都無法考證。興寧都督府也有再考察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中有關(guān)興寧都督府的一組地理信息。白敬立“薨于夏州之故里”,白氏世代為興寧府都督,“故里”當(dāng)指興寧都督府治地。至于“故里”所在,墓志“葬地”信息中說“乾寧二年,葬于夏州朔方縣”,說明興寧府都督寄治夏州朔方縣。《白敬立墓志》出土于今陜西靖邊縣紅墩界鄉(xiāng)華家洼林場(chǎng)[4]83,85,在唐朝夏州朔方縣境內(nèi),與基于故里、葬地信息得出的地理位置一致。因此,朔方縣寄治的羈縻府州和內(nèi)附人群就成為解開興寧府都督的重要線索。
《舊唐書》記載云中、呼延州、桑干、安化州、寧朔州、仆固州等六都督府寄治朔方縣,其中云中、呼延州為黨項(xiàng)內(nèi)附部落[1]1414-1415。對(duì)此,《新唐書》的記載有三處不同,一是無呼延州,另有不明寄治的呼延都督府;二是云中都督府為突厥內(nèi)附部落;三是有兩個(gè)寧朔州,安置回鶻部落之寧朔州寄治朔方縣,與《舊唐書》同,代宗時(shí)的吐谷渾寧朔州也在夏州,寄治縣則不明確[8]1120。兩書分歧中需要指出的有二,云中都督府是貞觀四年(631)析頡利右部置,為突厥部落[1]5163;岑仲勉指出呼延州所分黨項(xiàng)部落可能有誤,吳玉貴進(jìn)一步指其所領(lǐng)三州中至少賀魯州、□跌州與黨項(xiàng)無涉[15]248[16]254。由此可知,朔方縣至少分布突厥、回鶻等內(nèi)附人群及其羈縻州。
寄治朔方縣的六都督府中寧朔州為回鶻、突厥種落。《新唐書》記載:“白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8]4594《新唐書》新增白元光傳,應(yīng)是根據(jù)私家傳、狀、譜牒采訪所得[17]658。據(jù)《白道生神道碑》:“(白道生)鎮(zhèn)在疆場(chǎng),統(tǒng)其蕃部,尋為寧朔州刺史兼部落主。”[18]4779[19]7白道生任職為“寧朔州刺史兼部落主”,那么“寧朔州”應(yīng)該是羈縻府州,并非相繼任寧州刺史、朔州刺史。前面提到,唐時(shí)有二寧朔州都督府,一為安置回紇部落,“寧朔州都督府僑治朔方”[8]1122;一為安置吐谷渾部落,“寧朔州初隸樂容都督府,代宗時(shí)來屬”[8]1125。吳玉貴認(rèn)為白道生“‘誕自朔漠’,則所統(tǒng)應(yīng)為回紇部落所置之寧朔州”④。這種觀點(diǎn)是合理的。同時(shí)也要注意到,白道生系突厥種落,碑文稱其“鎮(zhèn)在疆場(chǎng),統(tǒng)其蕃部,尋為寧朔州刺史兼部落主”。寧朔州都督府雖為安置回紇部落,應(yīng)該也有部分突厥部落。
安置回鶻部落的寧朔州都督府由突厥白氏世襲,“戶三百七十四,口二千二十七”,在朔方縣六都督府中戶口數(shù)第三[1]1414-1415,是夏州都督府內(nèi)的重要?jiǎng)萘Α8匾氖牵c白敬立家族世襲的興寧都督府一樣,都在朔方縣境。根據(jù)《新唐書》記載,代宗時(shí)原屬樂容都督府的吐谷渾寧朔州被安置在夏州。按照古代行政區(qū)劃通名原則,推測(cè)回鶻寧朔州都督府在代宗時(shí)期已經(jīng)撤銷或者改名了。又《白元光傳》云:“元光初隸本軍,補(bǔ)節(jié)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8]4594安史之亂前白元光還隸屬本部寧朔州。那么回鶻、突厥系寧朔州都督應(yīng)該是在安史之亂到代宗朝之間發(fā)生了整合。地緣、姓氏與首領(lǐng)身份提示我們興寧都督府的出現(xiàn)很可能與此有關(guān)。
之所以認(rèn)為兩者之間存在淵源,還在于白敬立與白道生家族之間的譜系關(guān)聯(lián)。《白元光傳》云:“白元光字符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bǔ)節(jié)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其后歷靈武留后、定遠(yuǎn)城使。貞元二年卒,贈(zèng)越州都督。”[8]4594白元光主要活動(dòng)在安史之亂(755)到貞元二年(786)間,生年應(yīng)在8世紀(jì)初期。世襲興寧府都督的白敬立家族曾祖白令光不單名字與白元光(或符光)相聯(lián),生活年代亦有交集。《白敬立墓志》記載:“曾祖父字令光,年一百二十四歲,充興寧府都督,娶高氏,生祖父,字奉林,充興寧府都督,娶婆高氏。祖父字文亮,充興寧府都督,娶婆王氏,生公。”[4]84白敬立與白令光之間有兩代興寧府都督繼任,若以白敬立卒年乾寧二年(895)為基準(zhǔn),按一代二十年至三十年推算,白令光生卒年當(dāng)在835—855 年間,白令光“年一百二十四歲”則其生年當(dāng)在711—731年間。與白元光的生年相近,生活年代有很多重合。名字和生存年代的關(guān)聯(lián)顯示,白元光與白令光很可能是具有血緣關(guān)系的同輩。
更為重要的是兩者間的郡望。《白道生神道碑》中白元光“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8]4594。白氏望出南陽、太原,其中南陽為武安君白起郡望[20]91- 92。漢唐時(shí)期封爵傳統(tǒng)中郡望是重要依據(jù)[21]。唐朝重視氏族譜系,白元光封爵南陽郡王,說明突厥系白元光家族是以南陽作為郡望的。這也恰恰與《白敬立墓志》中的族源書寫吻合。
公諱敬立,字□,秦將軍武安君起之后。武安君將秦軍,破楚于鄢郢,退軍筑守于南陽,因而號(hào)其水為白水,始稱貫于南陽。武安君載有坑趙之功,為相君張祿所忌,賜死于杜郵。其后子孫淪棄,或逐扶蘇有長(zhǎng)城之役者,多流裔于塞垣。[4]84
白敬立家族與白道生家族居地、郡望一致,世系關(guān)聯(lián),都是羈縻府州首領(lǐng),說明興寧都督府與回鶻、突厥系的寧朔州都督府之間存在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前者應(yīng)該是在后者基礎(chǔ)上整合而來。這種調(diào)整應(yīng)該發(fā)生在安史之亂后到代宗朝之間,很可能與仆固懷恩叛亂引起的民族政策調(diào)整有關(guān)。
三、拓跋思恭勤王戰(zhàn)爭(zhēng)中的番將
白敬立在拓跋思恭擔(dān)任夏州教練使時(shí)就親隨左右,咸通年間的政變白氏家族都參與其事。其之所以能有如此地位,當(dāng)然是由于家族世襲回鶻、突厥系的興寧都督府。換言之,最晚到咸通年間,白氏家族與其興寧都督府已成為拓跋思恭勢(shì)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黃巢占據(jù)長(zhǎng)安后,“王自宥州刺使率使府將校,統(tǒng)全師問安赴難,及于畿內(nèi)。公時(shí)以親信從”。拓跋思恭起兵勤王時(shí),白敬立以親信將領(lǐng)隨從。“及收復(fù)長(zhǎng)安,王獨(dú)憐公之功,升居右職。命幕下為獎(jiǎng)飾之詞云:破黃巢于咸陽原上,非我不存;避洪濤于鄜畤城南,唯爾之力。時(shí)皆謂趙襄子舉高共,蜀先主得孔明,擢終始之功,言魚水之道,不過于此。”[4]84白敬立榮寵如此,肯定與其謀略過人有關(guān),更與突厥、回鶻系興寧都督府部落兵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作用脫不開干系。
傳世和出土文獻(xiàn)中記載有黨項(xiàng)拓跋部參與勤王的將領(lǐng)。《宋史》李繼遷世系云:“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于渭橋,表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zhàn)沒,僖宗贈(zèng)宥州刺史,祠于渭陽。”[22]13985由此可知,隨拓跋思恭勤王者當(dāng)有其弟拓跋思忠。另外,據(jù)《李彝謹(jǐn)墓志》載其祖:“思□,皇任京城四面都統(tǒng)教練使。”⑤京城四面都統(tǒng)教練使應(yīng)該是“思□”參加勤王時(shí)的官職。由此可以推測(cè),拓跋家族“思”字輩在勤王戰(zhàn)爭(zhēng)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在平定黃巢之亂后“思”字輩的將領(lǐng)的政治安排中也有反映。不難知道,拓跋家族所領(lǐng)黨項(xiàng)部落兵應(yīng)是“夷”兵的核心。
黨項(xiàng)部落兵中除了我們知道的拓跋部外,還有其他部族。據(jù)《李彝謹(jǐn)墓志》世系記載:“曾祖諱重建,皇任大都督府安撫平下番落使。曾祖妣破丑氏,累贈(zèng)梁國太夫人。祖諱思□,皇任京城四面都統(tǒng)教練使。”[4]130關(guān)于“思□”,前文已提到是拓跋思恭勤王時(shí)期的重要將領(lǐng)。值得注意的是,其父拓跋重建,任大都督府安撫平下番落使。大中年間平息黨項(xiàng)之亂后,“夏州節(jié)度使增領(lǐng)撫平黨項(xiàng)等使”[8]1785,安撫平下番落使的設(shè)立可能與此有關(guān)。拓跋重建與破丑氏聯(lián)姻表明,早在拓跋思恭勤王前拓跋部與破丑氏的聯(lián)系就相當(dāng)緊密。拓跋重建與破丑氏之子思□率軍勤王時(shí),所部包括有破丑氏部落是情理之中的,也應(yīng)是拓跋思恭所部“夷”兵之組成部分。
勤王前拓跋部已經(jīng)通過聯(lián)姻整合其他部落。五代宋初的定難軍墓志中仍有節(jié)度使與破丑氏的聯(lián)姻記載。在《白敬立墓志》中也看到類似的情況,“十七娘,適事王門,郎君司空”[4]85。以興寧府都督為代表的突厥、回鶻系等首領(lǐng)與破丑氏為代表的黨項(xiàng)他部酋長(zhǎng)以聯(lián)姻的形式成為拓跋思恭勢(shì)力的重要部分,這種聯(lián)合在起兵勤王前就存在,是勤王軍中“夷”兵的主要來源。
此后文獻(xiàn)常稱定難軍武力為“雜虜”。《舊唐書》記載:“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fā)自京師。”[1]4658[23]3652定難軍時(shí)期的何德璘家族、康成家族均為粟特人[24]。其中何氏于開平二年(908)就已繼職軍門[4]102,康成家族亦世為夏州武將[4]112。長(zhǎng)興四年(933)后唐軍隊(duì)進(jìn)攻夏州,李彝超“遣其兄阿啰王守青嶺門,集境內(nèi)黨項(xiàng)、諸胡以自救”[2]9083-9084。《資治通鑒》所記戰(zhàn)報(bào)云:“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shù)千騎救之,安從進(jìn)遣先鋒使宋溫?fù)糇咧!保?]9084此處劉敬瑭、阿啰王所率定難軍武力被稱為“諸胡”、“雜虜”。可見拓跋李氏對(duì)境內(nèi)番部的整合在擔(dān)任定難軍節(jié)度使后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但是從拓跋思恭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存在了。換言之,起兵勤王前以黨項(xiàng)拓跋部為主體、族群成分多元的區(qū)域勢(shì)力已有初步發(fā)展。
四、結(jié) 語
咸通年間接連發(fā)生的兵變是影響夏州政治局勢(shì)的大事件。先是征防卒發(fā)動(dòng)兵變,獲得定難軍馬步都虞候的重要職務(wù),這使得定難軍原來的政治平衡被打破。重組后的節(jié)度使政權(quán)采取了針對(duì)拓跋思恭勢(shì)力的打壓政策,這導(dǎo)致了拓跋思恭勢(shì)力反抗,很快發(fā)動(dòng)第二次兵變。征防卒與拓跋思恭的矛盾,很可能是不久前會(huì)昌、大中年間平夏、南山黨項(xiàng)之亂的余波。透過雙方勢(shì)力較量,可以觀察到拓跋思恭早期勢(shì)力的構(gòu)成。
興寧府都督白氏家族是拓跋思恭兵變的重要支持者,又隨從起兵勤王。通過對(duì)白敬立家族郡望、世系、居地、任官的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他跟該地的另一支白姓——白道生家族有著諸多相關(guān)性,興寧都督府與回鶻、突厥系寧朔州都督存在淵源關(guān)系。這只回鶻、突厥系的勢(shì)力參與拓跋思恭兵變、勤王等創(chuàng)業(yè)過程,是拓跋部勢(shì)力的重要部分。當(dāng)然,從勤王戰(zhàn)爭(zhēng)中將領(lǐng)和事后的政治安排看,拓跋部黨項(xiàng)仍是拓跋思恭勢(shì)力的核心,不過其中已聯(lián)合了部分破丑氏部族。從勤王時(shí)的“夷”兵看,拓跋思恭早期的勢(shì)力構(gòu)成并非單是黨項(xiàng)拓跋部,已經(jīng)成為突破黨項(xiàng)拓跋部、擴(kuò)展到黨項(xiàng)其他部族集團(tuán),甚至其他族群的區(qū)域勢(shì)力了。拓跋思恭勤王軍隊(duì)中的漢人,前引《通鑒》中有明確的記載。結(jié)合《白敬立墓志》的記載,“王自宥州刺使率使府將校,統(tǒng)全師問安赴難”。勤王軍中有宥州戍守的軍隊(duì),這說明拓跋思恭擔(dān)任宥州刺史后所部漢人逐漸增加了。而此前拓跋思恭勢(shì)力中的漢人成分目前還不易考訂。
注釋:
①全稱為《故延州安塞軍防御使檢校左仆射南陽白公府君墓志并序》,為引用方便,本文一律稱為《白敬立墓志》。收于杜建錄《黨項(xiàng)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4頁。另外,本文使用墓志錄文以《黨項(xiàng)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為底本,并參考《榆林碑石》、《中國藏西夏文獻(xiàn)》等,若無錄文修訂一般不標(biāo)注參考文獻(xiàn)與原圖版出處。參見康蘭英主編《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75、242 頁;寧夏大學(xué)西夏學(xué)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甘肅省古籍文獻(xiàn)整理編譯中心主編《中國藏西夏文獻(xiàn)》第18 卷《金石編、碑石、題記》,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7年。
②杜建錄《黨項(xiàng)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第84頁。另外據(jù)圖版,“之”后字應(yīng)為“間”,改正,參見寧夏大學(xué)西夏學(xué)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甘肅省古籍文獻(xiàn)整理編譯中心主編《中國藏西夏文獻(xiàn)》第18 卷《金石編、碑石、題記》,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27頁。
③按照志文結(jié)構(gòu),“祖父字文亮”應(yīng)為“父字文亮”。詳見杜建錄《黨項(xiàng)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第84頁。
④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下編《突厥第二汗國歷史編年輯考》,中華書局,2009年,第1235頁。王義康考證興寧府都督時(shí),已提到夏州尚有白道生所領(lǐng)羈縻府,但是并未論證兩者的關(guān)系。參見氏著《唐代邊疆民族與對(duì)外交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9頁。
⑤杜建錄《黨項(xiàng)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第129 頁。墓志所載“思□”的身份,諸家存在爭(zhēng)議。一種是認(rèn)為其當(dāng)為“李思恭”。(參見鄧輝、白慶元《內(nèi)蒙古烏審旗發(fā)現(xiàn)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銘考釋》,《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384頁;周偉洲《早期黨項(xiàng)史研究》,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4年,第252 頁;杜建錄、白慶元、楊滿忠、賀吉德《宋代黨項(xiàng)拓跋部大首領(lǐng)李光睿墓志銘考釋》,《西夏學(xué)》2006年第1輯,寧夏人民出版社,第83頁。)另一種以湯開建為代表,認(rèn)為可能是“李思孝”。(參見湯開建《隋唐五代宋初黨項(xiàng)拓跋部世次嬗遞考》,《西夏學(xué)》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1-102頁。)從現(xiàn)有材料看,湯氏對(duì)“李思恭說”的否定是合理的,不過是否為“李思孝”尚需更直接的材料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