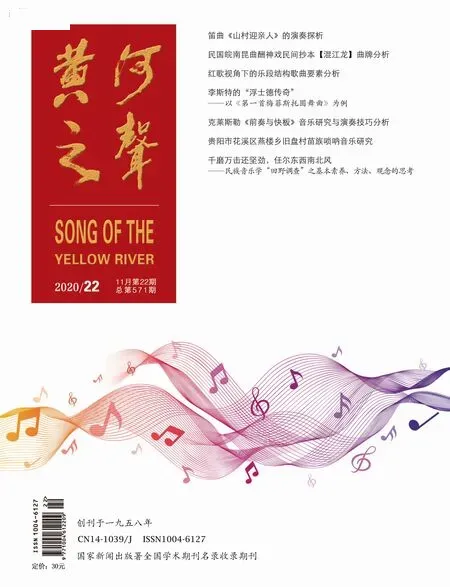音樂與心的文化解讀
◎ 王忠秀 (貴州師范大學)
《樂記·樂本篇》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是說音樂是人心的外顯。人類的文化組成成分多種多樣,其中“道德、藝術、科學,是人類文化中的三大支柱”[1],中國在道德與藝術兩個領域的成就最為顯著,深度挖掘和發展這兩大擎天之柱對中國甚至對世界來說意義非凡。徐先生說“中國文化的藝術精神,窮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莊子所顯出的兩個典型”[2],且是心的文化,即孔子的“仁心”和莊子的“虛靜之心”,兩家歸根結底都是為“人生而藝術”。音樂屬于眾多藝術門類中的一類,其實是可以用“仁心”“虛靜之心”來解讀的,作曲家在什么樣的心境中進行音樂創作;表演者用何種心情去演繹音樂作品;觀眾用何種心情去鑒賞音樂,鑒賞時又產生了什么樣的聯覺效應等問題,都與“心”息息相關,從徐先生的“藝術之心”來看,音樂其實就是人的生命精神。
一、仁心與音樂
孔子認為音樂具有教化作用主要表現在音樂可以引發人的仁心,當一個兒童聽到《韶》時如果能“其視精,其心端”,從內心深處受到音樂的感動,從而使自己的修養行為趨向于仁和善,從人生最根源處就受到影響,積極向上、那么人格就能得到提升和完善。比如當我們聽到電視劇《媽祖》的片尾曲中唱到“風里浪里,你救苦救難,恩義昭昭,如日月高懸”時,我們心里會立刻閃現媽祖為拯救處于水深火熱中的蕓蕓眾生,甘愿耗盡自己的神力、魂歸混沌等片段,她大愛無疆的行為、美麗圣潔的形象讓人永遠銘刻于心,在各種快餐娛樂文化“噴井”而出的今天,這樣的音樂聽之能讓人心變得安寧祥和、平靜柔軟,感動之余也會不自覺地引發自己的善良和博愛之心,這正是孔子所提倡的音樂的教化作用,徐先生指出,孔子強調“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可見音樂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欣賞善美協和的音樂能引發人的仁愛之心,能使一個人的人格達到最高境界。
孔子對《韶》“盡善盡美”的肯定,表明“善”與“美”的統一是儒家對音樂評價的最高標準。古代的中國,在道德和生理欲望的圓融中,仁對于一個人來說,“不是作為一個標準規范去追求它,而是情緒中的享受”[4],“仁”是人們自然而然的內心流露,人們在被音樂洗禮的過程中既完成“仁心”的修煉也獲得了精神上的愉悅。儒家“用藝術的形式將藝術家對社會的責任感的充分感知展現出來”[3],那么這里的音樂文化,就成了一種載體,傳達著藝術家們的意愿,正是音樂的社會功能得以淋漓盡致的體現,譬如我們聽到《飄零的落花》中“天涯何處是歸程,讓玉消香逝無蹤影,也不求世間與同情”時能深切體會到詞曲作者劉雪庵先生作為舊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戰亂年代充分承擔起了為民擔憂、為國奔走努力尋求解放之法的重大責任,歌詞看似在描述風中飄零散亂的落花,實際上卻賦予了人的感情,暗示劉雪庵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仍然堅守自己的品格和信念,他堅信戰爭終將取得勝利,因此即使身處險境也不隨波逐流、不向黑暗勢力低頭、更不渴求能得到世間的同情。他的這種我為人人、大義凜然的仁愛之心全都呈現在歌曲中,不管是作為演唱者還是聆聽者,都能被音樂中所傳達的家國情懷深深打動。
可見用孔子的“仁心”來解讀音樂不僅適用于古代中國,對當前乃至未來人類藝術文化的正常發展和藝術風氣的改善都有積極作用,“仁心”就像一面道德的標桿,能夠指導和規范人們的日常行為,無論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科技、文化、法律等發展到何種程度,人類對道德的修煉和所需要達到的高度只增不減,社會永遠需要善良和正義。作曲家們用一顆“仁義道德”之心去進行音樂創作,鑒賞者帶著“仁義善良”的心去聆聽和品味音樂,精神和思想漸漸被淘洗得干凈純粹,人心平和了,社會自然就能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
二、虛靜之心與音樂
莊子的“虛靜之心”對音樂的作用主要表現在鑒賞上,所謂“虛靜之心”,其實就是心靈的觀物境界,徐先生指出要達到這樣的程度,全在于藝術家個人極高的藝術修養,莊子所生活的時代動蕩不安,無論是社會環境還是政治環境,都不能使人生得到安寧,必須要“忘己喪我”,使思想能“遊”,成為“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使心達到“虛靜”。莊子的初心不在于把“美”做成一個標桿去刻意為之,“去加以思考、體認,更不曾把某種具體藝術作為他追求的對象”[4],徐先生認為莊子旨在“體道”,經過“心齋”與“坐忘”兩個過程的修煉,形成美地觀照,以心觀物時就能達到主客合一的境界。心在沒有目的和功利追逐的情況下,才能讓精神得到解脫和超越,才能成為純知覺活動的美地關照,用美地觀照來鑒賞音樂,常常能發現音樂本體以外的另一種意境傳達,能滋養和升華人的心靈。
比如當我們聽《云水禪心》時,如果身體放松、心無雜念,在我們的意識里,可能會產生這樣的聯覺效應:自己身處一片幽深寧靜的竹林中,山水掩映、煙波浩渺,心靈時而遨游云端、時而休憩泉底,這種欣賞音樂的心情,不正是莊子的“虛靜之心”么!再比如藝術歌曲《關雎》曲風唯美、旋律悠揚婉轉,讓人聽之回味無窮。“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優美的旋律一出,讓人仿佛看見河水中央相互嬉戲的雎鳥愜意的畫面,感受到謙謙君子對窈窕淑女獨特的情愫和歆慕之情,更有一種求而不得的遺憾。如果我們沒有一顆虛靜空靈的心來聆聽《關雎》,我們勢必會錯過這樣美妙的情感體驗。
徐先生還指出,現象學中的純粹意識是為了求得知識的根據暫時選擇忘知,帶著目的性,不是干凈而純粹的,“現象學之于美地意識,只是倘然遇之;而莊子則是徹底地全般的呈露。”[5]莊子的心齋之心才是真正的藝術精神主體。因此用純粹意識來鑒賞音樂,勢必會受到干擾,或者帶著某種意圖,而莊子看中“純素的人生與美,其本意只關注人生,而根本無心于藝術”[6],用自由的寬廣的“虛靜之心”來鑒賞音樂,常常會聽到弦外之音,精神上也會收獲意外之喜。
三、藝術之心與音樂
徐先生的“藝術之心”強調所有的藝術都是表現生命的,“藝術精神”即人的生命精神,《樂記》中提出的“音由心生”也充分體現音樂是人的生命精神。縱觀《中國藝術精神》一書,儒家文化只占了前兩個章節,第三章以下都是對莊子的論證,因此曾有學者指出徐先生有“重道輕儒”的傾向,其實從第一章的內容來看,徐先生并沒有這樣的傾向,他從音樂的角度入手,用音樂這把鑰匙去探索和挖掘孔子的藝術精神。其次,他認為繪畫是莊子的“獨生子”,并提到“歷史中的大畫家、大畫論家,他們所達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莊學、玄學的境界”[7],山水畫的空明澄遠、素雅高潔,能讓人觀之暫時忘憂、精神獲得片刻自由,生命負累得以減輕。他提煉出孔子和莊子兩個典型,不難看出他的意圖其實是想讓儒家的“仁義道德”與道家的“虛靜心齋”能夠匯通共融,成為一種有人的生命氣息的藝術。
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先生首次聽到《二泉映月》時感慨到:“這樣的音樂應該跪下來聽”。他與阿炳素未謀面,不了解阿炳其人其事,更不知《二泉映月》的創作背景,但是前奏嘆息性的幾個音一出來,立刻使他感動得熱淚盈眶,再次證明音樂是無國界的,也可見這首曲子準確地表達了阿炳的心聲,憑著兩根二胡琴弦,拉出了他對坎坷身世的呻吟、對悲慘命運的慨嘆,《二泉映月》正是阿炳生命精神的體現。再比如當我們聽到《琵琶語》時,清脆又哀婉的旋律總是讓人覺得無比傷感,我們會聯想到一個深閨女子,因與意中人難以相見,相思幾萬重,于是她輾轉反側,只能在夜深人靜時對月撥弦,遙寄思念。讓人不禁想到曲作者林海,他一定多次深入江南水鄉去采風,一定聽過無數個感人的故事,他一定是一個細膩又敏感的人,否則不會寫出這樣精妙且深情的曲子,只是簡單的彈撥,只是純純的單音色,就讓人看到了一段凄美的愛情故事,《琵琶語》正是林海藝術生命精神的體現。
現代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加深人們的功利心和焦灼感,善美協和的音樂在今天能讓人平心靜氣、撫平生活帶來的創傷與焦慮,這樣的音樂正是徐先生“藝術之心”的代表,它就像一杯甜潤的清涼飲料,療愈了現代人的浮躁之心。
結 語
音樂在孔子的“仁心”、莊子的“虛靜之心”及徐先生的“藝術之心”中的解讀證實了音樂是屬于“心的文化”,用“仁心”來解讀音樂,心靈能夠在音樂中得到感化,使人趨向于善和美,充分體現了音樂的功能性;用“虛靜之心”來鑒賞音樂,能使人產生多種聯覺效應,獲得音樂本體以外的意境傳達和審美體驗,充分體現了音樂的鑒賞功能;用徐先生的“藝術之心”來聆聽音樂,則讓我們體會到,音樂就是曲作者的生命寫照,聽音樂作品就是在聽曲作者內心真正的聲音,他提出“藝術精神”這個概念在中國是開先河性的創舉,因此有學者評價“在中國現代美學及藝術發展史上,明確標舉‘中國藝術精神’并以專注力度去展開深入學理論證的,徐復觀是第一人”。[8]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帶來了諸多弊端,音樂作為眾多藝術文化中最重要的一員,為人們在精神方面提供了一個休憩之所,在維持人類社會的平衡與正常發展中,音樂顯示出了它獨特的魅力與作用。音樂對道德的融合、對政治的宣傳教化功能,最終都體現為人的意愿和志向,人們創造音樂,演繹音樂,都是將內心的聲音和情感表現出來,音樂就是人們生命的活動,就是人的生命精神,就是心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