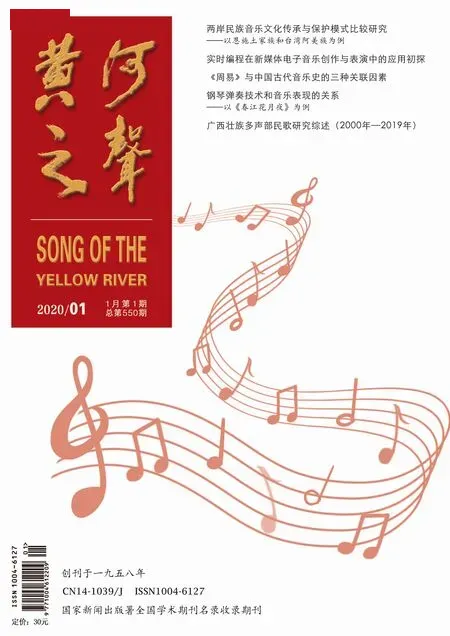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研究綜述(2000年—2019年)
◎敖雪瑩 (廣西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
壯族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壯族民歌是壯族人民賴以生活和勞作的優秀文化積淀,歷經千年的風雨,生生不息。廣西壯族民歌按聲部可以劃分為單聲部民歌和多聲部民歌,其中多聲部民歌因其獨特的多聲性思維和文化內涵而引發各界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起源于原始社會時期的集體生活,在勤勞智慧的壯族人民的長期農耕勞作和各種風俗活動中創造并不斷發展著。雖然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歷史悠久,但由于大部分民歌的傳承方式是口傳心授,因而許多音樂資源無形地流失了。上世紀50年代學者開始發掘壯族多聲部民歌,80年代后加大了民歌采集的力度和范圍,在廣西各地區發現了不同種類的豐富多彩的壯族多聲部民歌。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和經濟的發展,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拓寬了學術視野,研究視角走向多元與開放。筆者梳理了2000年至2019年間的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研究相關文獻,按內容將其歸納為三個部分,即藝術特征研究、審美內涵研究和文化生態研究,旨在通過整理歸納新世紀的研究成果把握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研究現狀和趨勢。
一、藝術特征研究
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以二聲部為主,三聲部次之,四聲部偶見,其藝術特征研究主要基于當下采錄的活態山歌,其研究成果表現了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獨特的音樂思維,尤其體現在音樂的支聲性和唱詞唱腔方面。
研究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支聲復調思維的有張升浩《論廣西多聲部民歌中的支聲現象》(2011)和邱晨《論廣西多聲部民歌的復調結合及其在復調教學中的運用》(2011),兩者都運用了壯族民歌材料分析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支聲性形態及特點。黃憲發表的《多聲部重唱的徵調套曲——廣西平果壯族嘹歌曲調研究》(2010)總結了平果嘹歌的曲調特征并進行了個案分析,其曲調大多為徵調式,旋律表現出抒情性和詩意性。多聲部民歌在音樂的調式體系以及和聲特征的比較分析研究有戴偉的《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和聲特征研究——以平果哈嘹<時逢好年景>與馬山三頓歡<孤苦吟>為例》(2018)。
民歌的唱詞唱腔研究包括江西師范大學湛晨的碩士論文《廣西平果縣壯族嘹歌雙聲合唱研究》(2017)闡述平果縣壯族雙聲合唱的音樂形態及其唱法,進而理解嘹歌雙聲合唱的審美觀念及線性思維。中國音樂學院徐冉的碩士論文《拆跨、行腔——壯族嘹歌腔詞關系初探》(2018)研究壯族嘹歌的腔詞關系,從而更深入地理解壯族嘹歌的審美原則。
音樂和唱詞的內在關系的研究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有部分研究在音樂方面也不僅限于對旋律、節奏、調式調性、曲式結構等表層音樂特征的描述,而是綜合分析拓深音樂本體研究的意義。丁蜀還《廣西上林縣壯山歌的語言與山歌探究》(2011)探討了以二、三聲部為主的上林壯山歌其音樂的旋律和唱詞語音聲調的關系。
綜合性研究有范志國的《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形態管窺》(2010),通過分析民歌演唱聲部情況、音樂結構形態特點、旋律骨干音和裝飾音的特點、和聲與音程的運用及解決試圖尋找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音樂形態的共性。中國音樂學院郭婧的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平果縣嘹歌音樂形態調查研究》(2012)對多聲部平果嘹歌的音樂本體作出了系統的分析,包括了歌詞和音樂形態各部分的研究。楚卓、廖琨銘《論壯族三聲部民歌樂聲形態之美》對馬山壯族三聲部民歌的音樂形態作了系統的分析。林慧思《龍江河流域壯族山歌藝術特征研究》(2014)以龍江河流域的北路壯族二聲部山歌為研究對象,分析其音樂本體的藝術特征。從整體來看,研究者對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音樂形態研究抱有極大的興趣,同時已不滿足于對某地民歌進行單純的藝術特征分析,而是把握藝術特征的內在動力,致力于發掘其深層規律,探尋其生發原因和過程。這一研究傾向立足于音樂研究本身,同時運用了跨學科知識對音樂本體進行分析,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剖析民歌音樂自身發展的原動力。這一研究現象雖然不普遍,卻有了積極的發展趨勢。
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顯現了壯族人民作為獨一無二的中國少數民族群體在生活中所產生的創造力和凝聚力,以及音樂對其產生的向心力。把握民歌藝術特征發展的變化亦是反映民歌文化變遷的極其重要的部分。對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藝術特征的全面觀照是研究其產生和傳播所形成的文化和歷史蹤跡,并從這些蹤跡中回到探索其音樂本質的“唯一”路徑。
二、審美內涵研究
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美學內涵可以從不同維度進行探究。從微觀視角來看,不同的地域特點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進而導致不同文化群體的審美觀念的差異,文化的變遷賦予群體整體上的觀念的演變,即同一個群體的審美觀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化,但其本質的特點不會脫離其本質的文化。從宏觀視角來看,民歌的審美內涵研究可以向更廣闊的領域和更深刻的思想延伸。
覃彩鑾《論壯族<嘹歌>藝術的美學價值——壯族<嘹歌>文化研究之六》(2005)從嘹歌的形式美、內涵美、社會美探討嘹歌藝術的美學價值及美學特點。廣西師范大學蔣劍的碩士論文《壯族嘹歌歌圩文化及其審美內涵研究》(2008)以審美人類學的視角考察嘹歌歌圩,進而探討其美學內涵,包括了嘹歌象征文化權利、尚歌的審美價值觀、反叛世俗之美、兩性和諧之美以及情感欲望表達的需要。李樹鋒《壯族嘹歌的審美意蘊》(2008)意在通過闡述嘹歌的韻律美、意象美和質樸的人性美來挖掘嘹歌的藝術性。黃金《廣西壯族三聲部民歌藝術特征折射出的民族個性》(2018)從壯族三聲部民歌的藝術特征入手闡述其蘊含的美學思想,從而進一步了解壯族最深層的文化精神。
范秀娟發表了多篇含有壯族多聲部民歌的美學思考的文章,《少數民族審美文化資源與當代中國美學的建構》(2008)提出對少數民族藝術文化審美研究的缺乏和必要性,闡述了壯族多聲部民歌誕生和發展于古老的群體社會,壯族單聲部民歌起源晚于多聲部民歌。從審美人類學的角度,她認為壯族多聲部民歌發展到單聲部民歌是經歷了從“集體性強、復雜嚴謹”到“更為自由”的過程,這一過程與文化根基以及社會變遷有著密切的聯系,并認為音樂是內在于人們的活動中。這一分析顯現了當下的民歌文化與歷史對話所產生的藝術起源和歷史發展中的美學思想。《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歌:美學意義及啟示》(2008)也有關于黑衣壯二聲部民歌“詩敏”中的大二度和聲的使用充滿了和諧悅耳的地域性特色,而一般的專業音樂工作者使用大二度和聲則顯得刺耳,多聲部民歌的美學內涵在不同的語境之下蘊含著不同的精神要素。可以看出表面上相同的某些音樂特性置于不同語境之下時其深層含義便會發生改變。《民歌與當代美學問題》(2009)提出民歌的美學研究要結合民俗學、語言傳統和文化環境,闡述黑衣壯二聲部民歌具有“日常生活審美化”性質的聽覺美感,是一種貴族的藝術和高貴的藝術,黑衣壯民的歌唱態度是純審美性的,純精神超越性的。
綜上,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審美研究主要涵蓋了音樂形式之美、人文內涵之美、本質精神之美等,既有微觀上對民歌群體審美特征的研究,也有從宏觀上把握民歌審美發展的研究。民歌的美學內涵探究是對于民歌科學邏輯性研究基礎上的感性和內化因素的理解與吸收,即從民歌本體的特征與規律、發展歷程的客觀事實、干擾外因的合理推論中歸納出民歌自我成長的動機因素以及內涵和外延。民歌的審美內涵也是群體的審美意識中反映出的對民歌的理性和感性的認識的綜合體現,包括民歌的功能性、氣質形象、核心精神等要素。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審美意識根植于廣西壯族這片土地和這一族群所孕育的文化傳統,迄今關于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審美意識的專門研究并不多見,但學者們已然明晰要研究民歌審美意識需立足于廣西壯族歷史發展的狀況、文化變遷的成因、社會群體的民族心理和個體心理等各方因素,并結合跨學科理論和知識深入探尋。
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美學內涵的研究亦是打開探索其地域文化的有效窗口,民歌中所蘊含的不論是美妙音樂、豐富知識或人文氣質等都為研究當地的文化生態的發展和變遷提供了多維度的解讀方式。民歌的審美思想不止一家之言,也非一成不變,正是如此,動態多變的審美觀才使得當下的民歌的研究閃爍出多樣的光彩。
三、文化生態研究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研究在探索其文化生態方面可謂是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究其原因,社會環境的不斷發展和變化為民歌的研究提出了新世紀的命題和任務。在科技愈益發達、經濟形勢迅猛的今天,民歌的發展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轉型期,其內容和深層含義也處于更新之中。
歷史見證了民歌的變遷,因為歷史蘊含著民歌發展適應性的因素——環境的選擇,這是民歌適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結果,當然也反映出文化生態的特性。以史學視角研究的有鄭超雄《壯族<嘹歌>的起源及其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2005)分析了文學作品《嘹歌》的起源于《越人歌》甚至更早,并發展成熟于明朝時期。李萍《從廣西平果嘹歌看壯族原始宗教信仰》(2011)通過平果嘹歌介紹壯族先民經歷了從自然崇拜到圖騰崇拜到祖先崇拜的信仰歷程,反映了壯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金萌《壯族嘹歌的文化淵源》(2018)回顧壯族嘹歌的原生文化背景,回溯其發展的源流。
研究民歌存見之下的文化生態變遷包括陸裴《文化適應:社會變遷中靖西山歌文化的選擇》(2006)闡述靖西山歌(包括多聲部山歌)在當下的文化多元和碰撞的趨勢中產生了文化適應性,并構成了文化轉型。廣西民族大學洪貴春碩士學位論文《“歌化”的生活——平果壯族嘹歌文化變遷研究》(2015)以文化生態學理論從嘹歌文化生態的各層次對文化系統變遷進行分析研究,包括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和心態文化層,還探討了嘹歌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中央音樂學院白雪的博士論文《音聲—社群形態互構——右江流域平果壯族嘹歌及歌圩活動研究》(2015)從民族音樂學的方法探討右江中游流域所滋養的壯族嘹歌文化,研究在傳統文化背景下社群和音聲是如何相互構建的,以及音樂的功能意義在現代社會變遷中發生的變化,以流域人類學的視角觀察音樂與人、音樂與生態和經濟的互動關系。
美國生態學家朱利安·H·斯圖爾特認為文化生態學就是對一個社會適應其環境的過程進行研究。它的主要問題是要確定這些適應是否引起內部的社會變遷或進化變革。①顯然,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是適應環境發展的產物,并在此過程中引發了不同形式的變革,民歌烙印著時代的印記。在新世紀,學者們針對民歌的發展趨勢作出了判斷,并提出了相應的改善措施。
側重于探討民歌的傳承和發展趨勢的研究有白翎的文章《廣西黑衣壯民歌的傳承與發展》(2005)探討廣西黑衣壯民歌的傳承方式、保護作用和發展等。毛艷《論廣西平果壯族嘹歌的保護與傳承》(2008)提出了平果嘹歌的保護和傳承的設想。蔣興榮《對南寧國際民歌節后黑衣壯歌謠重建的思索》(2009)認為傳統民歌的發展需要基于當地的文化,借助文化資源優勢和科技手段并提高自覺意識達到傳播和延續民歌文化的目的。韋惠玲《邕寧壯族嘹羅山歌的傳承和發展研究》(2012)論述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背景下邕寧壯族嘹羅山歌的傳承和發展。程艷、楊洋、高紅艷《文化生態視域下廣西馬山壯族三聲部民歌的傳承和發展》(2013)闡述馬山壯族三聲部民歌的文化生態價值、傳承和發展現狀。何穎、傅桂群《以原創特色激活文化品牌,以人文生態亮化自然生態——廣西特色民歌“壯族三聲部”文化產業規劃思路》(2013)創建馬山壯族三聲部民歌產業,作為馬山縣的特色文化的三聲部民歌有助于馬山文化品牌的形成和產業的發展。李常新《廣西平果壯族嘹歌歌書的傳播形態研究》(2014)研究嘹歌歌書作為傳播嘹歌文化的媒介與符號在嘹歌的傳承發展中的價值。李德彪《壯族多聲部山歌納入高師聲樂課程教學的思考》(2014)提出在高校進行壯族多聲部山歌的教學以發展我國民族聲樂。梁肇佐、李慧《馬山壯族三聲部民歌生存現狀調查分析》(2015)介紹了馬山壯族三聲部民歌的概況和發展趨向。
通過閱讀相關文獻,二十一世紀的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目前所生存的社會環境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社會發展以經濟發展為主導。這一導向對民歌發展的影響巨大,其負面影響是傳承人數量的驟減,青年人多選擇外出務工,經濟的充裕給他們帶來的安全感已勝過唱民歌所帶來的滿足感;生產力的提高逐漸弱化了民歌的功能性,民歌的功能向純粹的審美體驗過渡。二是全球信息大量涌入造成了文化沖擊。進入海量信息的“互聯網”時代,人們的娛樂活動和生活工作被大量外界信息所充斥,已難以集中專注于民歌的傳承發展。三是民歌傳承發展的制度體系不完善。在外力作用下民歌的傳承和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遇到了不少問題,制度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勢在必行。
針對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目前所處境況,總結研究者們提出的傳承保護措施主要集中在建立文化產業鏈、發展民歌傳承人和民歌進課堂三方面。文化產業鏈也可稱為發展文化品牌,將民歌打造成當地旅游文化產業的一個亮點,使民歌和當地其他代表性文化資源相結合形成當地的文化發展體系。發展民歌傳承人即利用政府經費或補貼促進人們踴躍學習民歌,各種形式多樣的民歌比賽也鼓勵了歌手們的學習熱情,要讓歌手們意識到民歌的重要性,并從內心認可和喜愛民歌。民歌進課堂有多種方式,可以請歌手們在校園里授課,傳授原汁原味的壯族多聲部民歌;也可以將民歌改編進教材,讓中小學生從小學習并認識不同的民歌,培養他們興趣和好奇心;還可以通過鼓勵創作來運用和傳播多聲部民歌,創作的范圍不限,可以結合現代的音樂元素進行實驗和創新。
當下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所處的文化生態環境復雜多樣。民俗生態下的民歌發展趨于多元化;教育生態下的民歌發展步入專業化;傳承生態下的民歌發展走向商業化。民歌的發展是順應時代的產物,其形式和內涵的衍進也是自身發展的必然。民歌的保護與傳承需緊密結合其所處的文化生態環境,因地制宜、順勢而行。
四、其他
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研究還涉及一些其他方面。如王靖茗的碩士論文《廣西壯族多聲部合唱作品的藝術特征及指揮技法探究》(2015)分析壯族多聲部民歌合唱的特點,以及研究改編的合唱作品的指揮技法。黨雨娜《多元視野下的女性音樂研究——以廣西平果嘹歌中的女性演唱為例》(2016)探究了女性在嘹歌演唱中的情形,認為在嘹歌演唱過程中男女具有平等的演唱地位。潘其旭、鄧如金、黃美玲《德保壯族“詩那·嘀抬樂”三聲部民歌自然天成——德保壯族山歌代表性傳承人黃美玲訪談錄》(2017)在傳統德保三聲部民歌瀕危的現狀下,潘其旭等研究員一起深入德保采訪當地的歌手所記錄的第一手珍貴的材料。黨宇娜《回到人聲的起點,人類學視域下的“歌者觀照”——以壯族民歌研究為個案》(2019)強調了關注歌者的重要性。從以上文章中可以看出多聲部民歌的研究可以為合唱指揮領域的發展注入活力。同時,學者們重視音樂事象主體——人,從人的行為和特性入手研究民歌。
五、總體特征及相關思考
(一)廣西本土研究者為主力軍。當下研究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學者以廣西本土學者為主。這是由于本土研究者作為一定程度的局內人,能更容易地融入當地生活,更長時間地觀察現象。然而,在研究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過程中,不僅需要深入研究廣西本土的民歌,同時也需要從研究廣度和深度上同時切入,以開闊的視野來擴大研究的范圍和內涵,因而呼吁廣西以外的研究者的涉足也是必不可少的。作為局外人的研究者能更容易打破環境所帶來的觀念束縛,與本土學者的思想碰撞出別樣的火花,為研究帶來不同的視角和理念。例如可以多進行跨地域的比較研究,發掘音樂特征的地域性異同;多進行跨學科的互聯研究,剖析音樂特征的本質內涵等。
(二)從個案研究窺探整體研究。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以樊祖蔭先生為代表的學者們深入中國各少數民族地區,在扎實的田野考察基礎上系統研究了中國多聲部民歌,歸納分析了中國民間音樂的多聲性思維,成果卓著,為后來的學者奠定了堅實的研究基礎。學者們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積極挖掘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并有了新的發現,記錄了當下的活態山歌,個案研究成果顯著。可以說,現今的研究成果由點及線、由線及面,既是對前輩研究成果的個案的更新與補充,同時也有助于中國多聲部民歌整體面貌的再現。
(三)注重研究成果的實踐價值。現今學者們除了對現象和事實予以描述和闡釋外,也更加強調其研究的實際運用。如學者們針對民歌當下的生存境遇提出參考性的改革措施,規劃民歌傳承教育在校園和社會中的實施方案,提出民歌傳播的可行性建議等,都證明了學者們期望將研究的理論成果運用于民歌傳承發展的實踐中。
結合筆者在研究壯族二聲部嘹啰山歌的過程中,發現藝人對嘹啰山歌充滿了熱情和執著,他們堅持著其音樂在單一的旋律模式中變幻無窮,講究唱詞的語言工整精妙,然則這些堅持卻讓大部分青年人望而卻步,所以現今嘹啰山歌的發展遇到了阻礙。但另一方面,國家政策和政府扶持又使得嘹啰山歌在復雜多樣的環境中存有一方凈土,藝人們精心呵護它的純粹和獨特,其已然成為南寧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
基于相關文獻的閱讀和實地考察,筆者認為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的起源和發展依靠著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民歌的精神內涵早已孕育在世世代代的族人心中,唱山歌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是在瞬息萬變的當代社會,民歌發展面臨危機和轉型,但熱愛歌唱的壯族人民總能在生活中以山歌為溝通交流、表情達意、顯露才華和展示魅力的媒介。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無疑通過山歌文化促進了自我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自豪感,但其外力的最終目的是使壯族人民心中“以歌為美”的精神存續下去,讓更多壯族青年體悟和理解其中的價值,讓族外人也能感受其中的魅力。廣西壯族多聲部民歌依然存有其“純粹”之處,這是壯族音樂文化的寶藏,亦是泱泱中華文明之果實。
注釋:
① 朱利安·H·斯圖爾特著,潘艷、陳洪波譯.文化生態學[J].南方文物,2007,(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