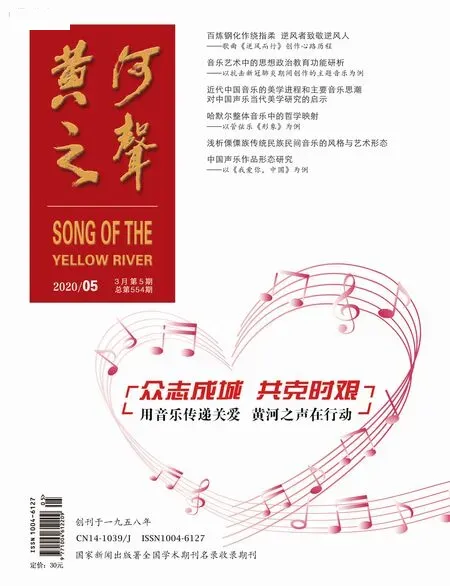沖破黑暗的號角,迎接黎明的曙光
——紀念人民音樂家張曙
◎ 紀愷 (黃山學院藝術學院)
他不是軍人,他卻是戰士。他不曾揮舞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建功立業。他卻用心頭的筆當作刀槍,直刺敵人的心臟,垂名史冊。他更不是將軍,指揮部眾,沖鋒陷陣,浴血疆場。他是一名歌者,用那震耳發聵的歌聲,解國人于倒懸,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用那慷慨激昂的旋律,號召人民團結起來,抵御外侮,以血肉之軀結起堅不可摧的鐵壁銅墻。
他就是我們敬愛的人民音樂家——張曙。
一、音樂創作歷程
張曙生于1908年9月18日(農歷8月23日),名五喜,字恩襲,號紹襲。安徽歙縣人。先后就讀于上海藝術大學和“國立音專”。是當時的進步文藝團體南國社和左翼劇聯的主要成員。“八·一三”淞滬會戰后去武漢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文化音樂組織工作,主要從事抗日救亡歌曲創作。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九·一八”事變后和聶耳等音樂家一起開展救亡歌詠運動,他是群眾歌詠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新音樂運動的奠基人之一。周恩來對張曙的評價極高:“張曙先生之可貴在于同聶耳同為中國文化戰線上的兩員猛將,他的救亡歌詠代表了大家發出了反抗的怒吼,代表了大眾發出了要求團結的呼聲,他為抗戰勝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的功績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1938年12月24日,人民音樂家張曙30歲的年輕生命厄止于日寇的飛機轟炸。這不能簡單的歸咎于避之不及或既定宿命,而是他早已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田漢在回憶張曙時說:“每遇警報,他很少躲防空洞,常常到山上或城墻上為與敵機戰斗的蘇聯志愿軍喝彩。”張曙鄙視敵人的大無畏英雄氣概赫然展現眼前。張曙夫人周畸女士在《血的回憶》中寫道:“每逢敵人無恥的瘋狂轟炸,他從沒有躲過,總是以泰然的態度回答我們,而且常常是執務不綴。他不愿因此而白費寶貴的時間。”可見,他是在敵人的炮火底下用生命寫歌。他是祖國的兒子,用生命回報了母親。他為音樂而生,把一切獻給了事業。他的音樂是震撼山岳的驚雷,是激勵斗志的詩篇,是刮骨療傷的猛藥,是蕩滌靈魂的華章。
張曙是音樂家,男中音歌唱家,二胡演奏家。更是最接地氣的音樂理論家。他說:“我們既然要通過音樂喚起大眾,組織群眾,那么我們必得先要懂得大眾的疾苦與希求。倘若你沒有懂得大眾的生活情緒,無論你的作曲技巧怎樣高,你一輩子也作不出大眾真正需要的音樂來;倘若你要憑理想去創造大眾的‘國難’音樂,至多也不過是你個人發發牢騷的東西罷了,與大眾是絲毫不發生關系的。所以我得要先從大眾去學習,然后才能去教育大眾。也只有從實踐地去參加大眾的一切運動,然后才能創造得出大眾真正需要的音樂來,也就才能創造得出大眾的‘國難’的音樂來。”這正契合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革命文藝理論指導思想。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踐行者,是新音樂發展方向的引領人。他的夫人對此深有感觸:“張曙同志有些作品是深受群眾喜愛的。他的這些作品之所以有強勁的生命力,就在于他能比較深刻地表現各個歷史階段中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思想感情上是與人民息息相通的。例如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天災加人禍,弄得民不聊生,他的《救災歌》《筑堤歌》就生動地反映了勞動人民反抗階級壓迫和戰勝自然災害的斗爭。當國家遭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他又做出像《洪波曲》《壯丁上前線》《日落西山》《大丈夫當兵去》等歌曲,描繪全民抗戰的精神面貌和生動情景,鼓舞著千百萬人民抗擊侵略者的斗爭意志。張曙同志就是這樣運用音樂藝術作為武器向敵人戰斗的。”
張曙畢生致力于新音樂運動,在外敵當前,國土淪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發出怒吼,以喚醒沉睡著的整個民族的靈魂。”他敏銳的意識到:“大多數人是一片散沙,需要你去組織他。大多數人是知識盲,需要你去教育他。大多數人是睡獅般的昏睡著,需要你去振發他,讓他自己從地獄里掙扎出來。”(張曙《談作曲》)他要用音樂去喚醒民眾,拯救靈魂。歌曲《生活教育歌》《抗戰進行曲》《還我山河》音調深沉但感情激越,節奏明快且鏗鏘有力,代表著時代精神和人民大眾的呼聲。
二、音樂風格特點
張曙的音樂創作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時代氣息。張曙出生在安徽歙縣的一個小山村,在幼年時就表現出了很高的音樂天賦,他音樂的啟蒙受益于母親。知書達理,善良賢惠的母親在常給幼年的張曙講述優美的民間傳說和古代英雄故事的同時,還教會了他吟唱很多民間流傳的歌謠和動聽的山歌小調。在他幼小的心靈深深的烙下了民族英雄的氣節,引導了他對民族音樂的興趣和愛好。張曙五歲就被家鄉當地的群眾業余組織的徽戲班子吸收為小學員,開始跟隨當地民間藝人學習,八歲時吹、拉、彈、唱樣樣皆能,并且開始接觸徽劇、京劇、昆曲等戲曲藝術,之后又就讀于上海藝術大學和“國立音專”,這些經歷都為張曙日后的創作和在音樂方面的造詣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音樂作品都植根于民族音樂的沃土,相當多的接受了中國民歌的遺產,并發揚光大,弘揚拓展。例如《日落西山》的音調、節奏、結構和表現手法,都是民歌體的。《干!干!干!》《農夫苦》《朝會歌》均是用民眾的語言和民族的詞匯直接反映群眾斗爭生活的。他所創作的歌曲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鮮明的個性特征。讓我們古老的民族音樂煥發出生機,使人民群眾民族民主精神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是歷史的記錄,時代的強音。
在張曙的創作過程中,也大量借鑒其他同時代作曲家的優秀成果以及創作特征,也發表了一些關于音樂創作風格的文章。在《聶耳作品的歷史性》(選自南京《新民報》1935年12月16日)中,他提及要對歷史有一種態度,并需要有一定繼承性。在遙望歷史的同時,還要彰顯現今時代的屬性(當時的音樂作品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與戰斗性)。另外,張曙還寫作一些關于音樂作品的“讀”后感。在《看〈回春之曲〉后》(選自南京《新民報》1935年12月8日)中,他不斷在呼吁民族的靈魂需要重新覺醒,必須武器,去戰斗、去抗爭。還認可一種方式,這些作品不僅僅是單純藝術的獻禮,而是民族靈魂醒悟的曙鐘,是民族生存斗爭開始的呼號。
總體而言,張曙的音樂風格在原有時代風格的基礎上,還具有一定前瞻性與創新性。前瞻性表現在準確把握到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同時也不忽視音樂藝術的真實價值,既有對歷史作品的一種回顧和守望,也有一種未來音樂作品發展的期許與希望。在創新的概念中,張曙對音樂藝術有一種始終追求本真的態度,不是一種華而不實的喧鬧,而是一種現實的抗爭,或者是一種生活的體味,更是一種時代的見證。
三、精神及思想評價
他是新音樂運動的參加者和推動者,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黃色歌曲彌漫靡靡之音盛行,少有代表人民思想和意志的歌曲。他和田漢、聶耳、冼星海、呂驥等進步的音樂詞曲作家一起,從事革命歌曲創作并開展群眾歌詠活動,使革命歌曲深入到基層的人民大眾之中。之所以張曙創作的革命歌曲能得到廣泛傳唱,是因為他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如《救災歌》《筑堤歌》《車夫曲》等就生動的反映了勞動人民反抗階級壓迫和希望戰勝自然災害的狀況。時至今日哼唱他的曲子,都能再現當時情景。這與他能深入群眾,了解民情,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是分不開的。張曙在思想感情上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并把這種思想感情運用到音樂創作中。這正是他創作的歌曲能夠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得以廣泛傳播具有強大號召力和強勁生命力的根源之所在。
張曙的精神是充滿著愛國主義情懷的民族精神,他短暫的一生是如歌的歲月。在那“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遷”風雨如磐的年代,他兩次入獄,大義凜然,不屈不撓。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求榮,民族存亡,何去何從。他不作“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屈原語)的低吟淺唱,而是高舉文藝革命的大旗,高歌“我們是民族的戰士,中國的呼聲,我們的歌是槍殺敵人的白刃,整千整萬的踏著血跡前進”(《抗戰進行曲》)。他的憂國憂民不是“載不動過許多愁”“怎一個愁字了得”(李清照詞),也不是“少年不識愁滋味”而后的“更上層樓,……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辛棄疾詞)的悲鳴哀嘆。亦非“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懷激烈”(岳飛詞)。而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具有的崇高志向:“干!干!干!鏟除世界的不平,填滿人間的缺陷”(《干!干!干!》)。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粉身碎骨全不怕”(于謙語),“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語)。
結 語
2018年是張曙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浩歌縈耳,英容在目,撫今追昔,浮想聯翩。筆者在2018年9月來到了張曙故居,走訪了張曙的后代,當翻閱著張曙作品集,看到張曙給父親的親筆家書,當與張曙的后代談起張曙,并跟隨他們一起演唱起張曙所作音樂作品來紀念和追憶張曙之時,大家都激動不已,深深的被張曙一生的音樂創作所震撼和感動,雖然一生短暫,但是他的音樂才能都服務于時代,都融入了中國人民雄壯的抗日交響當中。在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今天,珍饗革命前輩留給我們的精神食糧,重溫老一輩音樂家用生命和鮮血譜寫的革命樂章,感慨萬千,力量倍增。張曙先生挖掘出民族音樂的精髓,升華為萬古流芳的革命歷史歌曲,對時代的貢獻不可磨滅,對后世的影響更為巨大。如果說流行音樂能夠算得上是百花齊放花圃中的一支奇葩,那么獨具民族特色的革命歷史歌曲更應是百花院里的啼血的杜鵑,艷麗的牡丹,傲然的秋菊,斗雪的寒梅。
紀念是為了傳承,紀念是為了弘揚,紀念是為了學習,紀念是為了創新。我們要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繼承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向老一輩音樂家學習,多創作適應新時代的歌曲,在奔小康的康莊大道上,為早日實現中國夢高唱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