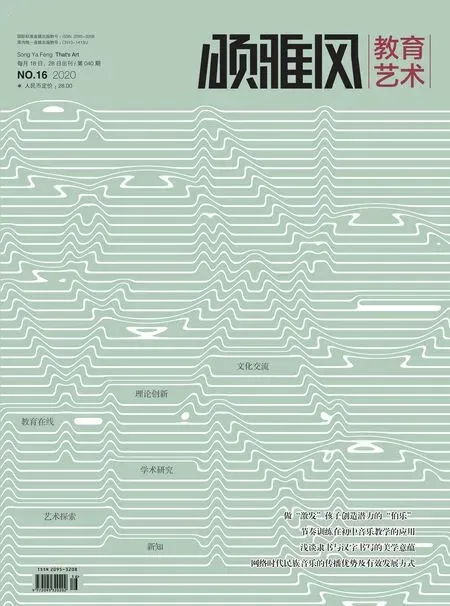所有的路都不白走
——讀《狂人日記》有感
◎宋長華
魯迅出生于紹興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是進士,做過知縣,后又捐了個從七品的內閣中書,也算是個京官。當時,魯迅家中有水田四五十畝,其父是個秀才,家境殷實。但在魯迅13歲那年,祖父因“科舉舞弊案”入獄,父親因此而生病,兩年后病逝,從此魯迅家道中落,便也放棄了私塾來到了費用低的新學堂——江南水師學堂和礦路學堂,魯迅因為學習優秀而獲得了清政府公派留學的機會。先是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兩年后獲得“日本語及普通速成科”文憑,按清政府給予的官費資格,他應該升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的采礦冶金科學習,但魯迅決意學醫,以便回國后能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中醫耽誤的國民,促進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戰爭年代還可以當軍醫。他來到了仙臺學醫,由于“紀錄片事件”,魯迅第二年便棄醫從文,走上了一條推廣文藝來救治國民的路,后來回到國內,他的創作也就一發不可收。
在我看來,魯迅的作品中批判舊制度最為激烈的首推他的《狂人日記》。從一個“狂人”的角度揭露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歷史,說他是最清醒的革命戰士,能見人所未見,想人所未想。我讀的遍數多了,越讀越想笑。笑“狂人”的癥狀,笑魯迅文字和思想嫁接的巧妙。魯迅不愧學過醫,“狂人”的種種癥狀表明,他是個標準的偏執型精神分裂癥患者。這種病人會出現幻聽、幻覺,而妄想是最常見、最重要的思維障礙。最常出現的妄想有被害妄想、關系妄想、影響妄想、嫉妒妄想、夸大妄想、非血統妄想等。
小說中“狂人”時常出現的就是被害妄想,他疑心所有的人都要害他,都是不正常的。動物是不正常的,“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鄰居們也不正常,“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他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來家的佃戶不正常,最親近的大哥不正常,“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看我幾眼,今天才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樣。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大哥找來給自己看病的大夫不正常,“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著地, 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夫說的話不正常,“不要亂想,靜靜地養幾天,就好了。——養肥了,他們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處?”在“狂人”的眼中,“大家聯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
所有的人都想害自己,都想“吃”我。這種被害的妄想讓“狂人”睡不著覺,“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于是他總是研究。研究別人,研究生活,研究歷史,“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一個人越是睡不著,就越愛胡思亂想,連續幾天不睡可能就出現幻聽、幻覺,這一切都符合精神分裂癥的特點。
精神分裂癥的另一個特點是關系妄想,就是什么事情都能和自己聯系上,都和自己有著密切的聯系。趙家的狗,街上人的聊天,女人打孩子說的話,佃戶和大哥的聊天,書上的“海乙那”,李時珍《本草綱目》上的記錄,自己踹了陳年古久先生的流水簿子與所有事情的關系。我們生活在世間,是與外界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是過于偏執的話,就是一種病態了。換位思考一下,這種病人的世界多么可怕,他每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讓人同情。
如果沒有學過醫學,或者沒有接觸過精神病患者,不可能寫得如此細膩逼真。不知道魯迅在仙臺學的是什么專業,但藤野先生是他的解剖學老師,那么魯迅學的應該是外科。當時的魯迅很勤奮,他應該也了解心理精神科的知識,所以把自己的醫學知識用到了創作上來,用一個在別人看來病態的表現,告訴大家了一個常人看不太透徹,也不太敢說的道理,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質,巧妙之極。如果沒有那段學醫經歷,會不會有《狂人日記》的誕生呢?
推而廣之,如果魯迅一直是小康之家,沒有嘗盡世態炎涼,沒有四處求學,會不會有揭露舊制度和國民劣根性的《吶喊》呢?如果國家和平安定,自己沒有反動文人們的冷箭暗槍和北洋軍閥的追查通緝,會有充滿溫暖與理性批判的回憶性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嗎?如果沒有舊中國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能有他像匕首和投槍的雜文嗎?林語堂說過,魯迅與其說是個文人,不如說是一個持矛把盾的戰士。
文學家憤而著書,創作一旦發生,憤不會煙消云散,而是蘊含在作家走過的路和審美內涵里。曹雪芹先生如果沒有經過兩次抄家而家道中落,以至于“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程度,能有古代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高峰《紅樓夢》嗎?吳敬梓先生如果科舉順利,官場得意,能有寫出抨擊封建科舉制和揭露封建士人丑態的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嗎?在北京的人總提北京的情形;從事革命的人,講話總帶著革命的氣概;書香門里走出來的人會帶著書卷氣。所有走過的路,都會以不同的方式改變著我們的模樣。魯迅是,我們也是,所有的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