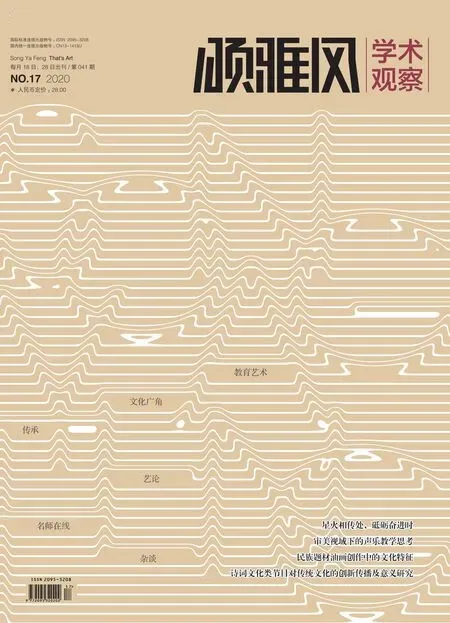“情”的探索:從湯顯祖到白先勇
◎李爾雅
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詞》中特地提出一個“情”字,它的表層意思是男女的自由愛情,但它的內涵卻決非僅限于此。從杜麗娘的出場到讀《詩經》,到游園驚夢,再到尋夢,這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過程,說明了所謂的“情”原來是一種自然人性(即“人欲”),它不受制于外在社會和道德理性,而是主體內部的獨立存在。
《牡丹亭》中的夢境和非現實世界決不只是一種戲劇手段,它和非現實世界具有鮮明的虛幻性特征。虛幻性在《牡丹亭》中的突出顯現,意味著“情”缺乏對現實生活的認同感。它是一種自覺的避讓,自覺地保持著一段距離,而這一種境界不屬于清醒的理性思維,事實上它是屬于審美活動的,它使得戲劇內容,也就是“情”逃避了普遍實用的價值判斷,而作為一種強烈的感性體驗得以保存。
同時,夢境和非現實世界的出現,是“情”和“理”嚴峻沖突的必然產物。與“理”相比,“情”顯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擊。但“情”一旦覺醒,就不會輕易退去,它對已經覺醒了的生命負有責任,它在社會上無立足之地,卻對個體生命極端重要。于是,“情”只能潛入夢中,潛入陰間,在這些世俗倫理鞭長莫及的地方,頑強而又充沛地表現自己。
自2005年起,“青春版”《牡丹亭》開始在京滬杭、香港、臺北、廣州等高校及國外演出,掀起了“白旋風”“牡丹熱”。
白先勇在接受訪談中認為“昆曲是一個切入點。整個中國文化的斷層如何彌補起來,如何讓中國人產生文化認同,我認為一定要先有一個實際的、看得見的表演藝術來感動人心。”“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卻破碎了……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在19世紀時幾乎整個被斬斷了”正是這些想法,加固了他對于將《牡丹亭》“青春化”的信念。
相較于大眾意義上的“改編”,“青春版”《牡丹亭》其實是將力氣更多地用到了戲劇的服裝、音響、燈光、舞臺背景上,對于原著的改動,白先勇主要對其采用了刪改、簡化,使劇本更加貼合現代年輕人的審美需求:從整個劇本來看,新版本將游離于中心之外的出目刪掉,由原來的五十五出刪并為二十七出;其次,從具體的曲子來看,把原來的大片的唱詞刪減為幾個簡單的唱句;再次,青春版劇本賓白通俗,優化敘述,并在必要情節增加相應描述,這樣賓白的充實使全劇的情節貫串更加流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為實際演出服務。
“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古今相同。現代社會,人們對于愛情的追求依然如此,現代青年對待愛情卻有種迷亂求真的自覺性追求、覺悟性追求,這一點可以在《牡丹亭》中仍然找得到共鳴。
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圍繞杜、柳情展開,共分“三情”:啟蒙于 “夢中情”,轉折為“人鬼情”,歸于“人間情”。雖然呈現了原著“情至”精神,但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以更單線條的“情”串聯起來的整部戲劇,不自覺地弱化了戲劇中以封建禮教為代表的障礙因素,讓“情”自然而然地成為男女主人公性格變化與成長的出發點、轉折點、結點。
黑格爾說:“歷史的東西雖然存在,卻是在過去存在的,如果它們和現代生活已經沒有什么關聯,它們就不是屬于我們的,盡管我們對它們很熟悉;我們對于過去事物之所以發生興趣,并不只是因為它們一度存在過”。白先勇對《牡丹亭》的解讀、重構與湯顯祖當初的建構,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點,體現了歷史與現實的關聯。
兩種對于“情”字的不同展現,意外地在不同的年代收獲了同樣的關注。湯顯祖以“至情”反理學、解放人性的理想,是通過他“意趣神色”的編劇理念來執行的;白先勇為了“復興傳統,文化創新”的理想,是通過展示“青春”“美”的理念和現代文化包裝與傳播手段來實現。因而在戲劇盛行的元明之際,《牡丹亭》卻能讓少女讀其劇作后深為感動,以至于“忿惋而死”,甚至有女伶演到“尋夢”一出戲時感情激動,卒于臺上;亦或是娛樂文化大爆發的21世紀,“青春版”《牡丹亭》在各大高校巡演,卻能讓從未看過傳統戲劇的大學生連看三場,流連輾轉。
從湯顯祖到白先勇,這絕不僅僅是兩個相隔千百年的文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簡單追尋。湯顯祖化昆曲為利器,直捅向封建社會窒息壓抑的兩性婚姻觀念;白先勇轉利器為溫情,用最純真的傳統情緒去渲染、擴大當代人對于愛情最質樸的向往。只有當我們拋棄時空建立的壁壘,才能夠頓悟:湯顯祖那含蓄婉轉的表達之下,從不缺乏最狂熱的對愛的忠誠,白先勇看似顛覆性的舞美設計背后,卻依然是對舊時人、舊時情愫的致敬與追憶。
苦海愛恨翻沉,情字始終如一。白云蒼狗,時空變遷,唯有傳統文化留下的永恒主題,能不斷地掀起世人心靈的觸動。曲高未和寡,源遠一直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