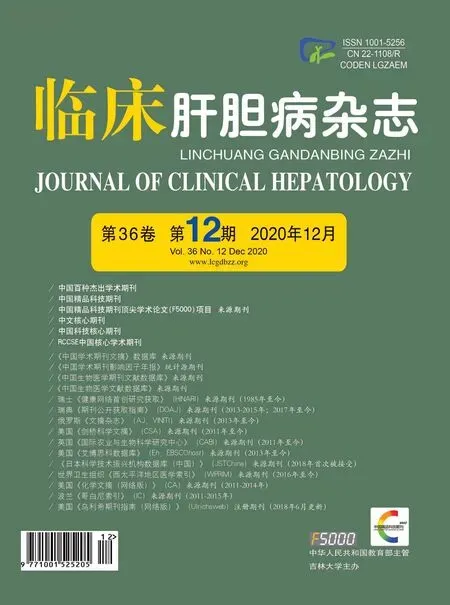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在肝膽胰外科手術(shù)中的應(yīng)用與前景
趙之明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yī)院 肝膽胰外科醫(yī)學(xué)部, 北京 100853
微創(chuàng)外科技術(shù)是繼器官移植技術(shù)后外科領(lǐng)域最大的發(fā)展,特別是進(jìn)入21世紀(jì)后,微創(chuàng)外科技術(shù)已成為當(dāng)代外科的主旋律。在胃腸外科、泌尿外科、婦科等學(xué)科中,微創(chuàng)技術(shù)的發(fā)展已經(jīng)非常成熟,且得到很好的技術(shù)推廣,基本普及至各級醫(yī)院。在肝膽胰外科中,微創(chuàng)技術(shù)雖然已經(jīng)得到長足的發(fā)展,特別是近10年中,腹腔鏡胰十二指腸切除等復(fù)雜的外科手術(shù)的開展已經(jīng)取得較好的進(jìn)展[1],國內(nèi)很多大型中心已經(jīng)累計(jì)超過500余例的臨床經(jīng)驗(yàn),但技術(shù)的推廣仍相對困難,這與腹腔鏡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shù)涉及到復(fù)雜的解剖分離以及消化道重建,特別是胰腸吻合、膽腸吻合的復(fù)雜性有一定的關(guān)系[2-3]。在肝臟領(lǐng)域中,國內(nèi)腹腔鏡肝切除技術(shù)開始于1994年,距今已經(jīng)20余年,腹腔鏡肝切除技術(shù)已經(jīng)較為成熟,且對于肝臟Ⅶ、Ⅷ切除腫瘤的切除手術(shù),雖然因其顯露困難,腹腔鏡下開展難度較大,但已有較多中心報(bào)道,且?guī)缀踉诟骨荤R下實(shí)現(xiàn)了所有肝段的切除手術(shù)[4-5]。相比于肝切除手術(shù),腹腔鏡技術(shù)在膽道外科手術(shù)中的應(yīng)用更具復(fù)雜性和挑戰(zhàn)性。腹腔鏡中2D的手術(shù)視野,缺少三維視野效果,雖然當(dāng)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3D腹腔鏡設(shè)備,但在手術(shù)中,術(shù)野的景深仍存在一定的變異性;腹腔鏡下的手術(shù)器械多為單一關(guān)節(jié)的活動,直桿效應(yīng),導(dǎo)致在進(jìn)行復(fù)雜的鏡下精細(xì)縫合時操作困難;另一方面,肝膽胰外科腹腔鏡手術(shù)多數(shù)耗時較長,術(shù)者長時間站立帶來的疲憊以及術(shù)者手臂的震顫等,同樣限制了腹腔鏡技術(shù)下精細(xì)的手術(shù)操作。
達(dá)芬奇機(jī)器人技術(shù)作為當(dāng)前外科領(lǐng)域的一個新星,其擁有3D的手術(shù)視野、7個自由度的器械活動以及術(shù)者可以保持一個自然體位,減少手術(shù)長時間操作帶來的疲憊等優(yōu)勢,使得其更加適合在狹小空間的手術(shù)操作以及進(jìn)行精細(xì)的分離與縫合。與開腹、腹腔鏡手術(shù)相比,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能夠獲得同樣的臨床療效和病理結(jié)果。同時,有報(bào)道[6]達(dá)芬奇機(jī)器人手術(shù)的學(xué)習(xí)曲線短于腹腔鏡技術(shù),且進(jìn)行操作訓(xùn)練時,術(shù)者不需要有一定的腹腔鏡經(jīng)驗(yàn),仍能快速掌握該項(xiàng)技術(shù)。因此,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外科技術(shù)逐漸得到關(guān)注。近2年,我國地市級醫(yī)院引入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設(shè)備呈快速上升趨勢,且應(yīng)用范圍不僅限于胃腸外科、泌尿外科、婦科等腹腔鏡開展良好的傳統(tǒng)學(xué)科,也在諸如心胸外科、口腔外科中顯示出巨大的潛在優(yōu)勢。達(dá)芬奇機(jī)器人技術(shù)在肝膽胰外科中的應(yīng)用已有較多中心報(bào)道,但較鮮有大規(guī)模樣本病例報(bào)道。本中心在劉榮教授帶領(lǐng)下,自2011年開展達(dá)芬奇機(jī)器人技術(shù)以來,已經(jīng)完成各類機(jī)器人肝膽胰手術(shù)近5000例,積累了一定的臨床經(jīng)驗(yàn),也引領(lǐng)了該領(lǐng)域中的一些技術(shù)性創(chuàng)新。
1 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在肝臟外科中的應(yīng)用與創(chuàng)新
自2002年以來,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在肝切除手術(shù)中被逐漸應(yīng)用,目前腹腔鏡肝切除技術(shù)已經(jīng)發(fā)展相對成熟,特別是對于肝邊緣性腫瘤的切除,多數(shù)中心已經(jīng)能夠成功開展。劉榮等提出的“模式化腹腔鏡肝左外葉切除”已成為肝左外葉良惡性腫瘤治療的一個金標(biāo)準(zhǔn),體現(xiàn)了腹腔鏡技術(shù)的巨大優(yōu)勢。但對于特殊部位或復(fù)雜肝葉切除,腹腔鏡下開展仍相對復(fù)雜與困難,限制了腹腔鏡肝切除手術(shù)的適應(yīng)證進(jìn)一步擴(kuò)大。
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在肝切除手術(shù)中體現(xiàn)了其特有的優(yōu)勢:(1)術(shù)野的顯露。在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肝切除手術(shù)中,術(shù)者可以操控3個機(jī)械臂和1個鏡頭臂,其中2個機(jī)械臂主要用于手術(shù)中肝周游離、肝門解剖以及肝實(shí)質(zhì)離斷等操作,第3個機(jī)械臂主要用于術(shù)野的顯露。在進(jìn)行右側(cè)肝葉游離時,特別是對于肝腎韌帶游離、腔靜脈韌帶游離,第3個機(jī)械臂能夠很好地抬高右側(cè)肝葉,并保證持續(xù)的穩(wěn)定性,從而充分顯露肝后空間,保證右側(cè)肝葉的游離。在進(jìn)行肝S7段及S8段的顯露時,第3個機(jī)械臂可以通過牽拉肝圓韌帶,將右側(cè)肝葉向左側(cè)腹腔牽拉,能夠有效保證肝S7段與S8段的顯露,從而便于術(shù)中的肝段切除。(2)機(jī)械臂的持續(xù)穩(wěn)定性和靈活性。在肝切除手術(shù)中,肝實(shí)質(zhì)離斷與出血的控制是兩大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在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肝切除中可以選擇的肝實(shí)質(zhì)離斷的器械有限,以超聲刀離斷為主。同時,采用雙極電凝進(jìn)行止血與超聲刀肝實(shí)質(zhì)離斷相配合,可以實(shí)現(xiàn)止血與切割的完美結(jié)合。對于明顯的肝斷面出血,在雙極電凝止血無效的情況下,也可以借助機(jī)器人下縫合的靈活性進(jìn)行縫扎止血。
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肝切除手術(shù)的適應(yīng)證在腹腔鏡手術(shù)適應(yīng)證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擴(kuò)展。目前已有腹腔鏡下肝S1~S8段切除的報(bào)道[7-10],但在S1、S7、S8段肝切除以及肝中葉切除、ALPPS(聯(lián)合肝臟分隔和門靜脈結(jié)扎的二步肝切除)中應(yīng)用微創(chuàng)技術(shù)仍富有挑戰(zhàn)性。隨著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肝切除手術(shù)適應(yīng)證不斷擴(kuò)大,已有較多文獻(xiàn)[9,11]報(bào)道亞肝段、肝段以及聯(lián)合肝葉的切除術(shù),且取得與開腹手術(shù)同等的臨床及病理療效。
2 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在胰腺外科中的應(yīng)用與創(chuàng)新
胰腺微創(chuàng)外科相比于肝臟外科整體發(fā)展滯后,但腹腔鏡胰腺體尾部切除手術(shù)目前已經(jīng)非常成熟。腹腔鏡胰十二指腸切除因其解剖的復(fù)雜性以及涉及消化道重建技術(shù),被認(rèn)為是腹部外科手術(shù)中難度最高的手術(shù)方式[12-14]。其他如胰腺中段切除、保留十二指腸的胰頭切除和胰腺腫瘤腕除術(shù)等,均由于胰腺解剖特點(diǎn)以及術(shù)后較高的并發(fā)癥風(fēng)險(xiǎn),限制了微創(chuàng)治療的開展[15]。對于Appleby(胰體尾癌根治術(shù)聯(lián)合腹腔干切除術(shù))、RAMPS(根治性順行模塊化胰脾切除術(shù))等,不但涉及胰腺的解剖,同時涉及血管的切除或裸化,要求腹腔鏡下操作更加精細(xì)、穩(wěn)定。
腹腔鏡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shù)經(jīng)過十余年的發(fā)展,已有大宗病例報(bào)道,且取得了與開腹同等的臨床療效。但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胰十二指腸切除仍少有文獻(xiàn)報(bào)道,已報(bào)道的病例數(shù)較少。本中心劉榮教授團(tuán)隊(duì)目前已完成一千余例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胰十二指腸切除術(shù),是國內(nèi)外最多的病例數(shù),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手術(shù)路徑[16],即經(jīng)足側(cè)向頭側(cè)、經(jīng)右側(cè)向左側(cè),經(jīng)后方向前方游離的順序進(jìn)行組織的游離與標(biāo)本的切除。切除標(biāo)本的游離主要采用機(jī)器人1號機(jī)械臂(達(dá)芬奇機(jī)器人Si系統(tǒng))的超聲刀。游離十二指腸及胰腺鉤突時,由于超聲刀無法調(diào)節(jié)方向,部分情況下顯露不足,可能對手術(shù)造成困難。胰腺鉤突顯露最大的障礙,來自于橫結(jié)腸的干擾。對此,多數(shù)情況下可以通過降低右半結(jié)腸肝區(qū),降低橫結(jié)腸張力,從而易于顯露胰腺鉤突部;部分肥胖患者仍顯露困難時,可以借助劉榮教授提出的“R”孔進(jìn)行顯露及游離胰腺鉤突部,即采用鉤突優(yōu)先的方式,打開Kocker切口后,顯露腸系膜上動脈根部,根據(jù)腸系膜上動脈根部而顯露腸系膜上動脈的全程,以此為標(biāo)記,進(jìn)行鉤突的離斷。在進(jìn)行消化道重建時,劉榮教授提出“301”式胰腸吻合,進(jìn)行遠(yuǎn)端胰腺斷面的3針交錯式捆綁,增加斷面的張力,減少縫合中對胰腺組織的切拉損傷,同時增加了吻合的牢固性[17]。胰腸吻合采用單層的連續(xù)縫合方法,減少了胰腸吻合的手術(shù)時間。膽腸的單層提拉式吻合,更是簡單易行。對于胃腸吻合,劉榮教授提出了經(jīng)“L”孔的吻合方法,即經(jīng)腸系膜血管的左側(cè)打開橫結(jié)腸系膜,顯露空腸后上提,與胃后壁進(jìn)行吻合,減少了對結(jié)腸的翻動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機(jī)器人手臂活動范圍有限,不適合較大范圍內(nèi)的移動,通過“L”孔的胃腸吻合,降低了手術(shù)的難度[18-19]。
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在其他胰腺外科手術(shù)中的應(yīng)用也展現(xiàn)了其優(yōu)越性。RAMPS手術(shù)在胰腺癌根治性手術(shù)中能夠很好的提高腫瘤的R0切除率,改善患者長遠(yuǎn)預(yù)后[20],但因其手術(shù)需要過多的顯露腸系膜上動脈、肝動脈、腎動脈、腎靜脈等血管結(jié)構(gòu),對于解剖的穩(wěn)定性與準(zhǔn)確性提出了較高的要求[21],機(jī)器人下放大的手術(shù)視野及精細(xì)的手術(shù)操作,保證了該類復(fù)雜手術(shù)的開展。此外,機(jī)器人下行血管吻合技術(shù)相較于腹腔鏡也有了很大發(fā)展,使微創(chuàng)治療局部血管侵犯的胰腺腫瘤得以實(shí)現(xiàn)。Beane等[22]報(bào)道了50例機(jī)器人下胰十二指腸聯(lián)合血管切除重建患者,證實(shí)了機(jī)器人下進(jìn)行血管操作安全可行;研究還提出經(jīng)過35例的血管重建病例后,術(shù)者即可以度過學(xué)習(xí)曲線,這一點(diǎn)優(yōu)于腹腔鏡下血管重建技術(shù)。
3 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在膽道外科中的應(yīng)用與創(chuàng)新
雖然腹腔鏡膽囊切除開展最早,但膽道外科的微創(chuàng)化治療發(fā)展之路卻最為艱難。膽道外科手術(shù)中,惡性腫瘤主要為高位的肝門部膽管癌,且往往伴右肝門鄰近的血管侵犯。尤其是ⅢA型(Bismuth分型)肝門部膽管癌以及膽囊頸部癌伴肝總管侵犯時,往往伴右肝門血管的侵犯,從而增加了手術(shù)難度,這也是膽道外科微創(chuàng)化進(jìn)展緩慢的主要因素之一。肝門部膽管癌根治術(shù)多數(shù)情況下需要聯(lián)合肝葉切除,以及肝門部膽管成型后吻合[23-24]。在狹小空間進(jìn)行精細(xì)操作對于腹腔鏡技術(shù)有較大難度,但這恰恰是機(jī)器人技術(shù)的優(yōu)勢,其可以在狹小空間進(jìn)行精細(xì)而穩(wěn)定的縫合與打結(jié),克服了膽道外科中的手術(shù)難題,有利于膽道外科疾病的微創(chuàng)化治療。Li等[25]報(bào)道了單中心48例行機(jī)器人肝門部膽管癌根治性術(shù)患者,平均手術(shù)時間276 min,術(shù)中平均出血量150 ml,總并發(fā)癥發(fā)生率為58%,主要并發(fā)癥發(fā)生率為10.4%,無30 d內(nèi)臨床死亡病例,與開腹手術(shù)相比臨床療效相當(dāng),相關(guān)結(jié)論有待更大規(guī)模臨床研究進(jìn)一步探討。
4 達(dá)芬奇機(jī)器人在肝膽胰外科的發(fā)展前景
目前,達(dá)芬奇機(jī)器人技術(shù)在外科領(lǐng)域中的優(yōu)勢已經(jīng)顯現(xiàn),但因耗材昂貴,限制了其在國內(nèi)的推廣[26]。機(jī)器人在肝膽胰外科領(lǐng)域中的應(yīng)用拓寬了腹腔鏡技術(shù)的適應(yīng)證,在肝S7、S8段切除以及肝全尾葉切除中均有很好的表現(xiàn)。同時,機(jī)器人能夠很好地完成血管的切除重建,對于胰腺腫瘤及膽道腫瘤伴有血管侵犯能夠有效開展微創(chuàng)化治療。
機(jī)器人技術(shù)開展早期面臨的困難主要是由于術(shù)者對機(jī)器人設(shè)備不熟悉,未經(jīng)過良好的技術(shù)培訓(xùn),在操作中未能了解其不足,如達(dá)芬奇系統(tǒng)無力反饋的缺點(diǎn),在加持組織或牽拉中不能很好地識別組織的張力,導(dǎo)致不必要的組織損傷。因此,在早期開展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肝膽胰手術(shù)時,一方面要求配備一個配合默契的手術(shù)團(tuán)隊(duì),另一方面還要配備一個經(jīng)驗(yàn)豐富的專家進(jìn)行手術(shù)指導(dǎo),具備上述開展條件后,先行模仿大型中心現(xiàn)行模式開展機(jī)器人肝膽胰手術(shù),再積累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手術(shù)特點(diǎn)。
在未來發(fā)展中,隨著對達(dá)芬奇機(jī)器人設(shè)備不斷深入的認(rèn)識與學(xué)習(xí),肝膽胰外科微創(chuàng)化手術(shù)的適應(yīng)證將進(jìn)一步擴(kuò)展,達(dá)芬奇機(jī)器人的臨床應(yīng)用占比也將顯著提升,開腹或腹腔鏡手術(shù)將主要應(yīng)用于特別復(fù)雜手術(shù)或進(jìn)行腹腔探查、組織活檢或類似肝左外葉切除等簡單的手術(shù)操作中,多術(shù)式齊頭并進(jìn),各顯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