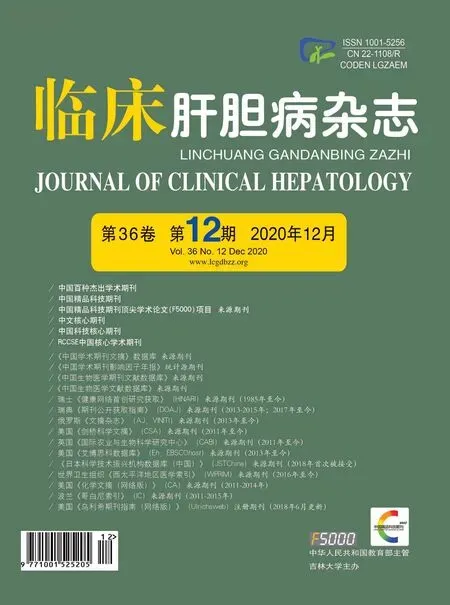肝硬化門靜脈血栓管理專家共識(shí)(2020年,上海)
門靜脈血栓(portal vein thrombosis,PVT)是指門靜脈主干和(或)門靜脈左、右分支發(fā)生血栓,伴或不伴腸系膜靜脈和脾靜脈血栓形成。急性PVT易導(dǎo)致腸系膜缺血,甚至腸壞死等嚴(yán)重不良結(jié)局;慢性PVT可導(dǎo)致門靜脈閉塞或門靜脈海綿樣變性,繼發(fā)門靜脈高壓。肝硬化患者PVT發(fā)病隱匿,常在體格檢查或篩查肝癌過程中偶然被發(fā)現(xiàn),需要與惡性腫瘤導(dǎo)致的癌栓鑒別。由于肝硬化本身存在凝血功能障礙和出血風(fēng)險(xiǎn)的矛盾,肝硬化PVT患者的抗凝治療難以實(shí)施。盡管越來(lái)越多的研究表明抗凝治療可促進(jìn)門靜脈再通,改善肝功能,但肝硬化PVT患者抗凝治療的最佳時(shí)機(jī)和藥物仍未確定。有些醫(yī)院已將經(jīng)頸靜脈肝內(nèi)門體分流術(shù)(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TIPS)用于肝硬化PVT的治療,但其具體適用人群有待商榷。迄今為止,國(guó)內(nèi)外尚無(wú)專門針對(duì)肝硬化PVT管理的指南或共識(shí)。因此,中華醫(yī)學(xué)會(huì)消化病學(xué)分會(huì)肝膽疾病學(xué)組牽頭,邀請(qǐng)國(guó)內(nèi)致力于該領(lǐng)域的相關(guān)專家共同參與討論和修改,歷時(shí)1年余,撰寫完成本專家共識(shí),以規(guī)范肝硬化PVT的臨床診治。本專家共識(shí)重點(diǎn)參考并分析樣本量大且有代表性的原創(chuàng)性研究和Meta分析結(jié)果。
1 肝硬化PVT的流行病學(xué)
共識(shí)意見1:PVT是肝硬化的常見并發(fā)癥之一。
肝硬化患者PVT患病率為5%~20%[1-2],年發(fā)病率為3%~17%[3-6]。由于不同研究納入肝硬化患者的性別、年齡、病因、臨床表現(xiàn)、肝功能嚴(yán)重程度和診斷方法各異,報(bào)道的患病率和發(fā)病率差異也較大。在2項(xiàng)以Child-Pugh A級(jí)患者為主的隊(duì)列研究中,PVT的1年、3年累積發(fā)病率分別為4.6%、8.2%及3.7%、7.6%[3-4]。在另外2項(xiàng)以Child-Pugh B或C級(jí)患者為主的隊(duì)列研究中,PVT的1年累積發(fā)病率分別為16.4%及17.9%[5-6]。國(guó)內(nèi)多中心、回顧性研究[7]表明,伴有急性失代償事件的肝硬化患者PVT患病率高于無(wú)急性失代償事件的肝硬化患者(9.36% vs 5.24%)。這些研究結(jié)果均表明PVT是肝硬化患者的常見并發(fā)癥,且與肝功能損害嚴(yán)重程度相關(guān)。
2 PVT對(duì)肝硬化預(yù)后的影響
共識(shí)意見2:PVT影響肝硬化患者預(yù)后。
PVT可能增加肝硬化患者遠(yuǎn)期死亡、出血、腹水、急性腎損傷及肝移植術(shù)后死亡的風(fēng)險(xiǎn)[8-9]。臨床醫(yī)師需結(jié)合PVT分期、嚴(yán)重程度及范圍評(píng)價(jià)其對(duì)肝硬化患者預(yù)后的影響。PVT和肝功能不全的嚴(yán)重程度是影響肝硬化患者預(yù)后的潛在因素。Senzolo等[10]發(fā)現(xiàn)抗凝治療后未再通的PVT僅增加了Child-Pugh B級(jí)與C級(jí)患者的病死率;而納入Child-Pugh A級(jí)與B級(jí)患者的研究[3]顯示,PVT并不會(huì)增加肝硬化失代償事件及死亡的風(fēng)險(xiǎn)。因此,PVT可能主要影響肝功能較差的肝硬化患者的預(yù)后。若PVT蔓延至腸系膜靜脈,將增加肝硬化患者肝移植的手術(shù)難度。
3 肝硬化PVT的危險(xiǎn)因素
菲爾紹(Virchow)靜脈血栓形成的三要素包括血流緩慢、局部血管損傷和血液高凝狀態(tài)[11],也適用于解釋肝硬化PVT的形成機(jī)制。
3.1 門靜脈血流速度降低
共識(shí)意見3:門靜脈血流速度降低與肝硬化PVT風(fēng)險(xiǎn)密切相關(guān)。
肝硬化患者肝內(nèi)纖維組織增生、肝竇破壞、血管扭曲閉塞,導(dǎo)致入肝的門靜脈血流速度降低。多項(xiàng)研究通過多普勒超聲檢查門靜脈血流速度發(fā)現(xiàn),若門靜脈血流速度低于15 cm/s,肝硬化患者發(fā)生PVT的風(fēng)險(xiǎn)將增加10~20倍[5-6,12]。非選擇性β受體阻滯劑是肝硬化門靜脈高壓患者最常用的藥物之一,可以降低門靜脈血流速度,導(dǎo)致肝硬化PVT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增加4倍[13-14]。
3.2 局部血管損傷
共識(shí)意見4:脾切除術(shù)是我國(guó)肝硬化PVT最常見的局部血管損傷因素。
腹部手術(shù)是肝硬化PVT形成最主要的局部血管損傷因素。脾切除術(shù)是國(guó)內(nèi)最常用于治療肝硬化門靜脈高壓和脾功能亢進(jìn)的外科治療方式[15],開腹或腹腔鏡脾切除術(shù)后PVT發(fā)生率約為22%。脾切除術(shù)可導(dǎo)致PVT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增加10倍以上[16]。因此,對(duì)食管胃靜脈曲張(gastroesophageal varices,GEV)伴脾功能亢進(jìn)患者行脾切除術(shù)應(yīng)特別慎重,術(shù)后需預(yù)防PVT。
3.3 易栓癥
共識(shí)意見5:遺傳性易栓癥可能不是我國(guó)肝硬化PVT的主要危險(xiǎn)因素,獲得性易栓癥可能是部分肝硬化患者發(fā)生PVT的潛在危險(xiǎn)因素。對(duì)于脾大但血小板計(jì)數(shù)正常或升高的肝硬化患者,建議篩查骨髓增殖性腫瘤的可能。
易栓癥是繼發(fā)于止血缺陷的遺傳性或獲得性血液高凝狀態(tài)[17]。靜脈血栓栓塞相關(guān)的遺傳性易栓癥的主要危險(xiǎn)因素包括亞甲基四氫葉酸還原酶(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MTHFR)C677T基因突變、凝血因子V Leiden突變及凝血酶原G20210A突變、遺傳性抗凝蛋白(抗凝血酶、蛋白C及蛋白S)缺乏等[18-20]。相關(guān)Meta分析證實(shí),MTHFR C677T純合突變、凝血因子V Leiden突變及凝血酶原G20210A突變與肝硬化PVT有關(guān),而抗凝血酶、蛋白C及蛋白S缺乏與肝硬化PVT并無(wú)顯著相關(guān)性[21-23]。我國(guó)漢族人罕有凝血因子V Leiden突變及凝血酶原G20210A突變,其對(duì)我國(guó)肝硬化患者PVT的影響可能非常微弱[24]。獲得性因素包括骨髓增殖性腫瘤(真性紅細(xì)胞增多癥、原發(fā)性血小板增多癥、骨髓纖維化)、抗磷脂綜合征、妊娠、產(chǎn)后、口服避孕藥、陣發(fā)性睡眠性血紅蛋白尿癥、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等,也可能是肝硬化患者PVT的潛在危險(xiǎn)因素[25]。尤其是伴有脾大但血小板計(jì)數(shù)正常或升高的肝硬化PVT患者,應(yīng)特別注意骨髓增殖性腫瘤的可能[26]。
3.4 炎癥
共識(shí)意見6:門靜脈、腹腔和腸道炎癥可能是肝硬化PVT形成的重要危險(xiǎn)因素。
肝硬化患者常存在腸源性內(nèi)毒素水平增高,其與肝硬化患者門靜脈系統(tǒng)的凝血酶生成潛力增強(qiáng)有關(guān),可導(dǎo)致血液高凝狀態(tài)[27-28]。Huang等[29]發(fā)現(xiàn),肝硬化合并GEV的患者中,PVT組的IL-6及TNFα水平均顯著高于無(wú)PVT組。
4 肝硬化PVT的影像學(xué)檢查
共識(shí)意見7:多普勒超聲是診斷肝硬化PVT的初篩影像學(xué)檢查方法,增強(qiáng)CT和MRI掃描有助于明確診斷。
影像學(xué)檢查可診斷和評(píng)估PVT的分期、嚴(yán)重程度、海綿樣變性側(cè)支血管,這與肝硬化患者的預(yù)后和治療方法的選擇密切相關(guān)。主要的影像學(xué)檢查手段包括多普勒超聲、增強(qiáng)CT、MRI和血管造影。
多普勒超聲檢查簡(jiǎn)單、便捷,可作為肝硬化患者PVT臨床篩查及評(píng)估的首選方法。多普勒超聲診斷PVT的靈敏度為89%~93%,特異度為92%~99%[30]。PVT表現(xiàn)為管腔內(nèi)高回聲或等回聲填充物,急性期可表現(xiàn)為血管腔擴(kuò)張。多普勒超聲還可用于測(cè)定門靜脈血流速度;門靜脈海綿樣變性表現(xiàn)為門靜脈周圍多發(fā)小血管影。然而,多普勒超聲檢查結(jié)果常受到操作者診斷水平、腹水和氣體的影響。
CT和MRI檢查,尤其是門靜脈重建,可用于進(jìn)一步確診PVT,其對(duì)腸系膜靜脈血栓和脾靜脈血栓的診斷更具優(yōu)勢(shì)。PVT表現(xiàn)為門靜脈管腔內(nèi)充盈缺損;新發(fā)PVT在CT平掃和MRI掃描下可表現(xiàn)為門靜脈管腔內(nèi)高密度影;門靜脈海綿樣變性在CT增強(qiáng)和MRI掃描下表現(xiàn)為阻塞的門靜脈周圍有諸多細(xì)小、迂曲的側(cè)支血管。CT檢查還可評(píng)判腸缺血和腸壞死。門靜脈直接或間接血管造影檢查屬于有創(chuàng)操作,目前很少用于PVT的診斷,而主要用于血管介入治療前的評(píng)估;此外,血管造影對(duì)附壁或部分性PVT的診斷未必優(yōu)于增強(qiáng)CT檢查。
5 肝硬化PVT的診斷和病情評(píng)估
共識(shí)意見8:根據(jù)慢性肝病病史和典型的影像學(xué)表現(xiàn),可診斷肝硬化PVT。對(duì)于影像學(xué)檢查發(fā)現(xiàn)有PVT,但肝硬化診斷證據(jù)不足者,肝臟穿刺活檢是肝硬化最重要的診斷方法。需結(jié)合生物化學(xué)指標(biāo)、血清甲胎蛋白水平、影像學(xué)特征和病理結(jié)果等,注意與非肝硬化PVT和門靜脈癌栓進(jìn)行鑒別。
5.1 診斷與鑒別診斷 通常根據(jù)慢性肝病病史和典型的影像學(xué)表現(xiàn)診斷肝硬化PVT。首選影像學(xué)檢查方法為多普勒超聲,增強(qiáng)CT和MRI檢查也可確診肝硬化PVT,并確定血栓范圍。對(duì)于影像學(xué)檢查有PVT表現(xiàn),但肝硬化診斷證據(jù)不足者,肝靜脈壓力梯度測(cè)定和經(jīng)頸靜脈肝臟穿刺活檢等是重要的診斷方法。肝硬化PVT需要與非肝硬化PVT和門靜脈癌栓鑒別,常可通過臨床病史、影像學(xué)特征和血清甲胎蛋白水平進(jìn)行初步鑒別。門靜脈癌栓常表現(xiàn)為門靜脈擴(kuò)張、血栓強(qiáng)化、新生血管、臨近血栓的腫瘤形成或血清甲胎蛋白水平>1000 ng/dl;若滿足以上3個(gè)或3個(gè)以上表現(xiàn),則考慮為門靜脈癌栓,靈敏度為100%,特異度為94%,陽(yáng)性預(yù)測(cè)值為80%,陰性預(yù)測(cè)值為100%[25]。
5.2 病情評(píng)估
5.2.1 肝硬化PVT的分期
共識(shí)意見9:肝硬化PVT的分期主要包括急性癥狀性和非急性癥狀性。
共識(shí)意見10:肝硬化患者發(fā)生急性腹痛,無(wú)論有無(wú)發(fā)熱或腸梗阻,均應(yīng)考慮急性癥狀性PVT可能。
確定PVT分期對(duì)制定后續(xù)抗血栓治療策略至關(guān)重要。肝硬化PVT多是在常規(guī)影像學(xué)檢查評(píng)估肝硬化嚴(yán)重程度或監(jiān)測(cè)肝癌時(shí)偶然被發(fā)現(xiàn),故常難以界定血栓形成時(shí)間。本共識(shí)并不推薦根據(jù)發(fā)病時(shí)間將肝硬化PVT分為急性和慢性,而推薦根據(jù)是否存在PVT相關(guān)的臨床癥狀進(jìn)行分期。肝硬化患者若存在急性腹痛(發(fā)病初期,癥狀與體征不一致)、惡心、嘔吐等PVT相關(guān)癥狀,則定義為急性癥狀性PVT;若無(wú)相關(guān)癥狀,則定義為非急性癥狀性PVT。建議肝硬化患者發(fā)生腹痛的時(shí)間>24 h,無(wú)論有無(wú)發(fā)熱或腸梗阻,均應(yīng)考慮急性癥狀性PVT,均需進(jìn)行影像學(xué)檢查確診;當(dāng)伴有發(fā)熱、畏寒,無(wú)論有無(wú)腹腔感染,推薦進(jìn)行常規(guī)血液細(xì)菌培養(yǎng)。
5.2.2 肝硬化PVT的嚴(yán)重程度
共識(shí)意見11:肝硬化PVT的嚴(yán)重程度主要包括附壁、部分性、阻塞性和條索化。
Yerdel分級(jí)是當(dāng)前最常用的PVT分級(jí)系統(tǒng)[31],包括4個(gè)等級(jí):(1)血栓占據(jù)門靜脈管腔的50%以內(nèi),伴或不伴輕度腸系膜靜脈血栓;(2)血栓占據(jù)門靜脈管腔的50%以上或完全占據(jù)門靜脈管腔,伴或不伴輕度腸系膜靜脈血栓;(3)門靜脈和近端腸系膜靜脈完全血栓;(4)門靜脈、近段和遠(yuǎn)端腸系膜靜脈完全血栓。Yerdel分級(jí)主要用于肝移植術(shù)前評(píng)估手術(shù)成功率及術(shù)后并發(fā)癥風(fēng)險(xiǎn),對(duì)于抗血栓治療選擇的價(jià)值有待商榷。Baveno Ⅵ共識(shí)[32]提出了PVT評(píng)估系統(tǒng),但并非專注于評(píng)估肝硬化患者,而是將惡性腫瘤、非肝硬化、肝移植術(shù)后等諸多疾病狀態(tài)均考慮在內(nèi)。目前,國(guó)內(nèi)有學(xué)者將肝硬化PVT的嚴(yán)重程度分為附壁、部分性、阻塞性和條索化,這更加簡(jiǎn)易,貼近臨床實(shí)踐,且有助于治療選擇和預(yù)后評(píng)判。附壁PVT指血栓占據(jù)門靜脈管腔的50%以下;阻塞性PVT指血栓完全或接近完全占據(jù)門靜脈管腔[33];部分性PVT指血栓程度介于附壁和阻塞性之間;條索化PVT指血栓長(zhǎng)期阻塞門靜脈而發(fā)生機(jī)化,影像學(xué)檢查無(wú)法探明門靜脈管腔[34]。阻塞性和條索化PVT常伴有門靜脈海綿樣變性。
5.2.3 肝硬化PVT的轉(zhuǎn)歸
共識(shí)意見12:肝硬化PVT的轉(zhuǎn)歸評(píng)判主要包括新發(fā)、部分再通、完全再通、進(jìn)展、穩(wěn)定和復(fù)發(fā)。
臨床需動(dòng)態(tài)觀察肝硬化PVT的發(fā)生及發(fā)展,以便及時(shí)調(diào)整治療方案。規(guī)范肝硬化PVT轉(zhuǎn)歸的定義有助于未來(lái)研究觀察終點(diǎn)的標(biāo)準(zhǔn)化。根據(jù)肝硬化PVT發(fā)生及其程度的變化,轉(zhuǎn)歸評(píng)判的定義如下。新發(fā)指既往影像學(xué)檢查提示無(wú)血栓,本次首次診斷為血栓;部分再通指血栓嚴(yán)重程度較前降低至少1個(gè)等級(jí),但仍存在血栓;完全再通指原有血栓完全消失;進(jìn)展指血栓的嚴(yán)重程度較前加重至少1個(gè)等級(jí);穩(wěn)定指血栓的嚴(yán)重程度較前無(wú)明顯變化;復(fù)發(fā)指原有血栓完全消失后再次出現(xiàn)血栓。
6 肝硬化PVT的治療流程
共識(shí)意見13:對(duì)于肝硬化急性癥狀性PVT,一旦出現(xiàn)腸缺血或腸壞死表現(xiàn),應(yīng)及時(shí)聯(lián)系外科醫(yī)師商討手術(shù)的必要性。
共識(shí)意見14:對(duì)于肝硬化非急性癥狀性PVT,可根據(jù)PVT的嚴(yán)重程度、范圍和動(dòng)態(tài)演變,酌情考慮是否采取抗凝藥物治療。
肝硬化PVT是否需要治療、何時(shí)啟動(dòng)治療以及采用哪種治療方式,取決于PVT的分期、嚴(yán)重程度、范圍,臨床表現(xiàn),門靜脈高壓并發(fā)癥、出血風(fēng)險(xiǎn),以及隨訪期間血栓動(dòng)態(tài)變化結(jié)局等[35]。肝硬化PVT的初步治療流程(圖1)提示,急性癥狀性PVT應(yīng)盡早啟用抗凝藥物治療,以再通血管并預(yù)防血栓蔓延;急性癥狀性PVT抗凝治療無(wú)效且出現(xiàn)腸缺血、腸壞死表現(xiàn),應(yīng)積極請(qǐng)外科醫(yī)師會(huì)診,探討手術(sh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伴有GEV出血或高危GEV的肝硬化PVT患者應(yīng)在控制靜脈曲張后再酌情啟用抗凝藥物治療;經(jīng)內(nèi)鏡和藥物治療后GEV仍反復(fù)出血的肝硬化PVT患者應(yīng)積極考慮TIPS;PVT程度<50%且血栓尚未累及腸系膜靜脈的患者可隨訪觀察,其中一部分患者的血栓可能在隨訪期間減輕或消失而無(wú)需抗凝藥物治療,而另一部分患者的血栓發(fā)生進(jìn)展后可酌情啟用抗凝藥物治療;若血栓占據(jù)門靜脈管腔≥50%或伴腸系膜靜脈血栓,則需考慮啟用抗凝藥物治療。
7 肝硬化PVT的治療方法
肝硬化PVT的治療方法主要包括抗凝治療、溶栓治療及TIPS。一部分肝硬化PVT患者在未應(yīng)用任何抗血栓藥物或其他血管介入治療的情況下可自發(fā)再通,即肝硬化一過性PVT[25,36],但如何準(zhǔn)確預(yù)判此類患者尚不清楚,影像學(xué)檢查隨訪間隔和觀察時(shí)限也未明確。由于PVT再通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從診斷到啟動(dòng)治療的時(shí)間間隔,越早開始治療再通率越高[37-38],目前仍需更多研究明確肝硬化PVT啟動(dòng)治療的最佳時(shí)機(jī)。
7.1 抗凝治療
共識(shí)意見15:抗凝治療的主要適應(yīng)證為急性癥狀性PVT、等待肝移植、合并腸系膜靜脈血栓形成;伴有近期出血史、重度GEV、嚴(yán)重血小板減少癥的肝硬化PVT患者應(yīng)暫緩抗凝治療。
共識(shí)意見16:肝硬化PVT患者抗凝治療前,應(yīng)進(jìn)行內(nèi)鏡和血液學(xué)檢查,充分評(píng)估出血風(fēng)險(xiǎn)。
共識(shí)意見17:存在GEV高危出血風(fēng)險(xiǎn)的肝硬化PVT患者,在抗凝治療前,建議啟用非選擇性β受體阻滯劑和/或內(nèi)鏡下治療進(jìn)行GEV破裂出血的一級(jí)預(yù)防。
共識(shí)意見18:既往有GEV破裂出血的肝硬化PVT患者,在抗凝治療前,建議啟用非選擇性β受體阻滯劑和內(nèi)鏡下治療進(jìn)行GEV破裂出血的二級(jí)預(yù)防。
盡早抗凝可有效安全治療非腫瘤、非肝硬化急性PVT已達(dá)成共識(shí)[39-40]。肝硬化患者常存在GEV破裂出血和鼻出血等出血風(fēng)險(xiǎn),也常伴有PT、國(guó)際標(biāo)準(zhǔn)化比值(INR)明顯延長(zhǎng)和血小板計(jì)數(shù)減少等凝血異常表現(xiàn)。對(duì)于肝硬化PVT患者,是否需要抗凝治療、何時(shí)啟用抗凝治療及如何應(yīng)用抗凝藥物均需謹(jǐn)慎評(píng)估風(fēng)險(xiǎn)與獲益。有2項(xiàng)Meta分析研究提示,抗凝治療后肝硬化PVT的門靜脈再通率為66%~71%,門靜脈完全再通率為41.5%~53%,血栓進(jìn)展率為5.7%~9%[41-42],抗凝治療較無(wú)抗凝治療可顯著提高門靜脈再通率和完全再通率,降低PVT進(jìn)展率;抗凝治療和無(wú)抗凝治療組出血風(fēng)險(xiǎn)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隊(duì)列研究更提示,抗凝治療可延長(zhǎng)肝硬化PVT患者的生存時(shí)間,尤其是抗凝治療后達(dá)到門靜脈完全再通的患者[43-44]。然而,這些研究在選擇抗凝治療的患者時(shí)可能存在潛在的偏倚,比如非阻塞性PVT、凝血功能及血小板計(jì)數(shù)相對(duì)正常、既往未發(fā)生過出血、無(wú)或低風(fēng)險(xiǎn)GEV和肝功能更好的患者等。抗凝治療的風(fēng)險(xiǎn)主要來(lái)源于高危GEV和嚴(yán)重血小板減少癥。因此,抗凝治療需在預(yù)防上消化道出血措施實(shí)施后啟動(dòng)。啟用抗凝治療前,可用非選擇性β受體阻滯劑和/或內(nèi)鏡下治療預(yù)防GEV破裂出血。
7.1.1 抗凝藥物的適應(yīng)證與禁忌證 肝硬化PVT的抗凝治療應(yīng)個(gè)體化。主要適應(yīng)證包括急性癥狀性PVT、等待肝移植、合并腸系膜靜脈血栓的肝硬化。主要禁忌證包括近期出血史、嚴(yán)重的GEV、嚴(yán)重的血小板減少癥。然而,界定嚴(yán)重血小板減少癥的閾值仍存爭(zhēng)議;國(guó)外學(xué)者認(rèn)為血小板計(jì)數(shù)<50×109/L的肝硬化患者出血風(fēng)險(xiǎn)增高[17,32],但國(guó)內(nèi)有學(xué)者發(fā)現(xiàn)血小板計(jì)數(shù)<50×109/L的肝硬化患者采用抗凝治療并未增加出血風(fēng)險(xiǎn)。進(jìn)展期肝硬化患者,特別是Child-Pugh C級(jí)患者,需謹(jǐn)慎考慮抗凝治療[17]。
共識(shí)意見19:低分子肝素和直接口服抗凝藥物對(duì)代償期肝硬化伴PVT患者相對(duì)安全、有效。直接口服抗凝藥物對(duì)于Child-Pugh C級(jí)肝硬化患者的安全性和療效需進(jìn)一步評(píng)估。
7.1.2 抗凝藥物類型的選擇 抗凝藥物包括維生素K拮抗劑、肝素和新型直接口服抗凝藥物。維生素K拮抗劑主要是華法林。華法林劑量達(dá)標(biāo)常需密切監(jiān)測(cè)INR,傳統(tǒng)認(rèn)為將INR升高至正常參考值上限的2.0~3.0倍為達(dá)標(biāo)。終末期肝病患者未服用華法林時(shí)INR已較高,在肝硬化患者中如何準(zhǔn)確監(jiān)控華法林的使用尚不確定。INR會(huì)受食物、藥物等因素的干擾,這也給華法林的藥效評(píng)估帶來(lái)了困難。
肝素類藥物主要包括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和磺達(dá)肝癸鈉。普通肝素劑量達(dá)標(biāo)常需密切監(jiān)測(cè)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shí)間(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傳統(tǒng)認(rèn)為將APTT升至正常參考值上限的1.5~2.5倍為達(dá)標(biāo)。值得注意的是,普通肝素可引起血小板減少癥,常于應(yīng)用肝素5 d后出現(xiàn),建議在使用后第3至10天復(fù)查血小板計(jì)數(shù);低分子肝素發(fā)生肝素誘導(dǎo)血小板減少癥(heparin-induced thrombocytopenia, HIT)和出血風(fēng)險(xiǎn)低于普通肝素,常無(wú)需監(jiān)測(cè)血小板計(jì)數(shù),但腎功能不全者慎用。低分子肝素需要皮下注射,如果患者用藥依從性差,可采取低分子肝素-口服抗凝藥物序貫治療。一項(xiàng)隨機(jī)對(duì)照試驗(yàn)發(fā)現(xiàn),低分子肝素注射治療1個(gè)月后口服華法林5個(gè)月的抗凝治療方案對(duì)肝硬化PVT患者安全、有效[45]。亦有研究[46]報(bào)道,磺達(dá)肝癸鈉成功治療7例失代償期肝硬化合并PVT患者,未發(fā)生出血或HIT等藥物不良反應(yīng)。
新型直接口服抗凝藥物包括直接Ⅹa因子抑制劑(如利伐沙班、阿哌沙班)和直接Ⅱa因子抑制劑(如達(dá)比加群),此類抗凝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能優(yōu)于傳統(tǒng)抗凝藥物[47-48],輕、中度腎功能不全者可以正常使用直接Ⅹa因子抑制劑。肝臟血管病興趣組進(jìn)行的多中心調(diào)查[49]顯示,38例肝硬化PVT患者中,最常應(yīng)用的直接抗凝藥物是利伐沙班,其次是達(dá)比加群和阿哌沙班;選擇直接口服抗凝藥物的原因是無(wú)需監(jiān)測(cè)INR。一項(xiàng)來(lái)自埃及的隨機(jī)對(duì)照試驗(yàn)[50]比較了利伐沙班與華法林治療慢性丙型肝炎感染、因脾功能亢進(jìn)行脾切除或化膿性門靜脈炎后發(fā)生急性PVT、處于代償期患者的效果及安全性。利伐沙班組門靜脈完全再通率(85% vs 45%)及部分再通率(15% vs 0)均顯著高于華法林組,而利伐沙班組消化道出血發(fā)生率(0 vs 43.3%)及病死率(0 vs 36.4%)顯著低于華法林組,結(jié)果表明肝病患者PVT抗凝藥物應(yīng)首選利伐沙班,而非華法林。考慮到這項(xiàng)隨機(jī)對(duì)照試驗(yàn)患者選擇的局限性,其結(jié)論尚需更多高質(zhì)量研究證實(shí)。利伐沙班主要通過肝臟代謝,適用于Child-Pugh A級(jí)患者,慎用于Child-Pugh B或C級(jí)患者[54]。
7.1.3 抗凝藥物劑量的選擇 深靜脈血栓形成的診斷和治療指南[51]推薦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的劑量為100 U/kg,1次/12 h。對(duì)于肝硬化PVT患者而言,各項(xiàng)研究報(bào)道的抗凝藥物劑量包括那屈肝素5700 U/d[52]、那屈肝素85 U·kg-1·12 h-1[53]和依諾肝素鈉200 U·kg-1·d-1[54]。Cui等[55]比較了皮下注射2種不同劑量(1 mg/kg, 2次/d;1.5 mg/kg,1次/d)的依諾肝素鈉治療肝硬化PVT的療效及安全性。結(jié)果表明2種不同劑量組間門靜脈再通率和靜脈曲張出血率差異均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但1.5 mg·kg-1·d-1劑量組出血風(fēng)險(xiǎn)更高。與傳統(tǒng)抗凝藥物相比,利伐沙班為凝血因子Ⅹa抑制劑,使用時(shí)常可按固定劑量給藥,無(wú)需因食物、體質(zhì)量、輕度肝腎功能損害調(diào)整劑量。
共識(shí)意見20:對(duì)于腸系膜靜脈血栓形成或既往有腸缺血、腸壞死、等待肝移植、存在遺傳性血栓形成傾向的患者,可考慮長(zhǎng)期抗凝治療。
7.1.4 抗凝治療療程 Baveno Ⅵ共識(shí)及歐洲肝病學(xué)會(huì)臨床實(shí)踐指南推薦抗凝治療療程常為6個(gè)月以上;門靜脈完全再通后仍需繼續(xù)抗凝治療數(shù)月或直至肝移植手術(shù);對(duì)于腸系膜靜脈血栓或既往有腸缺血或腸壞死、等待肝移植、存在遺傳性血栓形成傾向的患者,可考慮長(zhǎng)期抗凝治療[32,56]。一部分肝硬化PVT患者經(jīng)6個(gè)月的抗凝治療后門靜脈未再通,但繼續(xù)抗凝治療至12個(gè)月可實(shí)現(xiàn)門靜脈再通[37]。因此,若條件允許,對(duì)于抗凝治療6個(gè)月后PVT無(wú)明顯改善的患者,可嘗試持續(xù)抗凝治療至12個(gè)月。
共識(shí)意見21:抗凝治療過程中發(fā)生出血事件,建議根據(jù)出血嚴(yán)重程度延緩使用或停用抗凝藥物;發(fā)生消化道出血時(shí)應(yīng)及早行內(nèi)鏡檢查和治療;發(fā)生致命性大出血時(shí),及時(shí)使用拮抗劑,并進(jìn)行紅細(xì)胞、新鮮冰凍血漿、血小板輸注等替代治療。
7.1.5 抗凝治療過程中的出血管理 首先明確抗凝藥物的類型、劑量以及末次使用時(shí)間,完善血常規(guī)、肝功能、腎功能、凝血常規(guī),有條件者評(píng)估血漿藥物濃度,同時(shí)評(píng)估出血嚴(yán)重程度。輕度出血應(yīng)延遲用藥或停藥,并進(jìn)行對(duì)癥治療,調(diào)整抗凝藥物的種類和劑量;發(fā)生非致命性大出血,應(yīng)停用抗凝藥物,并根據(jù)出血部位采用機(jī)械按壓、補(bǔ)液、輸注紅細(xì)胞、新鮮冰凍血漿和血小板替代等對(duì)癥治療,可考慮使用拮抗劑;發(fā)生消化道出血時(shí),盡早行內(nèi)鏡檢查,明確出血部位和原因,可按相應(yīng)指南進(jìn)行處置;發(fā)生致命性大出血時(shí),應(yīng)立即停藥,并采取生命支持措施,使用拮抗劑對(duì)癥處理[54]。
共識(shí)意見22:抗凝治療成功后定期監(jiān)測(cè)門靜脈通暢性,以評(píng)估血栓是否復(fù)發(fā)。
7.1.6 抗凝治療后的監(jiān)測(cè)與隨訪 抗凝治療達(dá)到門靜脈再通后,仍可再發(fā)血栓。有研究[37,54]報(bào)道,停用抗凝藥物后PVT的復(fù)發(fā)率分別為27%、38%,中位隨訪時(shí)間分別為1.3、4個(gè)月。抗凝治療后3個(gè)月內(nèi)仍需再次監(jiān)測(cè)門靜脈通暢性,以決定是否繼續(xù)應(yīng)用抗凝藥物。
7.2 溶栓治療
共識(shí)意見23:溶栓治療肝硬化PVT的療效和安全性需要更多高質(zhì)量研究證實(shí)。
溶栓治療肝硬化PVT的相關(guān)證據(jù)匱乏,故可參考深靜脈血栓的治療經(jīng)驗(yàn),并結(jié)合肝硬化PVT自身特點(diǎn)制定溶栓治療方案。溶栓前需判斷以下問題:首先要排除禁忌證,如近期大手術(shù)、近期創(chuàng)傷史、近期未控制的活動(dòng)性出血、嚴(yán)重高血壓、主動(dòng)脈夾層等。其次是評(píng)估患者的意愿及整體情況,如年齡、營(yíng)養(yǎng)狀況、肝功能、腎功能、凝血功能等。最后再考慮適應(yīng)證,溶栓治療的最佳適應(yīng)證是急性癥狀性PVT,伴有血漿D-二聚體水平增高,且門靜脈高壓癥狀輕,無(wú)門靜脈海綿樣變性。條索化PVT或廣泛門靜脈海綿樣變性不適合溶栓。
溶栓治療方式主要包括全身溶栓和局部溶栓。局部溶栓包括經(jīng)皮肝穿刺、經(jīng)頸靜脈穿刺或腸系膜上動(dòng)脈置管溶栓等。鑒于經(jīng)皮肝穿刺途徑的潛在出血風(fēng)險(xiǎn),應(yīng)謹(jǐn)慎選擇[57]。溶栓治療期間,需密切動(dòng)態(tài)監(jiān)測(cè)血漿D-二聚體水平和凝血功能,避免出血并發(fā)癥;溶栓治療3~5 d后評(píng)估血管通暢情況;最長(zhǎng)溶栓治療時(shí)間≤2周。溶栓治療后可根據(jù)門靜脈再通情況和患者整體情況判斷是否需要繼續(xù)口服抗凝藥物及其療程。
在一項(xiàng)意大利單中心研究[58]中,9例診斷為近期PVT的肝硬化患者連續(xù)靜脈泵入0.25 mg·kg-1·d-1重組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物聯(lián)合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最長(zhǎng)療程為7 d;4例患者達(dá)到門靜脈完全再通,4例患者門靜脈部分再通,1例患者PVT穩(wěn)定;無(wú)臨床顯著的不良事件發(fā)生。經(jīng)腸系膜上動(dòng)脈間接溶栓或經(jīng)門靜脈直接溶栓可有效、安全地治療肝硬化急性或亞急性門靜脈和腸系膜靜脈血栓[59-60]。一項(xiàng)隨機(jī)對(duì)照試驗(yàn)[60]也比較了經(jīng)腸系膜上動(dòng)脈持續(xù)泵入15 000 IU· kg-1·d-1尿激酶與TIPS治療肝硬化PVT的療效差異。雖然溶栓組與TIPS組的門靜脈主干血栓的再通率相近,但溶栓組的腸系膜上靜脈和脾靜脈血栓的再通率顯著高于TIPS組,且肝性腦病發(fā)生率更低[60]。鑒于溶栓治療導(dǎo)致出血的潛在風(fēng)險(xiǎn)高,未來(lái)仍需更多高質(zhì)量研究探討溶栓治療肝硬化PVT的安全性。
7.3 經(jīng)頸靜脈肝內(nèi)門體分流術(shù)(TIPS)
共識(shí)意見24:肝硬化PVT患者行TIPS的適應(yīng)證主要包括抗凝治療效果欠佳或存在抗凝治療禁忌證、合并GEV出血但常規(guī)內(nèi)科止血療效不佳、急性癥狀性PVT合并GEV出血。
TIPS開通PVT的優(yōu)勢(shì)為可在肝內(nèi)建立門腔分流道以加快門靜脈血液回流速度,使更多淤積在門靜脈系統(tǒng)血管內(nèi)的血液回流入下腔靜脈,對(duì)局部血栓產(chǎn)生沖刷效應(yīng)[61]。TIPS對(duì)肝硬化PVT患者的技術(shù)可行性已得到認(rèn)可,但在肝內(nèi)門靜脈閉塞和門靜脈海綿變性側(cè)支血管管徑細(xì)小的患者中,TIPS技術(shù)難度仍非常高。TIPS主要的適應(yīng)證包括抗凝治療效果欠佳或存在抗凝治療禁忌證、合并GEV出血但常規(guī)內(nèi)科止血療效欠佳、急性癥狀性PVT合并GEV出血。對(duì)于高危GEV但未出血的PVT患者,是否可早行TIPS值得進(jìn)一步探討。
我國(guó)西安、成都、北京、昆明等地的研究已報(bào)道了TIPS對(duì)肝硬化PVT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數(shù)據(jù)。與傳統(tǒng)內(nèi)鏡聯(lián)合普萘洛爾和抗凝藥物治療相比,TIPS治療能明顯提高PVT再通率和顯著降低再出血率,但對(duì)生存率無(wú)明顯改善[34,62-68]。TIPS術(shù)后需警惕發(fā)生腹腔內(nèi)出血和肺栓塞的可能,建議至TIPS經(jīng)驗(yàn)豐富的醫(yī)療單位進(jìn)行該手術(shù)。也應(yīng)注意TIPS支架將增加未來(lái)肝移植手術(shù)難度。
8 有待解決的問題
(1)早期識(shí)別肝硬化PVT的高風(fēng)險(xiǎn)人群有助于盡早啟動(dòng)預(yù)防措施,但目前尚缺少可以準(zhǔn)確預(yù)測(cè)肝硬化PVT風(fēng)險(xiǎn)的模型。旋轉(zhuǎn)式血栓彈力測(cè)定、血栓彈力圖和凝血酶生成測(cè)定等可全面檢測(cè)凝血功能,其在預(yù)測(cè)肝硬化PVT風(fēng)險(xiǎn)方面的價(jià)值應(yīng)進(jìn)一步探討。
(2)及早啟動(dòng)治療可增加肝硬化PVT的開通率,但一部分患者可能無(wú)需任何抗凝治療即可達(dá)到門靜脈開通。因此,應(yīng)進(jìn)一步明確肝硬化PVT啟動(dòng)治療的最佳時(shí)機(jī)。
(3)抗凝治療是肝硬化PVT最重要的治療手段之一,但抗凝藥物的種類、劑量、療程都可能影響治療結(jié)局。因此,應(yīng)進(jìn)一步優(yōu)化肝硬化PVT抗凝治療方案。
(4)出血是抗凝治療期間最常見的不良反應(yīng)之一。肝硬化患者存在消化道出血風(fēng)險(xiǎn),且伴有血小板減少癥。早期預(yù)測(cè)、有效監(jiān)測(cè)可降低或規(guī)避出血風(fēng)險(xiǎn),但尚缺乏特異的方法。未來(lái)研究應(yīng)明確嚴(yán)重血小板減少的界值以預(yù)判啟動(dòng)抗凝治療的出血風(fēng)險(xiǎn),也需探討如何監(jiān)測(cè)肝硬化PVT患者抗凝治療過程中的出血風(fēng)險(xiǎn)。
(5)溶栓治療所致的出血風(fēng)險(xiǎn)高,肝硬化PVT患者溶栓治療期間如何規(guī)避出血相關(guān)事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利益沖突:專家組所有成員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執(zhí)筆者:祁興順(北部戰(zhàn)區(qū)總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楊玲(華中科技大學(xué)同濟(jì)醫(yī)學(xué)院附屬協(xié)和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
參與修訂、討論和定稿的專家(按姓氏漢語(yǔ)拼音排序):陳東風(fēng)(陸軍軍醫(yī)大學(xué)陸軍特色醫(yī)學(xué)中心消化內(nèi)科),陳立剛(廈門大學(xué)附屬中山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丁惠國(guó)(首都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北京佑安醫(yī)院消化中心),高艷景(山東大學(xué)齊魯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姜海行(廣西醫(yī)科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李弼民(南昌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李良平(四川省人民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劉杰(復(fù)旦大學(xué)附屬華山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劉梅(華中科技大學(xué)同濟(jì)醫(yī)學(xué)院附屬同濟(j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劉玉蘭(北京大學(xué)人民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陸翠華(南通大學(xué)附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陸倫根(上海市第一人民醫(yī)院消化科),陸偉(天津醫(yī)科大學(xué)腫瘤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馬雄(上海交通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附屬仁濟(j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祁小龍(蘭州大學(xué)第一醫(yī)院門靜脈高壓研究所),祁興順(北部戰(zhàn)區(qū)總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任曉非(安徽醫(yī)科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沈錫中(復(fù)旦大學(xué)附屬中山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舒慧君(中國(guó)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xué)院/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 王鳳梅(天津市第二人民醫(yī)院肝內(nèi)科),王吉耀(復(fù)旦大學(xué)附屬中山醫(yī)院消化科復(fù)旦大學(xué)循證醫(yī)學(xué)中心),王小眾(福建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協(xié)和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王擁軍(首都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北京友誼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吳浩(四川大學(xué)華西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謝渭芬(海軍軍醫(yī)大學(xué)長(zhǎng)征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徐嚴(yán)(吉林大學(xué)中日聯(lián)誼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徐毅 (浙江省中醫(yī)院消化科),徐有青(首都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北京天壇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許國(guó)強(qiáng)(浙江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附屬第一醫(yī)院消化科),楊長(zhǎng)青(同濟(jì)大學(xué)附屬同濟(j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楊玲(華中科技大學(xué)同濟(jì)醫(yī)學(xué)院附屬協(xié)和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楊妙芳(東部戰(zhàn)區(qū)總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姚冬梅(河北醫(yī)科大學(xué)第二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曾維政(西部戰(zhàn)區(qū)總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曾欣(同濟(jì)大學(xué)附屬東方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張國(guó)(廣西壯族自治區(qū)人民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張莉(北京大學(xué)第三醫(yī)院消化科),張修禮(解放軍總醫(yī)院第一醫(yī)學(xué)中心胃腸病及肝病中心),鐘碧慧(中 山大學(xué)附屬第一醫(yī)院消化科),周璐(天津醫(yī)科大學(xué)總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周新民(空軍軍醫(yī)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朱強(qiáng)(山東省立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諸葛宇征(南京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附屬鼓樓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鄒曉平(南京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附屬鼓樓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