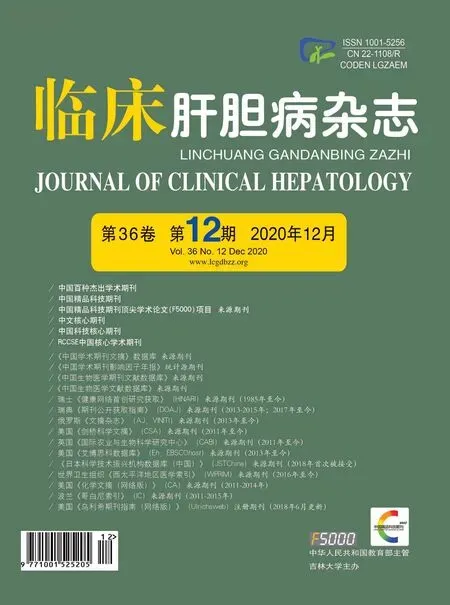細胞焦亡在肝臟疾病中的作用
肖偉松, 樂瀅玉, 曾勝瀾, 覃小賓, 吳 聰, 牙程玉, 毛德文
1 廣西中醫藥大學 研究生學院, 南寧 530222; 2 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肝病一區, 南寧 530023
肝臟炎癥已被證實與肝硬化、感染誘導的肝纖維化以及肝細胞癌(HCC)發展過程中的細胞焦亡有關[1]。細胞焦亡參與了針對細胞內細菌感染的免疫防御機制。作為促炎性程序性細胞死亡的一種新形式,正常情況下,有助于及時清除感染細胞,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過度的炎癥小體激活會誘發無菌炎癥,導致大量細胞死亡、嚴重組織損傷和器官衰竭,并最終導致某些疾病,例如急性或慢性肝炎和肝纖維化。因此,本綜述將重點論述細胞焦亡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酒精性肝病(ALD)、病毒性肝炎、肝纖維化和HCC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機制。
1 細胞焦亡的典型特征
細胞焦亡是依賴caspase-1/4/5/11介導的一種新型的程序性細胞死亡,caspase-1/4/5/11是一類促炎性半胱氨酸蛋白酶,均屬于caspase家族。細胞焦亡是機體應對細菌入侵的重要先天免疫反應。但是,過度的細胞焦亡可能會導致敗血性休克和其他免疫疾病。有研究[2]表明,在各種微生物和內源性刺激的情況下,人類的caspase-1/4/5和小鼠的caspase-1/11被激活以裂解gasdermin D(GSDMD)蛋白,導致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的細胞膜破裂,證明焦亡細胞質膜的破裂與GSDMD蛋白密切相關,caspase-1/11能夠切割GSDMD的接頭結構,釋放gasdmin-N端結構域,然后其與質膜的內部小葉相結合發生寡聚化,在細胞膜上形成1~2 nm的孔隙,從而增大了細胞膜的通透性,K+外流、Na+內流,細胞的離子梯度消失,細胞內滲透壓增加,細胞膜失去了調控物質進出的能力,迅速膨脹,最終導致細胞滲透性崩解。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P)等細胞內容物釋放到細胞外環境中,募集更多細胞因子,進一步延續組織中的炎癥級聯反應。細胞焦亡主要受兩個主要途徑調控:caspase-1誘導的經典型炎癥途徑和caspase-11誘導的非經典型炎癥途徑[3]。在經典型細胞焦亡中,來自細胞膜的一系列DAMP通過典型的炎癥小體激活caspase-1,從而釋放GSDMD-N末端以引發焦亡。對于非經典型細胞焦亡,細胞質脂多糖(LPS)激活capase-4/5/11后,主要通過裂解GSDMD來誘發細胞程序性死亡,其發生不同于經典型,不依賴于炎癥小體和caspase-1。
1.1 經典細胞焦亡途徑分子機制 經典型細胞焦亡途徑的激活主要由多種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和DAMP觸發,依賴于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PRR)接受危險信號分子刺激,通過ASC招募caspase-1前體(pro-caspase-1)組裝形成炎癥小體,并激活caspase-1分子進一步切割下游GSDMD目的蛋白,最終促進細胞焦亡的發生[4]。炎癥小體一般包括3個主要成分[5]: (1) 感受器:位于細胞質內的PRR, 主要有NOD樣受體 (NOD-like receptor,NLR)和黑色素瘤缺乏因子2樣受體 (absent in melanoma 2,AIM2) ; (2) 效應器:pro-caspase-1; (3) 凋亡相關微粒蛋白 (apoptosis 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RD, ASC) :將PRRs與pro-caspase-1結合起來的銜接蛋白。新興證據[6]表明,已經鑒定出5個典型的炎性小體,包括NLRP1、NLRP3、NLRP4、NLRP7和IFI16,均可由不同的刺激觸發[6]。在細胞焦亡的最初過程[7]中,炎癥小體通過NOD樣受體(NLRP1、3、6、7、12,NLRC4)和AIM2激活caspase-1,同時通過ASC的同源蛋白互作結構域和C端半胱天冬酶募集域(CARD)的寡聚化來募集上下游的PRR和pro-caspase-1,組裝成炎癥小體進行下游的信號轉導。通過CARD-CARD相互作用將pro-caspase-1募集到ASC中,導致其裂解成N端前結構域和C端催化和相互作用結構域;形成二聚體的pro-caspase-1進一步裂解成為p10亞基、p20亞基,并激活其自身的蛋白酶生成caspase-1。炎性體復合物的形成最終導致caspase-1的活化,將會誘導促炎性前體細胞因子(pro-IL-1β和pro-IL-18)的蛋白水解,從而釋放出活性的IL-1β和IL-18,最終誘導細胞焦亡。
1.2 非經典細胞焦亡途徑分子機制 多年來,caspase-1介導的途徑被認為是介導焦磷酸化的唯一途徑。但在2011年,Kayagaki等[8]觀察到caspase-11對于感染大腸桿菌、嚙齒動物檸檬酸桿菌和霍亂弧菌的巨噬細胞中IL-1β的產生和焦磷酸化至關重要,可激活小鼠巨噬細胞中caspase-11介導的信號傳導途徑,導致IL-1β/IL-18的成熟和釋放,這揭示了細胞焦亡的另一條調控途徑。與經典型途徑不同,非經典型焦亡途徑依賴于caspase-4/5/11的激活。具體而言,caspase-4/5/11通過其CARD結構域直接與LPS尾部的脂質體A相結合,可促進其自身的寡聚化和激活,活化的胱天蛋白酶裂解GSDMD可產生具有生物活性的GSDMD-NT,從而導致細胞焦亡的發生[9]。因此,在非經典型細胞焦亡途徑中,炎癥小體的裝配對于caspase-4/5/11介導的GSDMD裂解不是必需的。GSDMD-NT引起caspase-1依賴性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導致IL-1β和IL-18的分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細化,一些新的分子機制逐漸被發現[10]。Pannexin-1是細胞膜上的通道蛋白,控制小分子物質進出,caspase-11的激活會導致Pannexin-1蛋白斷裂形成通路,將ATP釋放到細胞外,當P2X7受體受到ATP長期反復的刺激時,P2X7通道開放使K+、Na+、Ca2+外流,打破細胞膜內外離子平衡,細胞發生滲透性腫脹進而膜破裂,最終導致細胞死亡。值得令人思考的是,LPS可直接與caspase-4/5/11的CARD域結合,但不與其他caspase結合。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解釋其具體作用機制,需要對LPS結合的caspase-4/5/11進行結構性研究以證實這些發現。
1.3 細胞焦亡的關鍵蛋白——GSDMD 最近的研究[11]已確定蛋白GSDMD是活性caspase-11和caspase-1的主要底物。Gasdermin(GSDM)蛋白家族是先天免疫和細胞死亡反應的調節劑。GSDMD包含一個N末端(gasdermin-N)和一個C末端(gasdermin-C),兩者通過一個環連接。gasdermin-N結構域具有強大的成孔活性,可與gasdermin-C結構域相互作用并受其抑制。激活的caspase-1和4/5/11裂解了GSDMD中的連接環,從而啟動了gasdermin-N結構域的自抑制作用。未釋放的gasdermin-N結構域通過與膜磷酸肌醇結合而遷移到質膜上,促使細胞膜穿孔,從而引起細胞腫脹并最終導致滲透裂解。GSDMD孔釋放細胞內容物,包括炎性細胞因子IL-1β和IL-18,這是caspase-1的其他底物。此外,活化的caspase-11裂解pannexin-1(ATP的膜通道)的胞質區,從而誘導ATP的細胞外釋放,后者以自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與P2X7受體結合,從而打開P2X7的通道,最終,小分子物質(例如Na+,水,胞質蛋白和促炎因子)將從通道流出,而較大的細胞器(如核糖體)將在細胞中被阻塞,最終導致細胞死亡,并在細胞周圍引發一系列免疫炎癥反應[12],從而導致細胞焦亡。GSDMD屬于gasdermin家族,其包含人類的6個成員和小鼠的10個成員。所有家族成員(DFNB59除外)都具有兩域結構,其gasdermin-N結構域能夠誘導細胞焦亡。最近的研究[13]表明,GSDME、GSDMA和GSDMA3的gasdermin-N結構域也能夠在體外的脂質體或單層膜上形成孔,提示了gasdermin家族采用了一種成孔機制來裂解細胞并執行焦磷酸化,這可能將焦磷酸化重新定義為gasdermin介導的程序性壞死細胞死亡。但是,gasdermin-N結構域組裝孔以穿透脂質膜的機制尚不清楚。
2 細胞焦亡與肝臟疾病的關系
2.1 細胞焦亡與ALD的關系 ALD是慢性肝病和導致肝纖維化、肝硬化的一個重要病因。由于ALD的損傷機制錯綜復雜,具體致病分子機制尚不清楚,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策略。故對ALD的發病機理和分子調控機制的了解將有助于開發良好的診斷指標以及預防和治療方法。近年來發現細胞焦亡可能是ALD發生、發展的關鍵機制。Khanova等[14]使用RNA測序分析發現,經組織學驗證的酒精性肝炎患者和小鼠肝組織中的caspase-4/11基因上調,但慢性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小鼠和健康的人類肝臟中沒有。另有研究[15]表明,在酒精喂養的小鼠中NLRP3、caspase-1和IL-1β高表達,而在NLRP3-/-或caspase-1-/-小鼠中,肝臟炎癥和脂肪變性卻明顯減弱。由此可見,NLRP3炎性小體參與了ALD的發生發展,酒精對細胞焦亡的影響是由PAMP和DAMP所觸發,例如ATP和可溶性尿酸,從乙醇誘發受損的原代肝細胞中釋放,并觸發炎性依賴性細胞因子的釋放,刺激并維持ALD的炎癥周期。在肝細胞中酒精代謝也增加活性氧(ROS)的產生和導致線粒體功能障礙,從而增加炎性細胞因子對肝細胞的敏感性。此外,酒精還可通過叉頭盒蛋白O1降低肝細胞中miRNA-148a的表達,并誘導硫氧還蛋白相互作用蛋白(TXNIP,α-arrestin家族成員)的過表達。TXNIP結合并促使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從而導致caspase-1介導的細胞焦亡。值得重視的是,有研究[16]證明慢病毒傳遞引起的肝細胞特異性表達miRNA-148a可直接抑制硫氧還蛋白與NLRP3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減緩細胞焦亡和降低ALD的發生率。上述報告提供了證據和方向,表明NLRP3炎性小體在ALD的發展過程中具有致病性,但是,啟動NLRP3激活的觸發因素尚待確定。
2.2 細胞焦亡與NAFLD的關系 NAFLD是一種無過量飲酒史, 以彌漫性肝細胞大泡性脂肪變性為主要特征的臨床病理綜合征。其病程包括單純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和脂肪性肝纖維化, 最后可能演變成肝硬化和HCC。目前對于NALFD病理機制認識尚淺,缺乏有效的治療對策,因此如何延緩NAFLD進展并嘗試逆轉這一過程一直是倍受關注的話題。研究[17]發現在NAFLD發展成為NASH的過程中, 細胞焦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加速了這一病理進程,并加重了肝臟的炎癥反應。最近的研究[18]表明,與普通飲食喂養的小鼠相比,NAFLD小鼠的NLRP3、ASC和caspase-1的表達明顯增加。在HepG2和L02細胞中證實了相同的結果,表明抑制NLRP3活性會降低兩種細胞系中脂質的積累。另有試驗[19]發現,NAFLD患者肝臟的NLRP3、IL-1β、IL-18和pro-caspase-1 mRNA水平顯著高于健康人群。值得重視的是,NAFLD發病的始動因素與胰島素抵抗有著緊密的聯系。而NLRP3可通過激活與胰島素抵抗相關的炎性因子(IL-1β、IL-18和NF-κB),促進NAFLD的病理進展。此外,在NAFLD狀態下,肝細胞承受過度的氧化應激,產生過量的ROS。使TXNIP與硫氧還蛋白分離,從而激活了NLRP3。有研究[20]表明TXNIP上調會導致IL-1β和IL-18的分泌增多,加重肝臟炎癥反應。在NASH模型中,具有IL-1α和IL-1β基因敲除的小鼠顯著減緩了從脂肪變性到脂肪性肝炎的病理過程,而IL-1β通過與TNFα的協同作用增加了肝細胞的TG水平并誘導肝細胞死亡。由此可見,抑制NLRP3炎性小體形成和活化的過程,能夠減弱肝臟細胞焦亡后引起的肝臟炎癥反應、細胞損傷和脂肪變性的現象, 具有一定減緩NAFLD的作用。
2.3 細胞焦亡與病毒性肝炎的關系 病毒性肝炎是肝炎病毒感染肝細胞并引起高病死率的肝臟炎癥,其中約90%可歸因于HBV和HCV引起的慢性感染, 嚴重的病毒性肝炎發展成肝纖維化、肝硬化甚至HCC。值得注意的是,NLRP3炎性小體是病毒性肝炎發生發展的潛在因素。研究[21]發現,活動性未經治療的慢性HBV患者肝臟的NLRP3、caspase-1和IL-1β的表達水平明顯高于慢性緩解的患者。此外,在HBV感染者中,IL-1β的水平與肝臟炎癥的嚴重程度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由此可見,NLRP3介導的IL-1β是HBV誘導的病毒性肝炎的潛在驅動力。此外,有關HCV感染的研究[22]表明,Kupffer細胞已被鑒定為慢性HCV感染者IL-1β的主要細胞來源,Kupffer細胞產生的IL-1β與炎癥反應增強有關。另外NLRP3炎性體亦能刺激肝細胞中脂質滴的形成,從而促進HCV的形態變化和復制,加速了肝臟疾病的進展。因此,進一步研究HBV和HCV與肝臟細胞焦亡關系, 能夠更深層次的探索人肝炎病毒誘導肝臟疾病產生和發展的致病機制。
2.4 細胞焦亡與肝纖維化的關系 肝纖維化是各種病因導致的細胞外基質 (ECM) 的形成與降解失衡, 使得ECM過度沉積并最終可發展為肝硬化和HCC。近年來發現,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在肝纖維化的發病機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肝纖維化的病理過程中,最顯著的表征是肝星狀細胞 (HSC)的激活。HSC具有促纖維化、促炎效應等性質, 激活過程中分泌多種ECM的成分, 如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A)、膠原蛋白等。在HSC中的NLRP3炎癥小體活化可導致α-SMA陽性細胞數量增加, 而α-SMA陽性是HSC活化的關鍵標志物, 與肝纖維化的發展密切相關。因此, NLRP3炎癥小體活化可激活HSC, 繼而導致肝纖維化發生、發展。研究[23]表明,與NLRP3-/-和ASC-/-小鼠相比,野生型小鼠具有更高的α-SMA表達和更大的天狼星紅染色面積,誘發嚴重的肝纖維化,證明了上述觀點。相反,小鼠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促進了肝臟炎癥和纖維化的病理過程。值得注意的是,活化的caspase-1、IL-18和IL-1β信號傳導也是使得NLRP3炎性小體活化,從而導致肝纖維化發展的關鍵。IL-1β和IL-18均可誘導膠原蛋白的沉積。有報道[24]MCC950是一種可阻斷NLRP3炎性體的藥物,降低肝臟caspase-1的表達以及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的數量,最終緩解肝纖維化,說明通過阻斷NLRP3炎性小體激活可能是治療肝纖維化的關鍵機制。研究[25]表明,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對肝纖維化具有調節作用。血管緊張素Ⅱ(Ang Ⅱ)是RAS的關鍵分子,它誘導NADPH氧化酶4/線粒體來源ROS的生成并加劇肝纖維化,而NLRP3的激活與兩者的生成緊密相關。Ang Ⅱ的抑制作用通過減少ROS的產生并影響NLRP3炎性小體的活化而減輕了肝纖維化。NF-κB信號在肝纖維化的病理過程中也很重要[26],NLRP3炎性小體的活化則伴隨著NF-κB信號的上調。抑制NF-κB信號傳導以及促進HSC凋亡可改善肝纖維化。這些因素與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密切相關,由此可見,通過探索對NLRP3炎性小體活性抑制的具體分子作用機制,從而預防和治療肝纖維化將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2.5 細胞焦亡與HCC的關系 HCC是肝臟中最常見,最具侵略性的原發腫瘤,治療選擇有限。手術切除被認為是標準的治療方法之一。但HCC仍表現出較高的術后復發率,進展迅速且預后極差。迫切需要尋找新的HCC治療靶點。細胞焦亡作為一種新的細胞程序性死亡方式, 可能是繼細胞衰老、凋亡后新的治療HCC的方法。Xia等[27]發現,NLRP3在HCC組織中的表達顯著下調,甚至完全不存在,并且與HCC的病理分級和臨床分期呈負相關,表明NLRP3炎性小體參與了HCC的發展進程。考慮到HCC發生率的性別差異,17β-雌二醇(E2)和雌激素受體(ER)β等因素也受到了重視。研究[28]表明,ERβ的表達在HCC組織中也降低,并且發現用E2激活的NLRP3炎性小體通過E2/ERβ/MAPK信號處理的HCC細胞系(SMMC7721、BEL7402和HepG2細胞)最終改善了HCC的進程。此外,E2處理激活的NLRP3炎性體誘導HepG2細胞中的caspase-1依賴性凋亡,導致HCC進程受到抑制。結果表明,E2和ERβ通過激活NLRP3炎性小體引發焦磷酸化,發揮抗癌作用。另外,關于晚期HCC的研究[29]發現, AIM2炎癥小體通過阻滯mTOR-S6K1信號通路, 使雷帕霉素靶蛋白對S6K1蛋白的激活作用減弱, 從而抑制HCC細胞生長、增殖, 且AIM2炎癥小體的堆積會使HCC細胞發生焦亡, 進而發揮抗腫瘤效應。表明通過誘導AIM2炎癥小體表達, 增強細胞焦亡的效應, 可能延緩HCC的進展。綜上所述,細胞焦亡有關的因素具有促進和抑制腫瘤發生的雙重機制。以藥理學靶向NLRP3炎性體可能會抑制HCC的增殖和轉移,這表明這可能是一種新的治療策略。
3 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細胞焦亡作為一種新型炎性相關的程序性死亡方式,其在慢性肝臟疾病發生發展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通過阻斷相關分子(例如NLRP3 caspase、IL-1)抑制焦磷酸化影響肝病的進展,并為肝病提供了一種潛在未來的治療方法。但是基于細胞焦亡研究肝臟疾病的領域仍然存在著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1)由于焦磷酸化是抵抗病原體必不可少的防御路線,抑制磷酸化可能會增加機會性感染,目前,要轉化為臨床療效,仍需要大量的研究。(2)PRR激活和細胞穩態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對生理功能的影響仍在研究中,許多PRR的功能和特異性配體仍然未知,了解受體激活機制和配體識別的受體結構對于設計新的免疫療法將是至關重要的。(3)此外,肝纖維化中炎癥小體信號傳導的機制尚有許多未知,需要進一步研究以闡明炎癥小體類型及其在不同類型肝損傷中的作用之間的相關性,以期為開發抑制炎癥小體組裝或作用于下游信號分子的療法提供機會。(4)值得注意的是,GSDMD主要在免疫細胞和胃腸道中表達,肝細胞中的表達水平可能較低。將來需要在免疫細胞和肝細胞中使用組織特異性GSDMD KO小鼠的工作將有助于確定細胞焦亡在免疫細胞與肝細胞中在酒精性肝炎的發病機制中的作用。(5)炎癥和細胞焦亡在NAFLD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中,還需要在更大且獨立的患者隊列中驗證肝臟GSDMD和GSDMD-N表達與NASH評分和纖維化指數之間的相關性,將其表達與疾病晚期(如NAFLD肝硬化)和/或NAFLD-HCC進行比較,可有助于確定其預后價值和治療干預措施的適當疾病階段。目前細胞焦亡調控肝臟疾病的具體機制尚不清楚, 還存在很多尚未闡明的關鍵科學問題。該領域的探索能夠為預防和治療慢性肝臟疾病提供新的方法和策略。
作者貢獻聲明:毛德文、肖偉松負責課題設計,資料分析,撰寫論文,修改論文;毛德文、肖偉松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樂瀅玉、曾勝瀾、覃小賓、吳聰、牙程玉參與收集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