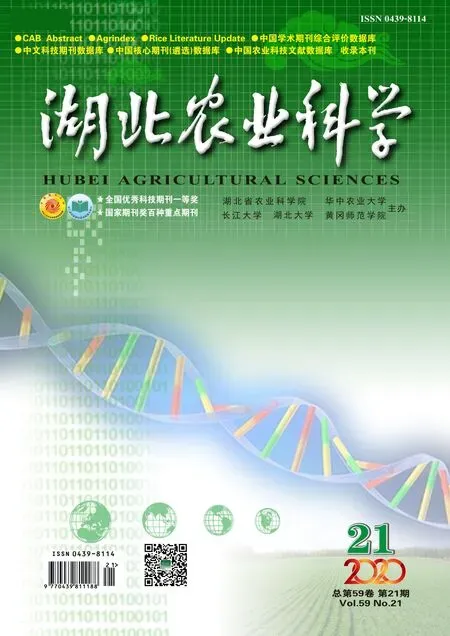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中國糧食安全的法制思考
郭曉蕊
(河海大學法學院,南京 211100)
近年來,中國糧食產量連年增收,但在人口數量、收入水平不斷提升的情況下,供求關系依然緊張,糧食進口量居高不下。美國作為中國農產品主要進口市場之一,中美貿易摩擦給中國國內糧食安全帶來較大影響,這使我們清晰認識到糧食安全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健全的糧食法制體系才能撐起糧食安全屏障,使中國踏上糧食生產強國之路。
1 中國糧食安全面臨的挑戰
1.1 糧食需求缺口增大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中國糧食安全領域的短板逐步顯露,首先體現在糧食需求缺口不斷增大。如大豆的需求缺口不斷增大,2018年中國大豆總產量1 600萬t,不足進口量的20%,同年中國進口美國大豆共1 664萬t,同比下降49.3%。由于美國是中國大豆進口主要來源國,且與另一主要來源國巴西大豆的成熟期不同,即使中國相繼拓展大豆進口來源國并加大其他國家的進口量,也難以彌補目前國內的需求缺口。其次,糧食需求缺口繼而引發國內部分糧食價格出現波動。糧價乃百價之基,糧價不穩勢必影響到社會各個方面。如提取大豆油的副產品豆粕是制作牲畜與家禽飼料的主要原料[1],由于國內大豆供給不足,導致近期雞蛋等價格飛速上漲卻依然供不應求。再次,國內糧食生產穩定性受到影響。針對大豆供給不足、過度依賴進口等情況,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大豆振興計劃,并出臺了加大種植大豆農業補貼的政策。但在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有限的耕地資源分配會變得更加艱難,大豆種植面積擴張勢必擠壓其他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導致其他糧食作物產量出現波動。
1.2 糧食主產區亟需轉型升級
糧食主產區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目前中國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結構性矛盾突出,亟需轉型升級。首先,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收入水平提高,食品消費結構發生轉變,直接口糧消費逐年下降,肉禽蛋奶等間接口糧消費持續增加。但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無法滿足食品消費結構升級的現狀,在大豆和優質小麥、高粱等糧食作物供給方面一直未能擺脫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其次,中國糧食安全面臨“天花板”與“地板”的雙重擠壓[2],農民的種糧利益得不到保障。一方面,部分糧食的價格高于國外糧食進口到岸完稅后的價格,國內外糧價出現倒掛;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種糧人口減少,勞動力價格和土地租金逐漸上漲等原因快速推高了糧食生產成本。最后,中國地少人多,耕地數量緊缺且地塊分散、中低產田居多、受污染狀況嚴重[3],糧食產量與質量參差不齊。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資金和技術投入,還需要從法律層面明晰糧食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完善糧食種植、流通、進出口等制度,加快糧食主產區的轉型升級。
2 中國糧食安全法制現狀與問題
2.1 缺乏糧食安全相關法律
糧食安全具有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地位,但國內糧食安全立法卻與其戰略地位不符。調整糧食安全的法律法規除《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和《農業法》“糧食安全”章節中的6個條文之外,主要依靠糧食政策來保證糧食產業的發展。不可否認,自2004年《糧食流通管理條例》頒布實施以來,各級糧食行政管理部門嚴格按照《條例》賦予的職責,結合相關政策的指引,對糧食生產、流通等領域的監管取得了顯著成效[4]。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及國際形勢的變化,一些影響糧食安全的新問題、新挑戰亟需通過法律來解決。如糧食主產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后,與主銷區財政收入相差較大[5];在增添、修繕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和改造中低產田、加大糧食補貼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方面存在不足,需要通過利益補償機制來平衡產銷區的發展。然而僅通過《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及各項政策中的鼓勵性質條款推動糧食產銷區之間建立長效合作機制,缺乏實際操作性。
當前中國處于從追求糧食產量到重視糧食整體安全的關鍵轉型時期,由于需要全國統籌,涉及面廣、問題較多,糧食安全相關法律時至今日還未出臺。完善的糧食安全法制體系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基石,沒有健全的糧食安全法制體系,糧食安全行政主管部門權責不清,產銷區利益補償機制無法落實。德、美、日等國家農業發展迅猛的原因除了科學技術水平發達之外,更重要的是具備完善的法律制度[6]。中國也必須通過法律制度的頂層設計來規范糧食產業秩序,保障糧食安全。
2.2 農村土地流轉法律規定不完善
根據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后的規定,耕地分配時應先根據土地肥力、位置等因素劃分不同地塊,之后將不同土地再次均分給每位農民。雖是為了保障公平,但造成農村耕地細碎化問題嚴重。為解決這一問題,提高土地利用率,中國于2014年提出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即土地所有權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變,將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進一步劃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農民有權將經營權通過簽訂土地經營流轉合同在一定期限內流轉出去以此獲得收益。2018年《農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正正式確立了“三權分置”制度。“三權分置”制度在中國農村推行之后,從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但并未出現預期的大規模增產,究其原因在于制度設計不合理,未能闡清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離之后的權利內涵和邊界,也未有相應的法律程序確保該制度的有效實施。同時,目前關于“三權分置”的法律法規及研究等基本以做大經營權為目標,集體經濟所有權虛化[7],如現實中缺乏集體經濟組織對土地的調控、農村土地分配混亂、無法確保農民有足夠的土地分配將影響農村穩定[8]。此外,相關土地流轉程序及市場機制規定不健全,實際流轉過程中問題頻發,如缺乏土地流轉法律服務機構等第三方服務機構,導致出現盲目流轉、低價流轉等不公平現象[9]。
2.3 糧食生產污染缺乏法律規制
中國過去以犧牲農業環境為代價來追求糧食高產的模式導致現階段糧食生產面臨土壤環境污染、耕地質量低下、高投入低產出等困境。不僅是糧食行業,整個農業行業的生態環境都是如此。糧食生產污染屬于農業污染的一種,沒有專門的立法予以防治,只能按照農業相關法律進行保護與防治。而有關農業污染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規定散見于《農業法》《環境保護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其他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專項法律。推動生態農業發展的措施基本以政策、政府發展規劃等形式為主,現有的規范性文件位階較低,無法涵蓋生態農業發展所需要的各個方面[10],如對糧食生產資料過量投入、輪作休耕制度與土地持續退化等在法律方面缺乏應對的手段。
3 中國糧食安全法制建設的對策思考
3.1 加快出臺糧食安全相關法律
糧食安全涉及多個方面,包括生產、倉儲、物流、進出口等,目前《農業法》《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及其他關于糧食安全的規定,已不足以調整中國的糧食安全法律關系,當務之急是加快出臺糧食安全相關法律。首先,應落實耕地保護目標責任制,提高區域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管好地方糧食儲備,確立糧食質量標準,維持糧食價格穩定,加強糧食安全監測與預警應急機制等。其次,拓展糧食社會監管與救濟途徑。糧食產業具有公益性[11],在保障政府宏觀調控的基礎上,可以仿照環境公益訴訟引入糧食安全公益訴訟,確認檢察機關和糧食行業協會等的原告資格,形成除了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之外自下而上的新型監管救濟機制,保障糧食市場利益主體的合法權益,全面維護糧食安全。最后,明確各糧食安全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避免出現部門職能交叉重疊、多部門共同執法的現象。
3.2 優化“三權分置”制度
中國獨特的集體所有制加上農業人口眾多,要想擴大規模經營,注定不能像美國那樣推行農場模式[12],通過優化“三權分置”制度可以推進適度規模經營,增加糧食產量。首先,應當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性質與權利邊界,防止出現糾紛時無法尋求確定的救濟手段。其次,應當強化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將農民的承包權與特定地塊分離[13],避免農民的承包權與特定地塊產生聯系,從而影響集體對農村土地的調控力。最后,政府要健全土地流轉市場交易平臺,鼓勵外出就業的農民將土地流轉出去。建立縣、鄉兩級監督機制,監管農村集體所有權的實施,引入第三方專業化經營機構如法律服務機構,以減少低價流轉、盲目流轉等土地不公平流轉現象。健全解決糾紛機制,避免由于土地流轉糾紛從而影響規模化經營。
3.3 推進生態農業法律發展
中國應當加快建立生態農業法制體系,健全相關配套制度以應對糧食及其他農業污染。首先,在耕地保障方面,應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同時各省份應結合本省實際,以法律法規形式出臺程序性規定,使耕地輪作休耕制度具有可操作性[14]。糧食主產區政府應當嚴守耕地保護紅線,依照《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劃定基本農田,保證耕地資源數量及質量,并嚴格執行農業農村部每年關于農田建設的任務。其次,針對糧食污染問題,行政機關應嚴格依照《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進行追責,預防糧食生產資料等的不當使用行為,使生態農業融入農民的生產耕種之中。
4 小結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提升國內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才是硬道理。應健全糧食安全法制體系,并與環保、經濟等其他法制體系相銜接,遵循規范糧食產業秩序、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促進社會穩定的基本要求,逐步走上糧食生產強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