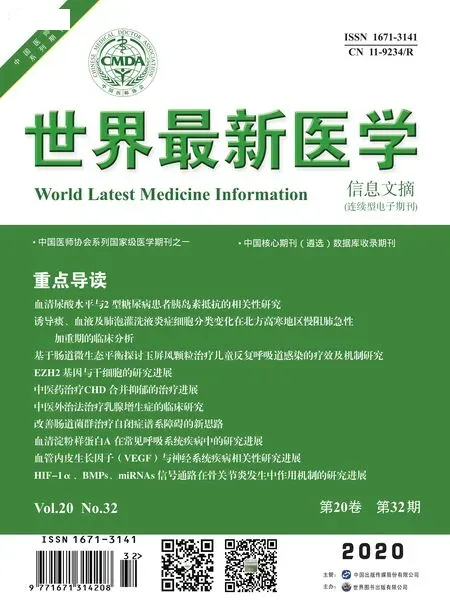慢性鼻竇炎病因病機研究進展
胡守亮,李璐
(成都中醫藥大學養生康復學院,四川 成都)
0 引言
慢性鼻竇炎(chronic sinusitis,CRS) 是一種鼻竇黏膜的炎性反應性疾病,其主要癥狀主要表現為鼻塞、流涕,同時伴有頭面部疼痛或腫脹壓迫感,病情嚴重時還會出現嗅覺減退、記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等[1]。病變過程中鼻竇黏膜常會伴隨一系列炎性反應并分泌出大量炎性分泌物,最終易導致鼻黏膜組織重塑,相關狀態持續12 周以上[2]。CRS 可分為伴息肉的慢性鼻竇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 nasal polyp,CRSwNP)和不伴息肉的慢性鼻竇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out nasal polyps,CRSsNP)兩種亞型。CRS 癥狀持續反復發作,不僅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同時也極大地增加了社會醫療成本,給國家社會經濟帶來巨大負擔。CRS可發生在各個年齡段,發病率約為5%~15%[3],并呈逐漸上升趨勢,所以CRS 的治療一直是研究的熱點。
CRS 的病程時間長,病因繁多,多由急性鼻竇炎轉化而來。CRS 的病因病機較為復雜,一般可從宿主局部性因素(鼻竇微生物平衡紊亂、黏膜纖毛功能障礙、解剖結構異常),宿主系統性因素(變態反應、伴隨疾病、免疫反應)歸納。
1 宿主局部性因素
1.1 鼻竇微生物平衡功能紊亂
鼻腔作為人體上呼吸道中的一部分,承擔著重要的清潔和生理保護屏障功能,鼻竇相關微生物在參與炎性反應自我抵抗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鼻竇腔一旦遭受細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感染,機體自我免疫功能紊亂,使其正常的微生物穩態結構失衡。研究表明,90%以上的健康人鼻腔中均有真菌定植[4]。Aurora 等[5]通過DNA 深度測序分析發現,真菌群在CRS 中的多樣性和豐度更高,新型隱球菌屬于鼻竇中較普遍性菌種,而馬拉色菌屬于CRS中最常見菌種之一,說明并非所有的真菌都屬于致病性菌群,當鼻竇真菌平衡穩態結構紊亂時,釋放相應炎性分泌物,導致炎性病理性損傷。
最新研究顯示微生物組失衡在CRS 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與該疾病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與某特定優勢菌種相比,病菌多樣性失衡致使CRS 發病概率增大[6]。鼻竇是一個微生物菌群的群落聚集處,其中包括了大量保護性菌群和致病性菌群[7]。鼻竇腔穩態結構本身是一個良性循環,保持著自我清潔和平衡,而當遭受細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感染時,隨著疾病遷延,導致黏膜局部的慢性持續炎癥反應,加劇鼻竇黏膜組織破壞,保護菌群和致病菌群失衡,宿主自生防御系統受損,最終易導致CRS 的發生。
1.2 鼻黏膜纖毛功能障礙
鼻黏膜纖毛傳輸系統障礙可分為兩型,即原發性纖毛運動障礙(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PCD)和繼發性纖毛運動障礙(secondary ciliary dyskinesia,SCD)。其中,PCD 屬于一種遺傳性不可逆的纖毛運動功能障礙,同時有研究發現PCD 纖毛運動功能障礙與CRS 患者基因變異密切相關[8],而SCD 主要是受后天外來環境等相關因素影響較大。原發性纖毛功能障礙由于黏膜纖毛缺乏蛋白臂,導致纖毛運動受限,清除能力下降而引起了疾病的發生[9]。由于PCD 中心微管發育不全,纖毛搏動頻率降低、外雙聯轉位不動及循環搏動等特征,導致其黏液纖毛自動清除功能障礙[10]。目前的研究發現,PCD 發病還與多種基因的突變有一定的相關性,如與編碼纖毛軸絲動力蛋白臂相關蛋白的DNAHll、DNAll 和DNAH5 突變可導致纖毛運動功能障礙,從而增大了PCD 發生的概率[11]。
鼻腔內粘液纖毛功能主要是通過粘液毯和纖毛上皮通過纖毛有規律的擺動,將呼吸道生成的及吸入的分泌物清除。而中性粒細胞釋放出的蛋白溶酶不僅能導致纖毛結構損傷,還能影響其正常運動功能。當鼻竇腔處于缺氧狀態時,其纖毛上皮ATP 產生減少,動能不足且運動明顯受限[12]。有研究表明[13]當遭受病毒感染和有害空氣污染時,會使呼吸道纖毛產生獲得性粘液纖毛功能障礙時,使復合纖毛形成和與呼吸上皮細胞修飾相關的外周微管改變。當病變嚴重時,甚至會有軸絲膜缺失、軸絲膜內氣泡、復纖毛、纖毛方向性喪失等超微結構的顯著損傷及改變,CRS 黏膜纖毛上皮還出現短纖毛再生、纖毛排列紊亂及鱗狀上皮化生,這些改變與疾病的嚴重程度明顯相關。鼻竇黏膜在多種因素刺激和影響下,會導致鼻黏膜出現水腫并伴有增生,并伴隨著炎癥反應長期存在并反復發展,最終致使鼻腔黏膜纖毛運動功能降低甚至喪失,鼻竇腔氣流受阻伴隨竇內分泌物淤堵,引起布局炎性反應惡化加劇,最終引發CRS[14-15]。目前,大多認為這些改變是由于細菌、真菌、病毒等有害微生物和不同程度炎性反應所釋放的分泌物刺激反復損傷導致。
1.3 鼻竇解剖結構異常
現在普遍認為是解剖結構異常是導致CRS 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鼻腔或鼻竇的解剖變異引起鼻竇引流不暢,竇口長期機械性阻塞使竇內氣壓發生變化,刺激并加劇鼻竇黏膜炎性分泌物水腫、充血嚴重程度,使引流受阻和鼻腔阻塞,形成惡性循環。在常見的解剖變異中,竇口鼻道復合體(Ostiomeatal Complex,OMC)的變異又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以中鼻甲為中心的臨近區域結構如鉤突、篩泡、中鼻甲、中鼻道等OMC 被認為是導致CRS 主要形成因素之一[16-17]。常見鼻中隔偏曲、下鼻甲肥大、反向中甲、鉤突息肉樣變等局部解剖結構異常都可影響鼻竇腔內自我正常功能運轉,由于鼻竇腔通氣引流功能障礙,從而也加劇了低氧損傷程度和局部損傷,致使局部微環境惡化。其中,鼻中隔偏曲、鼻甲大皰、中鼻甲畸形、鼻中隔畸形等因素均可導致鼻竇解剖變異,而鼻中隔偏曲影響程度最大[18]。
2 宿主系統性因素
2.1 變態反應
以免疫球蛋白E(IgE)介導變態反應性疾病通常被認為是CRS 形成及發展的一個誘發因素。在多種變應性因素刺激下,引發一系列變態反應并伴隨多種炎癥介質的釋放,血管通透性增加,鼻腔鼻竇黏膜發生水腫,從而導致竇口鼻道復合體引流和通氣不暢,分泌物瘀滯,形成炎性反應,局部惡化,最終加重感染,導致CRS 發生[19]。
在變應性因素誘導刺激下形成的變態反應是促使CRS 的重要致病因素。變應性因素在CRS 中的陽性率在32.9%~41.34%[20],Krause[21]調查研究還發現1/3 以上的CRS 患者伴有變應性鼻炎。王鴻等[22]報道,60.4% 的CRS 中伴有不同程度的變應性癥狀和體征,其中,25.3% 的患者伴隨有變應性鼻炎,42.2% 的患者變應原皮試陽性,94.3%患者對常年性變應原呈陽性反應。據此推測變應性因素及所引發的變態反應可能與CRS 的病變程度和范圍密切相關。從變態發反應對鼻竇黏膜損傷影響機制上看,L-4 基因編碼區存在多個多態位點,其中一些多態位點與變態反應中的的超敏反應密切相關[23]。在多種變應原刺激下所引發的變態反應可激發并釋放多種炎性分泌物,使鼻腔內血管通透性增加,鼻黏膜持續水腫,阻塞竇口鼻道復合體致使鼻竇引流不暢,纖毛功能障礙,黏稠分泌物潴留,致病性微生物易滋生繁殖,最終導致CRS[24],如此反復可造成病程遷延不愈或復發。
2.2 與伴隨疾病
近年來,有學者通過對CRS 的病理學研究發現,該病的黏膜炎癥反應與哮喘等變態反應性疾病較為相近,都包含上皮細胞破壞、胞外蛋白沉積及基底膜增厚等氣道重塑的病理特征[25]。有研究顯示,21.6%變應性鼻炎患者同時伴有鼻息肉。劉亦清等[26]通過CRS 鼻黏膜組織切片中研究發現,嗜酸性粒細胞浸潤的鼻息肉組織占50.8%。據此可推測,常見伴隨疾病與CRS 鼻黏膜組織密切相關,并且是促使CRS 發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變應性鼻炎尤其是反復發作的變應性鼻炎,會加速鼻竇炎特別是鼻竇炎合并鼻息肉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可能機制為變應性素導致鼻竇竇口復合體上的鼻黏膜發生持續性腫脹,進而引起疾病病情纏綿、遷延不愈[27]。 而變應性鼻炎患者的鼻黏膜纖毛擺動頻率和纖毛清除率減弱,直接破壞了鼻竇黏膜正常的清潔功能和天然屏障系統平衡,鼻竇穩態失衡,則易發生組織重塑,從而繼發CRS[28,29]。
2.3 免疫反應
在CRS 發病過程中,免疫因素是導致其發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免疫因素包括免疫缺陷、免疫調控紊亂等,Toll 樣受體(TLRs)是目前CRS 天然免疫病因研究中最重要的模式識別受體(PRR)。TLRs 激活后,上皮細胞可能激發產生針對特殊病原體的特異性防御分子,形成TLRs 特異性傳導通路,從而導致鼻腔炎癥的發生發展。TLR 是一種跨膜受體,在大多數細胞包括呼吸道上皮細胞中都有表達,TLRs 及其傳導通路在CRS 鼻息肉組織中表達異常,在天然免疫在CRS 發病中發揮一定的作用。王鑫等[30]通過Toll 樣受體信號傳導通路基因芯片檢測技術,得出CRS 鼻息肉組織中表達上調基因,其中TLR9 經驗證在CRSwNP 中明顯高于對照組,這可能與中國人鼻息肉組織中以Thl 炎癥類型相關。
3 討論
綜上所述,在長期各種病理性因素刺激下,鼻竇可出現一系列炎性反應,并導致鼻竇腔炎性分泌物增多,鼻竇口阻塞,最終導致鼻竇黏膜損傷,鼻竇結構破壞,易誘發CRS,并易使鼻竇內形成惡性循環,加重病情。CRS 病因病機復雜,目前還未完全明確,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對CRS 的認識深入,從各個角度及整體上加深對CRS 的認識和了解,會對CRS 的臨床診治具有更強的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