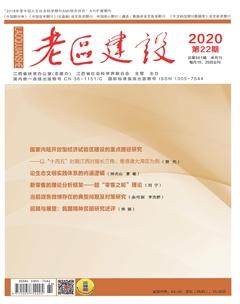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網絡輿論失序的表現、成因及應對
2020-12-28 03:02:02劉開源
老區建設
2020年22期
[提 要]隨著互聯網和新媒介的日臻成熟,形成廣袤的網絡傳播空間。人們在網絡空間中,表達思想、溝通觀點和宣泄情緒。網絡社會中多元利益訴求交織、多元價值取向雜糅的情緒,正悄然改變人們的認知方式、價值觀念以及行為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構并建構當下網絡空間的秩序形成,對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產生重要影響。網絡輿論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借助媒介技術的傳播對公眾認知的社會現狀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當前的網絡輿論傳播現狀在現實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與挑戰。通過立足于傳播主體、利益訴求和價值信仰等多個維度,意圖厘清當前網絡空間中輿論的生成、走向等脈絡,從而提出網絡空間中各個輿論主體通過意義共享、構建多元共識、話語突圍等途徑實現網絡空間的理性對話。
[關鍵詞]網絡輿論;價值信仰;利益訴求;理性對話
[作者簡介]劉開源(1976—),男,江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
塞繆爾·亨廷頓曾做過一個重要論斷,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1]。正是由于新媒介使用的日益普及,憑依網絡技術構建出的網絡社會,輿論表達的場域也由日常現實延伸到網絡社會,使得互聯網成為公眾輿論表達的重要場域。媒介技術的發展,同時帶來了信息傳播模式的變革和信息傳播生態的變遷。
互聯網與移動傳播網路構成中國新型的社會關系和組織形態的建設基礎[2]。……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