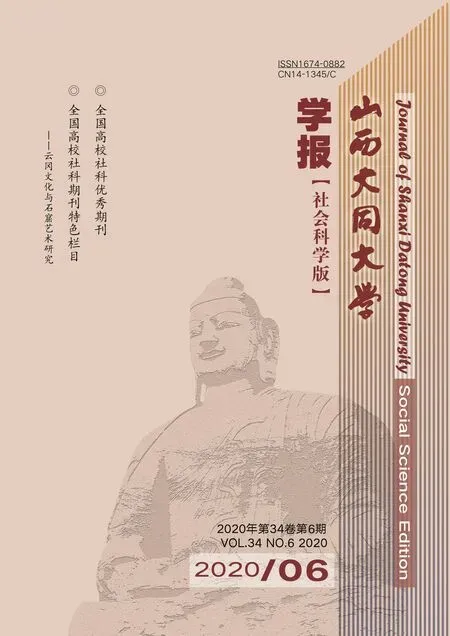城市中小學生新媒介素養對其網絡參與的影響
郭旭魁,馬 萍
(1.長治學院中文系,山西 長治 046011;2.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甘肅 蘭州 730020)
伴隨手機、Ipad 等新興媒介的普及,使用者日益呈現低齡化趨勢。據CNNIC 第44 次統計報告顯示,全國網民職業結構中居首位的是學生,占26.0%;年齡區間在10-19 歲的網民,達20.9%。[1]2013 年廣州市在全國率先推出《媒介素養》的專門教材,并在當年列入全省小學生媒介素養課程目錄。目前,城市中小學已經普遍開設了信息技術等方面的課程。這些媒介素養教育的效果如何?是否促進了城市中小學生參與新媒介實踐?這是本研究關注的問題。
一、文獻綜述
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指出,媒介素養是社會成員使用和解讀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識、技巧和能力。[2](P36)根據美國媒介素養領袖會議的定義,媒介素養包括公眾接近、分析和評價各種媒介信息的能力。波特則將這種媒介素養的核心概括為個人在媒介接觸中“取得控制權”。[3](P8)與此觀點相似,卜衛將媒介素養的核心理解為“使用媒介的能力”。[4]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個體媒體使用與媒介素養教育的關系:個體的媒介技能、個體對媒介的知識以及個體對媒介內容的批判性理解。
在個體的媒介使用方面,李金城等對大學生調查研究發現,數字媒介的使用技能對提升大學生的媒介素養有積極作用。[5]“知溝假說”也指出,媒介使用技能(Basic skills)與媒介使用之間聯系密切。[6](P218)
本文主要探討城市中小學生的媒介素養,筆者提出如下假設1:
H1:新媒介使用技能對城市中小學生網絡參與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
個體對媒體的知識,是指個體對媒體組織的生產運作機制的認識和理解方面的知識,也是考察媒介素養的重要內容。周葆華等通過對“超級女聲”節目的問卷調查,發現公眾在媒介知識方面的媒介素養“僅處于及格水平”,令人堪憂。[7]李春雷等通過對“烏坎事件”中的微博主研究發現,博主對微博新媒介的了解程度與媒介參與之間有密切關系。[8]城市中小學生掌握新媒介性質的知識程度是否對其新媒介參與存在積極影響?據此筆者提出假設2:
H2:擁有新媒介性質方面的知識對城市中小學網絡參與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
在個體對媒介內容的批判性方面,一些研究者借鑒德國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模式,認為在中國培養媒介使用的“批判型受眾”具有明顯的迫切性。[9]萬曉紅等對湖北高校大學生社交新媒體使用調查發現,大學生雖然對社交媒體使用率高,但看待問題視角狹窄,缺乏批判性的獨立思考。換言之,大學生在新媒介內容的評判方面的媒介素養較低。[10]目前針對批判性媒介素養教育主要集中在大學生群體,本文試圖延伸和檢驗城市中小學生群體。因此,我們提出假設3:
H3:新媒介內容的評價對城市中小學網絡參與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
二、研究設計與調查實施
(一)研究設計因變量:新媒介參與。新媒介參與程度設置了5 個題項:“我利用網絡搜索工具,主動獲取想要的信息”,“我在網絡上發表對熱點時事新聞的看法”,“我在網絡上發布個人狀態、照片等”,“我在網絡上制作短視頻”,“我在網絡上學習課程知識方面的內容”等,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從“完全不參與”到“總是參與”,分別賦值1-5。
自變量:分別為新媒介使用技能、新媒介性質的知識程度、新媒介內容的評價程度。
新媒介使用技能設置了7 個題項:“對手機上網技能”,“對微博、微信等使用技能”,“對網絡游戲”,“對網絡圖片、音樂、影視劇等下載技能”,“對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制作技能”,“對網絡購物技能”,“對網絡中檢索信息與學習技能”等,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從“非常不熟悉”到“非常熟悉”,分別賦值1-5。
新媒介性質的知識程度,設置了4 個題項:“我認為不同網站對同一事情的呈現會有不同”;“網絡產品是營利性的,所以網絡傳播的信息都具有目的性”;“微信朋友圈中的內容都是真實的,完全可以相信”;“我能清楚分辨報紙、電視與網絡的優缺點”等。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從“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別賦值1-5。
新媒介內容的評價程度,設置了4 個題項:“我認為點擊率高的網站,其內容質量也越好”;“我對網絡暴力內容有清楚的認識”;“我能正確理解網絡中的內容,并淘汰不重要的內容”,“我對網絡謠言等不實信息能夠很容易識別”等。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從“堅決反對”到“完全同意”,分別賦值1-5。
控制變量:性別、年級、上網頻率、家庭經濟狀況、學習成績、開展媒介素養課程情況。控制變量在以往研究中探討得比較多,但不作為本次研究的主要內容。
性別:男為1,女為2。
學段:小學、初中、高中。
上網頻率:“每天上網的頻率情況”,從“基本不上”到“總是在上”,賦值1-5。
家庭經濟狀況分為3 種類型:低于當地平均水平,與當地平均水平差不多,高于當地平均水平;學習成績分為3 個等級:班級前面、班級中間、班級靠后。
媒介素養教育,主要是通過詢問“學校是否開展‘信息技術’等方面的課程”。
通過對問卷信度和效度檢驗,信度方面Cronbach’s Alpha 值為0.717;效度方面KMO 值為0.718,總體上信度和效度良好。
(二)調查實施本次研究的調查范圍主要是山西省的城市中小學,采用實地發放問卷的形式。調查實施中運用非概率抽樣和分層抽樣的方法。在全省范圍抽取3 個地級市:晉中、長治和運城,在每個地級市中選取3 所不同的學校,即小學、初中和高中,一共抽取了9 所學校。然后在每所學校的每個年級中各選取1 個班級,每個班級選取20 個樣本(小學選取30 個),總樣本有540 個。發放問卷540 份,回收且有效問卷449 個,問卷有效率83.1%。本研究統計運用SPSS22.0 軟件進行。
三、結果呈現
在449 個有效樣本中,男女性別分別占總體的53%和47%。學段分布情況:小學段、初中段和高中段,各占總體的17.8%、45.0%和37.2%。“在自由支配時間中,第一選擇會做的事情”,排在第一位的是“上網”。說明城市中小學生,在閑暇生活中對網絡的使用程度較高。
(一)媒介技能方面此次調查主要涉及上述新媒介使用中的“手機上網技能”等7 項內容,均值最大為4.00,是“手機上網技能”;最小為2.99,是“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制作技能”。說明城市中小學生對新媒介技術技能總體上熟練程度較高。

表1 城市中小學生新媒介參與多元線性回歸
在控制變量前提下,實施逐層回歸統計分析,見表1。從中可以看出,在模型2 下,新媒介使用技能(p<0.05,β=0.362)對城市中小學生新媒介參與呈現出統計上的顯著性,而且是正向關系,H1 假設得到驗證。說明城市中小學生的新媒介使用技能越高,其參與新媒介的積極性越高。
(二)新媒介的知識方面
在有關新媒介性質的知識方面,考察城市中小學生對新媒介組織性質、信息生產及消費等方面的知識了解程度。通過對4 個題項均值比較(表2),發現在李克特量五級表中4 項得分都比較高(第4項為負分題,即得分越低說明對新媒介知識越正確)。說明城市中小學生對新媒介方面的知識程度較高。在控制變量的前提下,在表2 的模型2 中,新媒介知識程度與新媒介參與之間的統計不顯著(p<0.05,β=0.030),H2 假設沒有得到證明。由此看出,雖然擁有對新媒介性質的正確認識,但并不能有效促進城市中小學生積極參與新媒介傳播實踐。

表2:城市中小學對新媒介的知識程度各項均值
(三)對新媒介內容評價方面
考察城市中小學生在新媒介內容評價方面的表現與其新媒介參與之間的關系,屬于傳統媒介素養教育“文本理解”的范疇。在對新媒介內容李克特五級量表的評價中,除第一項得分較低外(為2.5746),其余相對較高(在3.2532 以上)。在表2 模型2 中,發現城市中小學生對新媒介內容的評價與其新媒介參與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p<0.05,β=0.097)。換言之,對新媒介內容評價越積極,其越能夠積極參與新媒介。由此,H3 假設得到驗證。
四、研究結論與討論
首先,媒介素養的提升并不必然促進城市中小學生參與新媒介傳播實踐。媒介素養教育是一項傳播實踐性很強的工作,意在指導公眾更好地參與各類媒體傳播。因此,以往研究中一個潛在的主題就是,媒介素養高,則媒介參與程度也會高。本次研究發現,新媒介的使用技能和新媒介內容的評價對城市中小學生新媒介參與存在顯著影響,而新媒介知識方面的素養的影響則不顯著。換言之,新媒介素養方面的提升,并不一定促進城市中小學生在網絡上積極表達觀點。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復雜,如學校課業較多、升學壓力較大以及家庭監管等方面,都可能對新媒介參與產生重要影響。
其次,在城市中小學生媒介素養教育中,學校教育比較顯著,但家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在表1 的模型1 中,可以看出學校的“信息技術”(p<0.05,β=0.361)方面的課程,有力地促進了城市中小學生的新媒介參與。因此,推動學校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新媒介素養教育體系中,家庭的作用也非常關鍵。本次調研中主要涉及“家庭經濟狀況”(p<0.05,β=0.103),對城市中小學的新媒介參與產生了積極作用。“知識鴻溝”假設中的經濟狀況因素再次得到證明。筆者主張,一方面繼續消除貧富差異對城市中小學生新媒介參與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要破除媒介素養教育責在學校的固定思維,建立家校有機聯動的媒介素養教育體系。
最后,從個體發展角度來看,媒介素養教育與新媒介參與程度是一個逐步提升的過程。從表1 的模型1 中,可以看出學段越高的學生,在新媒介參與中越積極(p<0.05,β=0.181)。從個體認知能力發展過程來看,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分析事件發生的原因、解釋教師的反饋、從行為結果中推測穩定特質等能力不斷提高。[11](P354)這種學習能力自然也會遷移到新媒介的傳播實踐中。因此,城市中學小生的新媒介素養教育,要根據不同學段的學生認知特點,制定相應的媒介素養教育內容,實施針對性訓練。
另外,囿于客觀條件,本研究采取非概率性抽樣方法,在由樣本推及總體時需要謹慎。本次調查主要關注城市中小學生的媒介素養教育對其新媒介參與的影響,在設計問卷中側重學校媒介素養教育的情況,相對地忽視考察家庭在媒介素養教育方面的作用。這些不足有待后來者進一步研究。
由大眾傳播時代進入社交媒體時代,新媒介對青少年社會化的影響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現象。目前對青少年媒介素養的研究側重于媒介接觸的現象描述,較少在關系層面的探討。
本文從媒介素養的三個維度研究新媒介素養與網絡參與的影響。結論是,新媒介技能、新媒介內容理解對城市中小學生的網絡參與有顯著影響,而新媒體知識的影響不顯著。新媒介素養的提升并不必然帶來積極的網絡參與。新媒介素養教育既需要學校和家庭的共同作用,也要尊重青少年個體心理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