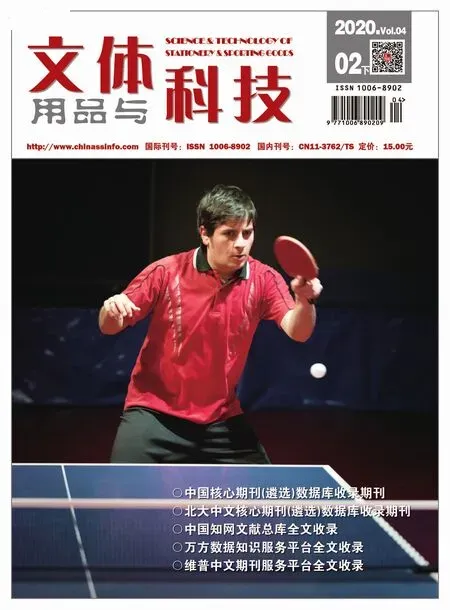高校高水平運動員學訓融合的路徑研究
(南京理工大學 江蘇 南京 210094)
前言
2016年的里約奧運會,美國、英國體育運動隊名列金牌榜一、二名,通過分析運動員來源結構情況發現,美、英代表隊約有70%以上運動員來自于大學,例如美國運動員總數為555名,其中約有470名來自大學。我國當前也在研究在普通高校中培養高水平運動員,補充單一“舉國體制”的運動員培養模式,這其中最突出的現存問題就是“學訓矛盾”。因此,當前應深入探索“學訓融合”的改革路徑,高校高水平運動員在在體育競技與文化素質兩方面綜合發展,作為運動員能出成績,畢業后能夠利用自身專業和體育技能實現就業,回報社會。
1、我國高校高水平運動員學訓融合發展概述
1.1、我國高校學訓融合發展歷程
我國自1987年開始在全國建立了51所高水平運動員試點高校,至2018年已擴展至235所,并在2001年頒布的《2001-2010年體育改革與發展綱要》中確定了高校高水平運動員“學訓融合”的路徑設計,迄今已有30多年歷史。在里約奧運會后,2017教育部頒布了 《關于進一步加強普通高校高水平運動隊建設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指出高校高水平運動員學訓融合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引領學校體育課余訓練和競賽發展,為國家培養全面發展的高水平體育人才,完成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及國際、國內重大體育比賽任務”,可見高校學訓融合培養高水平運動員是當前體改的大趨勢。
1.2、當前高校學訓融合的現狀
為響應國家號召,許多高校都都招收一批高水平運動員,代表高校參加職業比賽、大運會甚至奧運會賽事,例如清華大學的皮劃艇項目在國際上處于高水平行列,就是在“學訓融合”制度下培育出一批高水平運動員。這些運動員在畢業后即擁有專業知識,又擁有體育經驗,為體育事業繼續發揮貢獻。
2006年“學訓融合”還處于體育訓練與文化課教育相結合的研究探索途中,到了2016年里約奧運會前后,學訓融合處于體育部門與教育部門的雙重管理之下,與美國、英國相比,兩部門分別管理與的效率不及美英的“共同培養”體系。
2、我國高校學訓融合模式
2.1、教育系統獨立運行模式
此種模式的考生屬于高考報名后統招,根據體育成績和運動等級制定錄取分數線,這些高水平運動員學科專業由高校單獨限定,學生訓練方面依托高校自身教學資源和專職教練,即培養體育生的“學生運動員”的模式。但教育系統自與體育系統的訓練水平差異較大,系統性不強,高水平運動員入學后的競技能力提高有限,或者停滯、后退,無法勝任,也導致高校的體育競賽體制無法滿足運動員的發展。無法達到參與國內外重大賽事的成績要求,學習的提升也十分有限。
2.2、聯合培養現役運動員
此種模式系體育部門與教育部門聯合制定單獨招生辦法,由高校,各高校體育學院、專業體育高校負責招生培養。這種模式下運動員仍以體育為主,訓練方面仍由體育部門負責,即所謂培養“運動員學生”,高校負責學生的學習方面。“運動員學生”由于有體育部門安排的比賽任務,以及很高的訓練強度,與高校正常的課程安排沖突較多,正常的專業學習難以落實。從總體情況來看,此種“學訓融合”實則成了體育部門與教育部門“雙軌制”,融合型態不完全。
2.3、組建特色項目運動隊模式
此種模式以高校依靠自身力量通過特招方式組建優勢項目運動隊,教育系統和體育系統聯辦的一種組織方式,“省隊校辦”模式即屬于此種模式下的一種探索,例如清華大學皮劃艇專業,屬于高校優勢項目系科單獨招生,運動員的來源渠道比較廣泛。也有高校自行組建業余運動隊的模式,從各個系科招收高運動水平的學生參加本校優勢項目運動隊,運動員在不影響本專業正常學習的情況下,訓練方面采取統一集訓的方式,這種制度下學生在本專業和體育技能方面都能夠有所發展,畢業就業也有一定的優勢。
3、高校高水平運動員學訓融合發展困境
3.1、訓練方面
當前學訓融合模式高校招收的高水平運動員多數是以特招加分、保送免試等方式招生為主,渠道比較單一,運動員的年齡、運動技術等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往往通過高強度訓練也難以提升,屬于業余選手、專職教練的訓練模式,運動訓練的課程設置比重與文化課程設置相比比例平均,實際上身份既更貼近“學生”,在訓練時間、訓練條件方面與專業運動員相比不容易保障,與體育系統的合作深度也十分有限,尤其是一些特色項目只能依托高校資源,“學生運動員”在個人身份界定方面難以向“運動員學生”方向轉變。
3.2、課程設置方面
高校針對高水平運動員的課程設置方面不夠專精,主要原因是高水平運動員對訓練時間和參加賽事的客觀需求,與文化學習有沖突,接受文化教育有一定困難。從實際情況來看,高水平運動員在這種環境下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全面、不持續,學訓融合在各高校中基本還是“以訓為主”,課程設置上更偏向于專業課,文化課退化至輔助地位,教學質量得不到保障。例如針對體育生的大學英語的學習難度完全達不到英語科目實際應用的需求,而且只象征性地開設2年。導致許多運動員訓練與學習脫軌,無法保證發展自身的文化素養,學訓融合的實際目標實現起來比較困難。
3.3、體系方面
當前無論是“學生運動員”還是“運動員學生”,都反映出當前教育和體育兩套體系難以融合的現狀,學訓融合的實質是兩種體系的融合,如果拆分成教育、體育兩方面的培養目標,仍然屬于各行其道,運動員找不到自身的合理定位。以普遍現象為例,在教育系統培育的“學生運動員”層面,普遍存在重引進掛名、引進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等現象,在學訓融合后為運動員文化素質提升有限,畢業后也很少能夠勝任專業工作崗位;在體育系統系統培育的“運動員學生”層面,訓練、生活都不依托高校,只是掛上了“學訓融合”的名義取得高校文憑,實則學訓分離,未能達到學訓融合的真實目標。
3.4、教練員方面
當前我國高校學訓融合傾向于招收高水平的教練員,或者招收退役的優秀運動員,再或者由本校畢業的高水平運動員擔任教練員,上述三類教練員都受限于整體文化水平,對于設計訓練計劃、更新訓練理念、體育研究能力等貢獻有限,限制了新招收的運動員技術水平提升空間。
4、高校高水平運動員學訓融合解決路徑的對策研究
4.1、基于招生根源的解決路徑
當前高校運動員學訓融合的解決問題手段比較有限,例如擴大招生范圍、選聘更優秀的教練員、優化課程設置等等,都是對當前學訓融合表面問題的小修小補,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學訓分離的本質問題,運動員仍然難以真正意義上接受高校文化教育。當前學訓融合模式的核心是體育,但體育系統與教育系統的合作模式仍然沒有突破“金牌至上”的唯成績論,違背了學訓融合的教育目標,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學訓矛盾。基于此,應從教育系統與體育系統雙方合作,從高校教育的根源上進行配合,將特長生從高校入校前的小學階段開始培養,在教育資源方面準備充分,經過九年針對性文體培養后招收入高校,使高水平運動員在義務教育階段打下良好的文化素質基礎。
4.2、基于教練員的解決路徑
鑒于教練員層面文化素質缺失的現實情況,高校可以考慮加大對教練員進行培訓,例如在職碩士課程、繼續教育等,使教練員在當前崗位上繼續融入高校的教育環境,增強教練員的文化素質和專業素質,并使自身的體育研究學術能力得到發展,在培育運動員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方面有所創新,有能力挖掘運動員的潛力,成為高校培育的科研型的教練人才。
4.3、基于課程設置的解決路徑
從課程設置考慮出發,學校應適當加強運動員應用文化課程的安排,例如計算機應用技術、英語等文化基礎課程應增加一定課時。在當今信息化社會中,計算機應用技術和英語是影響高水平運動員繼續深造的基本科目,也是運動員適應現代社會的必要基本技術。加強實用技術的文化學習,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高水平運動員畢業、退役后的就業問題,夯實我國體育人才培養的基本保障。所以,深化學訓融合改革首先應從課程設置中篩選出與運動員自身發展息息相關的基礎科目,使其與運動員的實際發展需求相適應,有助于他們適應激烈的社會競爭。
4.4、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解決路徑
里約奧運會上,美國和英國取得優異成績的原因就是高校體育為培養競技人才發揮了巨大作用,我國依靠”舉國體制“難以建立長期的競技優勢,因此應該借鑒美、英等國的高水平體育人才培養模式,變單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為多元化培養模式,使體育人才的培養逐漸打破“學生運動員”或者“運動員學生”之間的學訓界限,使運動員在文化水平和運動水平兩個方面共同發展,避免專業運動水平高、文化水平低的畸形發展狀態。基于此,高校應對高水平運動員的學業完成情況高度重視,在優化過后的基本課程設置必須完成方準許畢業,如因參賽等原因不能完成學業或按時參加考試,可以考慮延期畢業,使運動員連續、全面地接受高校文化素質教育,并能夠在畢業后應用所學文化專業課程為社會服務,以全面內化的文體素質回饋高校教育。
5、結語
“學訓融合”是我國體育改革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它符合國際化趨勢和人才培養規律,避免出現運動員缺失教育水平、技能單一的不合理現象。應通過探索學訓融合的新路徑打破運動員和學生的界限,使運動員與學生雙重身份融合,并且在文體素養方面都有質的發展,使競技體育事業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