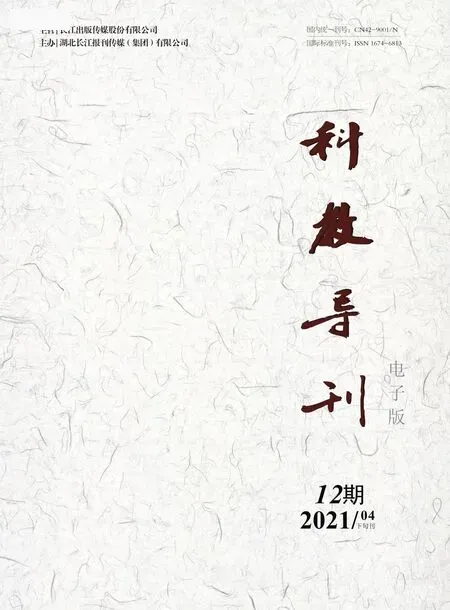高等教育的“兩個規律”與“適應論”論戰
馮子然
(上海師范大學 上海 200234)
1 高等教育“兩個規律”提出的背景及內涵
潘懋元先生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創始人,他在20世紀50年代第一個提出要建立專門的高等教育學科,并在建立高等教育學科方面進行了首次探索。20年后,他再度倡導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在他的建議下,中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廈門大學高等學校教育研究室成立。1980年11月8日至20日,潘先生應一機部教育局之邀,到湖南大學為一機部所屬院校領導干部教育科學研究班作了題為“高等教育學及教育規律的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學說,該學說為《高等教育學》的編寫奠定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四年后,由潘懋元先生主導編寫出版了中國第一部《高等教育學》,該著作的出版成為了高等教育學科建立的標志。
從全書的內容看,書中的許多理論和觀點正是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理論和高等教育特點論的指導下形成的。高等教育的“兩個規律”是高等教育的外部規律和內部規律。外部規律,也稱教育同社會關系的規律,指的是教育作為社會的一個子系統與整個社會系統的其他子系統——主要是政治、經濟、文化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規律。這條規律被表述為:“社會主義教育必須通過培養全面發展的認為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服務。”教育外部關系規律的依據是教育的本質,它是教育的本質的體現。在《高等教育學講座》中,外部規律得到了更加全面系統的闡述,外部規律的含義和表述均得到了進一步的提煉和豐富。教育的外部規律是指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等的關系。這條規律的主要含義就是“教育必須與社會發展相適應”,也就是“社會主義教育必須與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相適應”。
而內部規律,或叫教育自身的規律,指的是教育作為一個系統,它內部各個因素或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規律。它被表述為:“社會主義教育必須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或者“社會主義教育必須通過德育、智育、體育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教育內部規律就是教育方針所包含的教育目的的內容。
“內外部關系規律”學說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確立教育主體地位。把教育作為一種主體,就是要重視教育群體的內在聲音。同時,兩條基本教育規律也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教育的外部規律制約著教育的內部規律,教育的外部規律必須通過教育的內部規律來實現。教育的外部規律和教育的內部規律是相互起作用的,缺一不可,也不可分割。
2 高等教育“適應論”的分歧與論戰
2.1 高等教育適應性與“兩個規律”的關系
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及高等教育的特征來看,現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點分為九點,“適應性”就是其中一點。“適應性”原本為生物學概念,它指的是有機體與周圍環境相適應的一種特性,這是一個有機體能夠存在的前提,否則該有機體就面臨滅亡或絕種的危險。達爾文的進化論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所以,有機體的適應性已被人們普遍接受。在教育學界,人們普遍接受“適應性”這一基本觀點,人們也把教育看成一個有機系統,處于與周圍環境或其他社會系統不斷地適應過程中,人們一般相信教育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系統,因此必須與周圍環境進行物質的、信息的和能量的交換,這樣才能維持教育作為一個有機系統的運轉。這正是系統論給人們闡述的基本原理。
高等教育的“適應性”,即潘懋元先生所提出的外部規律:“教育必須與社會發展相適應”。這里的適應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所制約,并為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服務。教育主要受到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社會制度、文化傳統三個因素影響。同時,潘懋元先生在總結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過程中,也提出教育受要三方面的制約,并為三方面服務。一是教育受政治制約并為政治服務。二是教育受經濟發展制約并為經濟服務。三是教育受科學文化發展制約并為科學文化服務。可以說,“適應論”是由教育的外部規律所引申出來的,即現代高等教育要適應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適應世界高新科技發展的需要,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需要,適應社會對各類人才培養的需要,這不僅是我國特有的現象,而適應于各國的高等教育。
2.2 關于“適應論”的論戰
《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年第一期上發表了北京大學兩位教授展立新和陳學飛的長篇文章《理性的視角:走出髙等教育“適應論”的歷史誤區》。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否定潘懋元關于高等教育“兩個規律”的理論,否定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需求的“適應論”,作者認為,“高等教育適應論是一種無奈的歷史選擇”,導致兩大失誤:一是“顛倒了認知理性與各種實踐理性的關系,使國內高等教育難于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二是“不惜壓制其他實踐理性的發展,以至于在髙等教育的各種目標之間、不同的目標之間與手段之間,造成了極大的矛盾和沖突”。因此“突破與超越適應論,是現階段我國髙等教育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該文章在竭力否定和貶低高等教育“兩個規律”理論和“適應論”的同時,鼎力推崇和提倡所謂的“認知理性”,認為高等教育要擺脫“適應論”的思想束縛必須“回歸認知理性,建設完善的學術市場”,認為“髙等教育本質上是發展認知理性的事業”、“高等教育追求的核心目標應該是認知理性的發展”。
而楊德廣教授認為,高等教育的“適應論”是經濟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必然,是高等教育生存和發展的必然,潘懋元提出的“兩個規律論”即外部關系規律和內部關系規律,是“適應論”的理論基礎,是符合實際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的,對推動經濟社會和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對此,他撰寫了文章《高等教育適應論是歷史的誤區嗎?——與展立新、陳學飛教授商榷》,刊登在《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年第3期上,對展陳的觀點進行一個反駁。楊認為,該文用哲學上的一個普通概念“認知理性”來否定和取代高等教育“適應論”和“兩個規律”論,甚至將其提高到是高等教育的“本質”和“核心”是不適當的。觀點中片面地提倡為學術而學術的“理性的視角”,是脫離現實、不顧現實社會的需求,是思想的倒退,歷史的倒退,是一種退縮到“象牙塔”里的企圖。對此,本文指出,潘愗元的“兩個規律”論是符合教育實踐和客觀現實的,并非由展、陳提出的“認知理性”所取代。
不久后,展立新、陳學飛又發表了新作《哲學的視角:高等教育適應論的四重誤讀和誤構——兼答楊德廣商榷文》,點名與楊德廣教授商榷“適應論”。該文翻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引用了從馬、恩、列到涂爾干、舒爾茨等人的觀點,進一步否定高等教育“適應論”,認為高等教育機構實質上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建設健全學術共同體精神,是高等教育事業健康發展、長盛不衰的根本保障。展、陳在文章中鮮明地提出:高等教育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的基本關系并不是“適應”與“被適應”的關系,而是批判反思主體和批判反思對象的關系。因此,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務不是迎合政治權力和“當權者”的需要,而是要自覺把政策、權力、當權者等,都當作批判反思的對象。
對此,楊德廣教授認為其中的有些評判過于斷章取義,有些觀點甚至是錯誤和片面的。他認為,“學術共同體”僅適用于一些研究性大學而不適用于應用型、專業型大學,展、陳只片面的考慮大學的學術研究功能,而忽略了大學生的實踐性、現實性和技能性。其次,展、陳強調了大學的“批判性”問題,而大學生不能只為了“批判”而“批判”,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大學的批判性是建立在維護國家利益的、人民利益的基礎上,因此并不存在對立。另外,關于大學與社會“適應”與“被適應”的問題,楊教授指出幾個例子,中世紀的大學為教會服務,美國現代大學為社會服務,威斯康星大學提出社會服務職能,說明大學的“適應性”是客觀存在的,并沒有存在大學必須為當權者和政治服務的關系。綜上所述,潘懋元提出的高等教育適應論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客觀現實的,大學如果一味地強調學術功能,不接地氣,不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所發展,那么很容易被社會淘汰。楊德廣教授還結合學界上其他學者提出的“適應論是受特定年代計劃經濟和傳統理論模式的產物的”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時代,高等教育不僅要適應社會發展,更要主動去適應。由于教育的滯后性,高校要發展更是需要去“超越”,如果把“走出高等教育適應論”誤以為不要適應,注定是走不通的。
3 結語
總體而言,高等教育“適應論”能夠較好地處理好知識與個人及知識與社會的關系,因為它首先把社會發展需求放在第一位,其意義就是把社會視為一個整體的存在,高等教育僅僅是社會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不能封閉起來推行自我中心主義。同時高等教育必須尊重人的發展要求,因為人不僅是社會的基本構成,也是社會價值的歸宿,換言之,沒有人就沒有一切。這正是教育內外部規律的內涵。但兩個規律學說對知識獨立價值論述偏少,常常給人一種忽視知識、忽視髙等教育本體的印象。這也正是“理性視角”批判的重點。
世界各國的大學從一個功能發展到兩個功能,再發展到三個功能,這就是主動適應社會的必然結果。因此,并非像展、陳所說,“高等教育‘適應論’是我國所特有的一種社會需求角度闡述和論證高等教育問題的理論”。事實上,“適應論”適合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高等學校為了更好地為社會服務,應建立教育產業、發展教育市場。這是大學為社會服務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