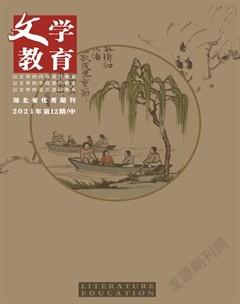時間、空間、受眾坐標中的狐形象研究
趙寧
內容摘要:在縱向的中國歷史時間范疇中,“狐”形象經歷了從“圖騰祥瑞”到“妖化”到“神化”再到“人化”的演變;從縱向時間范疇擴展到橫向的空間范疇,許多國家都有關于“狐”的文學和藝術作品;而以成人為受眾的“狐”和以兒童為受眾的“狐”也帶著局限和差異。本文將“狐”形象置于“時間”、“空間”和“受眾”三個坐標軸之中展開立體式研究,引出當前“狐”形象的特征分析:多元和娛樂。
關鍵詞:“狐”形象 時間 空間 受眾
在古今中外“狐”有多受偏愛呢?“狐”出現在民間傳說,也出現在文學作品;有漢畫形象,也有卡通動漫;你能在博物館看到抽象聚義的“狐”形象圖騰,也能在現代化城市的街頭巷尾看到形態各異的“狐”形象LOGO。
在中國文學作品領域,自先秦古籍《山海經》,到以《搜神記》為代表的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到以《青瑣高議》為代表的宋代傳奇小說,到以《聊齋志異》為代表的清代文言短篇小說,再到前兩年大熱影視劇“三生三世”系列,“狐”形象橫貫古今。對于“狐”形象的研究在空間范圍上從東亞到歐洲再到美洲,“狐”形象遍布世界。
一.時間軸:在中國文化中變遷的“狐”
在中國古代“狐”形象的研究主要依據于民間傳說和文獻典籍,廣為人知的含“狐”故事有《山海經》《搜神記》《抱樸子》《太平廣記》《宣室志》《西游記》《封神演義》《聊齋志異》《夜譚隨錄》《閱微草堂筆記》等,還有一些有少量記載,如東漢趙曄所撰《吳越春秋·禹與涂山氏》、曹丕的《劉異傳》、三國時陸璣作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沈既濟的《任氏傳》、郭璞的《玄中記》、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牛僧孺的《玄怪錄》、和邦額的《夜譚隨錄》以及劉斧的《青瑣高議》等。
1.“狐”形象的三次轉折
梳理中國古代“狐”形象參武錯綜的研究發現,“狐”形象共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轉折。先秦時期的“狐”是祥瑞的象征,第一次轉折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狐”獲得幻化為人的神力,人們依據人的容姿和精神來塑造“狐妖”,《玄中記》:“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這是“狐”化人的開端。“狐”的妖化在東漢已有跡可循,東漢許慎的《說文》和后漢黃憲的《三難》均有所論述,至魏晉時期“狐妖”之說更為成熟;第二次轉折在入唐之后,《朝野僉載》:“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狐”從被排斥的妖異轉化為能支配人類禍福的神靈;狐神信仰在明清時期受到日益增長的理性主義精神的挑戰,立足于審美立場的文人促進了“狐”故事的發展,故事里的“狐”被納入人的價值體系之內,徹底“人化”,也標志著“狐”形象的第三次轉折。
2.“狐”形象的變因探析
是什么導致了“狐”形象的流變?離不開社會發展中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綜合影響,不同時期的“狐”形象影響因素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狐”的神化形象一則源于早期人們應對自然和改變自然的能力處于被動狀態,人被自然所縛,對自然飽有神秘感、恐懼感和敬畏感,為了尋求自然的庇護,“萬物有靈”論盛行,“狐”逐漸被神化;再則神化“狐貍”符合儒家的“天人感應”觀,迎合了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到了兩漢時期,政治鞏固,經濟繁榮,伴隨農業定型和農用器械的改造,人與自然的融合更加密切,自然剝離了神秘的外衣,“狐”走下神壇成為必然。魏晉時期儒學衰微,玄學興起,民間巫術盛行,道教和佛教為爭取信眾編造神怪故事,“萬物成妖”的風頭蓋過了“萬物有靈”。加之社會動蕩不安,朝代更迭頻繁,百姓流離失所,鬼神理所當然地成為禍亂人間的罪魁禍首,誠如魯迅曾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所說:“可見六朝人視一切東西,都可成妖怪”。唐代是小說發展的轉型期,魯迅先生說“小說至唐代一變……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渲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是始有意為小說。”胡應麟也說“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唐代小說情節加長,故事曲折,注重角色塑造,有更多的筆墨描寫“狐”的擬人化特征。明清時期“狐”形象的人格特征趨于完整的原因是都市發展,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經濟社會出現了世俗化的進程。在思想上,日益增長的理性主義精神挑戰著“狐神”、“狐妖”、“狐仙”形象的真實性,人們開始以審美觀點來處理“狐”信仰及傳說,因而促進了“狐”故事的發展。文人不僅用“狐”形象來補償男性的自尊需求和情感需求,也用“狐”形象來撻伐封建落后的政治文化體制。
“狐”形象的三次轉折是一個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動所促進的連續運動過程①。在這一過程中,“人”是決定因素,傳者和受眾的意識覺醒和關系博弈成為影響“狐”形象轉折的重要一環。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中概括:“魏晉南北朝三百年學術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個人自我之覺醒。”受眾個人意識的普遍覺醒,為“狐妖”故事產生和傳播提供可能的空間;受眾理性主義的普遍發展才能合力撬動“狐神”故事的可信度,使文人以審美地立場創作“狐”故事,以期實現傳播的教化功能。
二.空間軸:在對比研究中鮮活的“狐”
1.被偏愛的“狐”
“狐”不止在中國的文學、藝術和民間傳說中大放異彩,在世界范圍都可見“狐”的身影。例如古希臘的《伊索寓言》中《狐貍與山羊》《狐貍與猴子》《狐貍與狗》《寒鴉與狐貍》等,不同的“狐”形象反映了人類的不同行為舉止和性格特征;法國拉封丹寓言中《狐貍與烏鴉》、《狐貍與公雞》等,用“狐”類比狡詐的人;英國作家羅爾德·達爾的《了不起的狐貍爸爸》刻畫了一位幽默機智、樂觀勇敢的父親形象;美國電影《瘋狂動物城》中狡猾卻又善良的赤狐尼克;韓國的“狐”形象主要圍繞九尾狐展開,例如《九尾狐》、《九尾狐外傳》、《傳說中的故鄉》之《九尾狐》、《九尾狐姐姐傳》、《我的女友是九尾狐》、《九家之書》、《九尾狐傳》等等。日本的“狐”形象比較多元,有稻荷信仰中的“狐”,有宮澤賢治和新美南吉童話中“狐”,還有日本動漫作品中的“狐”。
2.偏愛之由
為什么偏愛“狐”?首先源于藝術創作的需求,一則將異類進行藝術加工具有形式上的美感和內容上的沖擊,再則受制于歷史環境的制約,借“狐”比人,可以側面表達作者的思想。其次源于“狐”的生活習性、性格特征和外貌氣質,不同于傳說中的“龍”、“麒麟”等祥瑞,“狐”經常闖入人類生活,逐漸拉近了人狐的空間距離和心理距離,高艷霞就說“古希臘人長期與狐貍共同生活,因此能夠深刻了解狐貍機智、狡猾及冷靜的特點,……使得人們十分尊崇狐貍的習性特點……并影響著古希臘的社會發展及文學創作”②;“狐”作為一種行動敏捷、聰明狡獪、生性多疑的犬科動物,其性格特征極大程度上滿足了創作的需要;吉野裕子在《神秘的狐貍》中對“狐”外形的高度贊美,大膽揣測,“狐貍的毛色、體型、姿態和三角形的臉部輪廓,比較符合中國古代男性社會對異性的審美要求”,在我國妖化“狐”形象階段,時常將“狐”刻畫成魅惑、淫蕩的女性形象。“狐”的出類拔萃,是創作者在滿足創作需求的前提下的情感選擇、審美選擇的結果。
三.受眾軸:在受眾本位中差異的“狐”
以受眾視角出發,可以將“狐”形象分為以兒童為核心受眾的“狐”和以成人為核心受眾的“狐”。前者中“狐”形象一般以“狐”的動物本體出現,間或有擬人化描寫。而“狐”的妖化、神化和人性化都是成人世界的“狐”,帶著妖嬈魅惑與愛恨嗔癡,在成人世界里游戲流連。
1.以成人為受眾
將“狐”形象進行審美改造的集大成者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除了《賈兒》和《劉海石》中少數的害人狐妖,蒲松齡在民俗審美的基礎上對“狐”進行文學審美改造,創作了眾多具有人性美和藝術美的“狐”形象,例如《嬰寧》《小翠》《辛十四娘》中知恩圖報的“狐”女,《念秧》《馬介甫》中仁愛信義的“狐”男。郭沫若也曾評價《聊齋志異》,“寫人寫鬼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
《聊齋志異》主要取悅于男性受眾,將“狐”偏重于善良的描寫并不能用來力證作者對于女性的尊重,反而在文中對于女性“圣母”般行為和心理的描寫,表明作者對于女性的觀念是困囿于男權社會的束縛之下的,并不具有突破社會現狀的先進性體現。正如黃婉燕所述,《聊齋志異》中紅顏知己般的“狐”形象是“科場失意后希望知己獎掖的真實心態的反映”以及“對現實情感缺憾的藝術補償”,不管蒲松齡如何刻畫“狐”女的容貌與風華,“都是他在男權話語編織的白日夢中充滿男權意識,寄托著無限希望的文化載體”③。
2.以兒童為受眾
以兒童為受眾的“狐”形象多以動物形態示人,伴有人性特征,但是對于狐貍形象的刻畫多半苑囿在貶義群像中。例如兒童文學作家金近的《狐貍打獵人》、沈石溪的《再被狐貍騙一次》,以及成語“狐假虎威”、“狐朋狗友”、“狐媚猿攀”、“兩腳野狐”等,這些“狐”形象往往和狡猾、欺詐等貶義的詞匯相關聯。馮昀在比較研究中西兒童文學時也表示,雖然中西“狐”形象在“母題”和“情景”上有關聯性,但是“在西方兒童文學作品中,狐貍往往是機智智慧的象征”,而“(中國兒童文學)狐貍一上場,接下來準沒有好事發生”。張婷婷在研究中日兩國的兒童教育觀時也發現,中國兒童文學時常將“狐”塑造成“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與周圍他者對立、沖突的方式解決問題的一種動物形象特征”,而日本作家意將“狐”形象“刻畫成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形象”,宣傳人與動物的和諧相處。
中國“狐”偏向于貶義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國的兒童教育觀念,我們的兒童教育觀念注重“載道”和“樹人”,中國兒童文學肩負著重大的道德教育和現實教育的使命,旨在通過故事教育兒童理性思考,使兒童明辨是非,認知并適應社會,成為國家未來建設和發展的棟梁,因此中國的兒童文學帶著濃重的“使命感色彩”。伴隨跨文化傳播的進一步緊密,中國的兒童文學也將教育功能的基礎上突出“兒童本位”價值,強調了個體發展的自主性、全面性與創造性。
胡堃說,“中國古代狐信仰終于借明清狐仙信仰掀起了它的最后一次波瀾”,伴隨理性主義的發展和封建時代的終結,跌宕起伏的“狐”形象在清末走向衰落。歷史大環境的變化深刻地影響著“狐”形象的沉浮。隨著中國文化自信的增強,對各類文化抱持更加開放和寬容的態度。近年來,新的“狐”形象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并且逐步影視化,傳播范圍更廣。例如《三生三世》系列中青丘九尾狐“白家”,《赤狐書生》中男狐白十三,動畫電影《白蛇·緣起》中寶青坊主雙面狐貍,原創卡通形象《小狐貍發明記》中的“小狐貍叮咚”。有面向兒童受眾的動物化的“狐”,也有面向成人受眾的人性化的“狐”,這些“狐”形象多元豐富,但其實質并未突破“獸”、“妖”、“神”、“人”的范疇,并未實現“狐”形象的第四次轉折。新時代的“狐”是在原基礎上的框架延展和故事細說,是受眾市場細化和傳播功能定位的產物。這些大眾傳播中的“狐”不是為了滿足統治的需要,不是不同宗教間的碰撞,不是文人的心理慰藉,“娛樂”成為新時代“狐”形象傳播的主要功能。
參考文獻
[1]陳登平.“狐貍精”形象變遷及其美學意義[J].陜西學前師范學院學報,2017(3):70-75.
[2]馮昀.從狐貍形象到中西兒童文學比較[J].安徽文學,2009(11):330.
[3]高艷霞.基于古希臘文化的《伊索寓言》中狐貍形象解析[J].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8(11):54+56.
[4]胡堃.中國古代狐信仰源流考[J].社會科學戰線,1989(1):222-229.
[5]黃婉燕.淺談狐女意象所反映的蒲松齡女性文化心理[J].劍南文學,2011(2):77.
[6]李小成,唐海寧.從《搜神記》看魏晉時期的個體意識[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53-58.
[7]張婷婷.從兒童文學中的動物形象看中日兩國的兒童教育觀[J].東北亞外語研究,2018(4):90-97.
注 釋
①胡堃.中國古代狐信仰源流考[J].社會科學戰線,1989(1):229.
②高艷霞.基于古希臘文化的《伊索寓言》中狐貍形象解析[J].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8(11):54+56.
③黃婉燕.淺談狐女意象所反映的蒲松齡女性文化心理[J].劍南文學,2011(2):77.
(作者單位: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